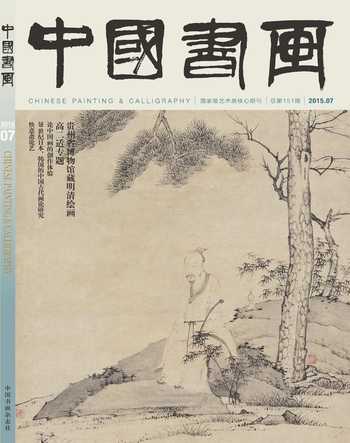我的創作觀


編者按:紐約當地時間2015年1月6日至1月9日,“家在中國富春山——羊曉君隸書展在紐約中關藝術中心成功舉辦,共展出了羊曉君近期創作的百余件書法精品,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家在中國富春山:羊曉君隸書作品選》同時首發。本次展覽是羊曉君繼中國美術館、臺北孫中山紀念館的展覽之后推出的“富春山系列”第三次大型作品展,三次展覽內容均以富春山水為主題,但各有側重: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家在富春山”主題為“感恩”,臺北孫中山紀念館舉辦的“公望富春山”主題為“展望”,而此次紐約的“家在中國富春山”主題為“溝通”。本專題推出的羊曉君書法作品,不僅向大家展示了羊先生近作的風格面貌,而且也展示了他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開闊的文化視野和真摯的藝術情懷。
在多年的書法學習和創作實踐中,我形成了自己以隸書為主攻方向的藝術追求之路。漸漸地,我的這種創作觀與一些作品,開始為人們所接受與肯定。這對于我來說,是最值得欣慰的事。
回想自己走過的路,思考今后努力的目標,也許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首先,追求方整、厚重、高古的藝術風格:其次,重視作品的表情達意。目前,我只能這樣比較粗淺地認識自己。如果要更加具體一些地談談,大概如下。
我在書法學習的過程中,二十多年前就選擇了以隸書作為主攻方向。可能與大多數書友一樣,我是從漢碑著手,刻苦臨寫,中間也寫過一段時間的簡牘帛書,試圖豐富自己的書寫手段;當然也隨時關注當代隸書創作高手的新作品,了解他們的新思考。但一直以來,我在各位老師的指導與鼓勵下反復提醒自己不要跟時風,要努力走自己的路,從而逐步調整自己的取法與創作路子。大約在十年前,我就堅定了自己的想法:追求隸書的高古之意、自然之味,但又不一味取險,而是注重方整、厚重的調子,小心不讓自己的隸書變成時髦的“新”東西。為此,我選擇了《張遷碑》作為自己的書法基調,要求自己多多臨寫,同時選擇了《石鼓文》一類的篆書作為日課,從篆書中去補益隸書的高古之意,避免把隸書寫熟、寫俗。我很欣賞清人姚孟起《字學憶參》里說過的幾句話:“書貴熟,熟則樂;書忌熟,熟則俗”,“古碑貴熟看,不貴生臨,心得其妙,筆始入神”,“熟能生巧。強事離奇,魔道也。弄巧成拙,不如守拙”,“學漢、魏、晉、唐諸碑帖,各各還他神情面目,不可有我在,有我便俗。迨純熟后,會得眾長,又不可無我在,無我便雜。”并正在努力地實踐。
對于臨摹與創作的關系,我的體會是,意識與感覺決定一切,但感覺是建立在長期的臨寫練習的基礎之上的,而意識則是眼界高低的反映。其實,對于某家某碑某帖的臨寫,可能每個人的理解都會不同,而個人在不同階段也會有不同的理解。我在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創作風格后,對于老師推薦的幾種經典碑帖的臨摹仍不放松,但重點轉入到關注如何從中汲取有利于調整與豐富自己創作的方面,而不再是簡單追求臨摹得像不像,也許可以用“神似而形不模糊”這句話來概括。
我的創作觀的另—方面是比較重視作品的表情達意。記得一位前輩書家曾經說過:“書法之精者,可寄性靈,可舒懷抱,表現個性,發揮巧思。”雖然目前我的作品與自己心目中“精”的境界還有很大距離,但是我一直努力追求以書法表現自己的惰性。在這個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了要在筆下達到理想中的目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因此感受到了創作的艱難。首先,我體會到了基礎的重要性。沒有“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的基礎,就無法有更高層面的表現與演繹。但反過來說,在創作中不求表現與演繹,而僅作某家某碑的簡單再現,就達不到書寫的高度。因此,我在平時的創作中特別注重表現、要成調子,演繹要有內涵,即在作品的整體上強調從小處著手,從大處著眼,做到胸中有數:在書寫上緊緊圍繞高古原則,以筆法原理為基點,從容著筆,大膽發揮。在這種心態下'我大體上在一個階段里均能保持較為穩定的創作水平。其次,我不斷體會到藝術修養的提高和精神境界的拓展在創作上的重要性。這決非一句空話大話。我自己是越來越多地感受到書法不應該是簡單地拼筆墨功夫,讀書、明理,氣質、修為,總在遠處召喚自己,我努力避免做單純的文抄公。因此,最近我更多地思考如何在創作中表達自己心靈深處的某些觸動與感受,謹慎地告誡自己不要讓作品出現面貌上的“結殼”,即避免作品過早出現風格定型。雖然一位比較成熟的書法家,風格是必要的外在標志,但我堅持認為:只要觀念上不結殼,創作上就不會結殼:堅持從古代經典中汲取養料,入古出新應當是水到渠成的東西。在這方面,似乎只可意會的東西多一些。我也知道自己在這方面的欠缺,因此可以用言語表達出來的,比如我對形式的關注,我對書寫內容的選擇等,也僅僅如此而已。
以上是我對于自己的書法創作觀念的一些粗淺思考與小結,懇請諸位專家、讀者批評指正。在此,我先行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