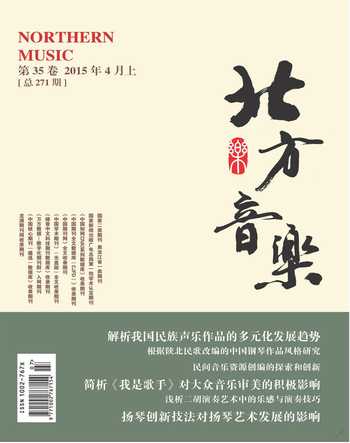中國民族五聲調式“偏音”在旋律中的調色功能之研究
【摘要】中國民族五聲調式中,位于五聲音階兩個小三度間的變宮、清角、變徴、閏幾音,統稱“偏音”,顧名思義,即無正式地位或非骨干之音,因此,傳統的解釋是“在旋律中的作用,多半具有裝飾性,并以經過音或輔助音的形式出現” [1](p67)。但是縱觀民歌、尤其是當代大量的創作歌曲,偏音并非都以經過音或輔助音的裝飾性形式出現,相反,在重要的節奏、節拍位置,樂句、樂段的終止音上,無論民歌還是創作歌曲,偏音都被大量非裝飾性使用,非但不覺生硬、難聽,反而色彩斑斕,引人入勝。本文就各個風格的音樂作品作全面分析,以此來鑒賞民族調式中偏音運用空間的豐富性。
【關鍵詞】偏音;屬性;調色功能
一、五聲各調式的色彩屬性及性格特征
“色彩”是從美術中借用來的術語,在美術中指各種物體因吸收和反射光量程度不同而呈現出復雜的色彩現象。音樂色彩(旋律色彩、和聲色彩),指旋律、和聲在進行時因音高、節奏的不同結合產生不同效果,通過聽覺刺激大腦引起不同心理感受的復雜的音響現象,是一種聽覺藝術[2],它不具美術色彩的直觀性,往往因聽者所受的教育、經歷、環境以及專業知識的不同而感受不同。因此,它具有不確定性,因人而易等特點。
旋律的色彩,主要是通過調式形態來體現的。研究旋律的色彩,首先要了解各調式具有的一般屬性。由于音樂色彩的不確定性和因人而易的特點,很難統一規范。一般情況下,在民族五聲調式的調式色彩方面:宮調式、徴調式熱情、明快,類似美術的紅、橙、黃等暖色;羽調式、商調式含蓄、柔和,類似美術的青、藍、紫等冷色。性格方面:宮、羽調式趨于男質;徵、商調式趨于女質。角調式因缺乏屬音支持,運用較少,性格、色彩均居中。調式的色彩常因其他音樂表現因素影響而發生變化,羽、商調式如配以明快的節奏,也能表達熱烈奔放的情緒。宮、徴調式配以徐緩的節奏、平穩的進行,同樣具有柔和、低沉的色彩。了解各調式的一般色彩屬性和性格特征,在實際運用中才能把握方向,為旋律調色時才能做到心中有數。
旋律的色彩,主要是通過對旋律音高的不同處理獲得不同解釋來實現的。旋律的音高關系,集中表現在調式關系上。如果把旋律音擴大到調的轉換、交替上,使調式中心(主音)轉移,就可擴大調式范圍(調色面)而獲得不同的色彩對比。“偏音”的引入,在一定條件下能形成不同的調式中心轉換,具有調色的可能。
二、偏音的屬性
我國民族調式是以“宮、商、角、微、羽”這五聲為基礎的。在宮和羽、角和微這兩個小三度之間可分別加入“變宮”、 “閏”與“清角”、“變微”,這些加入的音稱做偏音,以C宮為例:
[例一]
顧名思義,“偏音”即無正式地位或非骨干之音,因此,傳統的解釋是“在旋律中的作用,多半具有裝飾性,并以經過音或輔助音的形式出現”[1]。 在我國的民族民間音樂中,由于有著“正音”與“偏音”之分,故而作為正音的五個音常常用得最普遍,即使是含七聲調式中雅樂、清樂或燕樂的民歌或樂曲,也仍然以五聲為基礎,“偏音”只是為了使曲調更加圓潤流暢而作為經過性和輔助性的出現,并不影響五聲正音的基礎作用,一般不出現在節拍或節奏的重要部位,即使出現,也只是輕點一下很快過去,并不作強調,這種用法在民歌中極為普遍[3]。但是也有一部分民歌和現代越來越多的音樂作品中,偏音的功能不僅僅如此, 在旋律中,“偏音”往往呈現出兩種功能,即“以音調色”和“以調調色”的功能。當它與相鄰的音呈小二度、增四度、大七度、減五度音程關系時,“偏音”的裝飾作用未改變,主要起到以音調色的作用,調式中心和宮音位置不產生變化(個別民族的特殊調式例外);當“偏音”與相鄰的音呈大二度、小三度、大三度、純四、純五度、大小六度、小七度關系并處于重要位置得以突出時,即具有他調性——以他調正音作用出現,調式中心改變,“偏音”的裝飾作用被否定,對旋律起調的調色作用。他調性的發展、鞏固構成轉調,偏音變正,起到段落間的調式(性)對比作用,他調性作循環進行,則產生調游移。這種“游移”的連續形成“色彩塊”,使旋律獲得豐富的色彩對比。二者為“偏音”的調色創造了必需的條件。
三、“偏音”在旋律中的調色
“偏音”的調色作用,主要由以下幾種條件實現的。
(一)“偏音”的調色作用依賴于自身的他調性與游移性
[例二]
開始的“#g”只具裝飾作用,詼諧、上口,不改變調式中心;后面“g”音的出現,具有他調性,進入G宮系統D徴調式,形成開放性半終止,配合“在哪里?”的問句,十分貼切。
[例三]
全曲為#f商調式。開篇至半終止處由于偏音“#d”的“經過”作用和“輔助”作用,特別是半終止的輔助作用,助音居于節拍重音,色彩感明顯。
第二句由“#c”音承上句旋律句尾逐步下行至“a”音出現,進入A宮系統循環,具有宮音作用的“a”音的二次強調,又以經過音的形式進入“#g”音,實現鞏固自己,對比前后的目的。與前句色彩音“#d”為增四度關系,與后“#g”音為小二度關系,關系遠,對比強(后另述)。“#g”音本為“正音”,因“a”音的強調被擠為“偏音”,也成為色彩音。因此,盡管“#f”音出現結束全曲,調式仍處于游移(商、羽之間)狀態。正是這種游移,造成一種流連忘返的藝術效果,故多次反復白聽不厭。
從以上兩例中發現,凡調色作用明顯的“偏音”,大都在重要的位置(節奏或節拍)上起作用,因此,大致可用公式:“偏音”+重要位置=色彩來概括。
(二)“非同宮性”的多樣化決定“偏音”的不同色差和必然的調式擴展
調式中心的確立,依賴于宮音和主音的確定。在歌(樂)曲中,主音、宮音總是往返出現于重要的位置以明確調式。“偏音”的他調性就是依據上述原理,利用“偏音”脫離原宮實現調式中心轉移取得色彩對比的,因此,具有“非同宮性”。這種“非同宮性”又因“偏音”在新調的不同地位而產生不同色差。“變宮為角”、“清角為宮”往屬、下屬方向發展,與原宮系統音列有四個共同音(五聲音階,下同),宮音關系為四、五度近關系;“變徴為角”、“閏為宮”往重屬、重下屬方向發展,與原宮系統音列有三個共同音,宮音間為大二度關系。由于共同音的多少、宮音關系的遠近,使旋律的對比具有不同的色差:宮音關系越近、調式共同音越多,色差越小;宮音關系越遠、調式共同音越少,色差越大。因此,同宮系統僅具調式轉換、交替功能,色差最小;非同宮系統除具有調式轉換、交替功能外,還具有調性對比功能,色差要比同宮系統的調式轉換、交替大。非同宮系統中,宮音為小二度關系、增四度關系的,又因無調式共同音,色差最大。
“偏音”能以他調性對旋律起調的調色作用和以裝飾性對旋律起音的調色作用,關鍵在于“偏音”在五聲性旋律中較少被強調使用,當其處在突出地位被強調時,具有“稀為貴”的新鮮感,為二者取得豐富的色彩提供了一定的條件。這種“稀為貴”的作用,關鍵在“稀”,如果連續不斷使用,非但不貴,特別是對于一些習慣簡譜記譜但首調與固定調概念不是很清楚的業余作曲者而言,如果由于記譜不當,在分析作品或實際寫作時很可能會引起誤會。試比較下例:
[例四]
正確的首調簡譜記譜應為:
[例五]
例五的#F音,分別起調的和音的調色作用。
如果把例三不做1=G的簡譜記譜而作為了1=F的簡譜記譜,就成為:
[例六]
例六出現的這個#F音,很容易被誤會成偏音,但是它其實只是首調中的“mi”音,只是旋律被記成一般化旋律固定記譜,因此#F并不具偏音的調色作用。
非同宮性的多樣化導致必然的調式擴展,為旋律獲得豐富的色彩提供了極大的選擇性。
當“偏音”以調的作用調色時,一宮系統的四個“偏音”分別進入四個不同的宮系統,每一個宮系統又產生五個不同調式,加上本宮五調式共二十五個調式,這種調式擴展,極大的豐富了旋律的色彩。試以C宮系統列表說明如下:
[例七]
運用這一理論,使擴展后的新調“偏音”——“變音”的出現和解決得到解釋,調關系也變得簡單、處理自由,旋律的色彩隨之而得到豐富。在實際運用中,可選擇一宮對比,也可綜合多宮多調式對比。下面是一首綜合調式實例,限于篇幅,不再做分析。
[例八]
(三)“偏音”以他調宮、角音出現,對新調的明確具有積極的作用
五聲調式,最顯著的特點是唯一的大三度音程是在宮角兩音之間構成的,因此,宮角音對調式的明確具有重要的作用。缺少宮角音,調式模糊。
[例九]
例九究竟屬商調式、羽調式、徴調式很難確定。它可以是C宮系統的D商調式,也可以是F宮系統的D羽調式,還可以是G宮系統的D徴調式。如果略加調整,出現大三度(或小六度)音程,無論其調關系多遠、記譜如何,出現大三度音程時,根音為宮,冠音為角;小六度時,根音為角、冠音為宮,調式也隨之明確。
[例十]
例十就是由于宮角之間的大三度音程定位,d商調式很明顯的得以明確。
通過分析我們發現,在“偏音”的調色過程中,相鄰兩調的差異往往是發生在宮、角兩音,或“偏音”為宮,或“偏音”為角。即“變宮為角”、“清角為宮”、“變徴為角”、“閏為宮”。
[例十一]
上述差異都發生在本宮(C)系統七聲調式的“偏音”上。因此,當偏音出現并與另一旋律音構成大三度(或小六度)時,他調感便油然而生,鮮明的色彩對比也隨即形成。
[例十二]
例十二調式轉換,“偏音”浸透到C、bB二個宮系統,并用宮、徴調式進行交替,由于大三度音程的出現,使調式關系十分明確。同時我們還發現,旋律的五聲性風格并不因“偏音”的出現而沖淡,相反,不同宮系統的調式互換不但使旋律豐富多彩,對比效果也比較明顯。(由于各調之間關系較近,這種對比沒有突發性)。
例十三調式布局為:
商調式 ——徴調式——商調式 ——徴調式——商調式 ||
(E宮系統)(D宮) (A宮) (D宮) (A宮)
[例十三]
該“偏音”調色的調性思維是“它宮切入、本宮陳訴、開放結束”的結構原則;調式思維是“本調(式)開頭、它調(式)結束”的結構原則。形成它宮系統與主調式(商調式)、本宮系統與它調式緊密結合的對比、統一的有機體,伴以五聲性的旋法處理,使遠關系的調式對比自然、流暢,歌曲朗朗上口,既易于演唱又五光十色,既大眾化又專業化,是一首群眾喜聞樂唱的好作品,也是一首運用“偏音”調色的典型作品。由于其轉換自然,連公開發行的刊物《百名歌星成名曲》也將頭四小節用首調簡譜記為:
[例十四]
另人啼笑皆非。
通過分析我們發現,幾乎所有調式的轉換和色彩對比,都是通過“偏音”為宮或角并與其他音構成大三度或小六度來明確和實現的,充分證明了“偏音”對新調的明確和調色的積極作用,其在旋律中的突出地位和調色作用也隨之得以確立。
四、結語
研究旋律的色彩,復雜而艱難。利用偏音調色僅是多種手法中的一種——重要的一種。研究它的目的在于運用,即在實際創作中重視“偏音”、運用“偏音”和樹立“偏音”的它調意識,運用固定調思維發展旋律,使我們的調式視野更加開闊、調式應用范圍進一步擴展、色彩更加豐富,是克服旋律單調、表現平淡的有效方法。在運用“偏音”調色的過程中,如何做到自然、對比、統一,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色彩對比,涉及到具體的旋法技巧,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需要我們做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李重光.音樂基本理論[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62-10:67.
[2]周青青.中國民歌[M].人民音樂出版社,2005-02:78.
[3]李沙夫.“偏音”在民歌中的運用——民歌中的移宮手法[J].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1993(3):25.
作者簡介:吳麗云(1979—),女,苗族,貴州凱里人,學士,廣西藝術學院音樂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作曲技術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