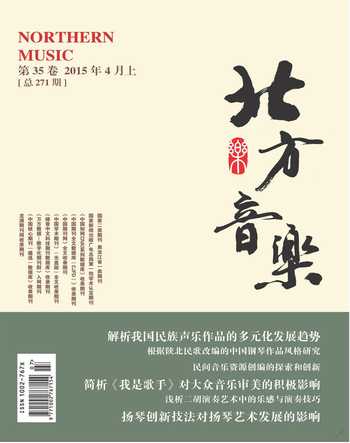跨文化交流視野下的中國舞蹈
伴隨著科學與經濟的發展,人類社會的進步。麥克盧漢所預言的“地球村”在今天已經成為現實。信息交流的快捷、頻繁,突破了傳統地理空間的界限,也為文化藝術的交流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1959年由愛德華.霍爾在《無聲的語言》中首次提出“跨文化交流”,上個世紀已有許多西方文化人類學家針對這一問題進行過論述。20世紀70年代其蓬勃發展,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它的研究成果被應用于政治、外交、文化藝術傳播甚至商業領域。然而舞蹈的“跨文化交流與傳播研究”在我國尚處于初步探索階段,還沒有形成系統化的理論體系,但它的存在與意義是無可置疑的。受到“全球化”與“跨文化交流與傳播”的影響,世界各國藝術在與“異文化”的相互交融中既不斷生成新的內容,同時又極力保持“母文化”的民族精神與獨特性。當下,中國舞蹈藝術工作者們處于一個極易迷失自我的十字路口。我們一方面需要以開放的心態與國際接軌,接受西方文明的養分,并讓承載著民族文化結晶的中國舞蹈藝術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又擔心在國際交流中受到西方強勢文化的影響,喪失本土舞蹈文化的獨立性。于是,跨文化舞蹈交流與傳播的一系列關鍵問題亟待研究。
一、中國舞蹈與世界文化的接觸、碰撞由來已久
在中國古代,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不僅開通了“絲綢之路”,也開啟了中西舞蹈文化交流的歷史篇章。四夷樂、胡樂胡舞、角抵百戲豐富了中原樂舞內容,漢代樂舞的形式多樣化、景象大繁榮正是得益于“跨文化的藝術交流與傳播”。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興盛的娛佛樂舞,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那些具有濃郁西域風情的佛像、人物、“飛天”和“反彈琵琶”等舞姿,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在敦煌石窟壁畫之中,見證了中外舞蹈文化交流與融合的史實。中外文化藝術的交流與影響從來都是雙向的,中國樂舞《春鶯轉》《蘭陵王》《佳人剪牡丹》等在唐宋時期已傳入日韓,對于日本、朝鮮、韓國的舞蹈文化產生了極大影響。
中國近現代,特別是民國初期到抗日戰爭爆發之前,是中國與外來舞蹈文化交流頻繁的年代。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文化受到沖擊,為尋求救世良方,中國進步知識分子主張向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學習以強大自己。在“西學東漸”的時代洪流中,西方舞蹈文化被帶到了中國:俄國僑民在中國開設芭蕾舞培訓班;中國都市市民熱衷于跳交誼舞;包括圣丹尼斯—肖恩舞團、莫斯科鄧肯舞蹈團在內的西方藝術團體頻繁訪華演出;中小學學堂舞蹈課翻譯使用外國舞蹈教材;以及留學歸國的舞蹈家裕容齡、戴愛蓮、吳曉邦等人的藝術活動。可以說,這一時期西方舞蹈文化的傳入對于中國現代舞蹈演藝和舞蹈教育的影響是比較明顯的。與此同時,梅蘭芳與圣丹尼斯的同臺演出和出國訪問,黎錦暉、梁倫的南洋演出,也讓世界看到了中華民族是一個善舞的民族。
二、目前,中國民族舞蹈在對外交流中出現的問題及原因
1949年建國后,中外舞蹈文化交流進入了全新的時代。從《飛天》《荷花舞》等中國民族舞蹈獲得國際金獎被世界認可,到西方芭蕾繞道前蘇聯全盤引進,并與中國民族傳統舞蹈相碰撞相交融而產生的大量舞劇,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之后的三十幾年里,中國人以兼容并包的開放心態參與世界文化交流。各國不同舞種、不同風格的舞蹈大師、一流舞團紛紛到訪中國演出。“跨文化舞蹈交流”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但同時也存在中國民族舞蹈的“西化”現象以及由此引發的“文化身份認同危機”。
1978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藝術團首次登陸美國,在巡演30場民族民間舞的同時,與美國現代舞蹈家們進行交流,這次行程讓中國舞蹈家在原有俄羅斯芭蕾基礎之外看到了廣闊無限的可能性,而且直接影響了中國民族民間舞“元素”教學理念的形成,間接影響了一批舞蹈作品的問世。中國古典舞,毫無疑問是能夠反映中華本土文化與民族精神的舞種,它來自于對于我國傳統樂舞文化的挖掘與繼承。
但是,在其創建與發展的過程中,也曾經兩次受到來自于不同文化語境的不同舞種的影響。第一次是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舞蹈家根據戲曲身段、史料文物中的舞蹈形象,創建中國古典舞學科時,借鑒了西方芭蕾舞的訓練方法。第二次是20世紀80年代,現代舞傳入中國,一些舞蹈編導借鑒現代舞編舞技法進行創作,為中國古典舞注入了全新動作語匯。今天,全國各地的大小舞團,舞者們大多以芭蕾基訓作為每日的“必修課”全國各地的舞蹈院校在招生時也盲目照搬了西方芭蕾對于肢體條件的苛刻標準;中國古典舞里芭蕾的腳下動作和現代舞編舞技法所創造的“頗具現代感的古典舞動作”,更是令我們對于自己的本土舞蹈產生了“文化身份的認同危機”。
分析中國民族舞蹈“西化”現象的產生,原因是復雜的。我們應該給予客觀、辯證地看待。首先,向西方先進舞蹈文化學習,吸取其養分,甚至“洋為中用”是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時代背景下是“歷史必然選擇”。為了迅速改變落后狀況,中國舞蹈家們不得不大量地借鑒于西方芭蕾舞系統化、科學化的訓練體系和現代舞實用化的編舞方法。第二,在“親蘇反美”的特定政治環境下,我們盲從于前蘇聯的一切,認為“什么都是蘇聯的好。”“芭蕾代表人類舞蹈的最高成就”“舞劇是舞蹈的最高形式”,在這樣的狂熱心態下,自然忘記了中西方舞蹈中存在著諸多差異和中華民族“形神兼備”“氣韻生動”的美學理想。
三、我國目前在舞蹈文化的進出口中處于弱勢地位
跨文化交流的最終目的是雙向的文化互動,而不是單向的文化導入。遺憾的是,目前我們在中外舞蹈的進出口方面,尚處于弱勢地位。中國舞蹈文化并沒有在世界上廣泛傳播、推廣。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很多。我們過去往往將其歸咎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政府推動的不力、藝術資助的缺乏等,這些問題確實客觀存在,但是,僅僅看到這些并不利于問題的解決。事實上,我們對于中外舞蹈的市場的需求缺乏調查分析;對于中外舞蹈審美習慣的異同、“文化沖突”的解決等跨文化交流與傳播的基本問題更是缺乏研究,一切尚處于盲目狀態之中。因此,跨文化舞蹈交流與傳播研究對于中國舞蹈文化“走向世界”不僅具有現實意義,且任重而道遠。
現階段,我們必須正視中國舞蹈在國際交流中的弱勢地位。一方面,保持與世界文化的交流與對話,緊跟時代審美步伐。另一方面,自覺堅持自我文化的獨特性,不盲目跟從于“西方”。“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堅持“母文化”的民族性、獨特性我們從能在世界舞壇之上發出屬于自己的聲音。但并不是一切“民族的”都能成為“世界的”,我們在舞蹈藝術的對外交流與傳播中,必須克服以往的“盲目性”遵從民族藝術——世界藝術的發展規律,尊重他國觀眾的審美習慣,以“共同美感”“普適價值”的塑造來引發“文化共鳴”,從而打動世界各國的觀眾。
四、跨文化舞蹈交流與傳播研究帶給我們的啟示
(一)正確看待中國民族舞蹈在與國際交流中出現的問題
跨文化交流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在這一過程中,人們通過對異文化的體驗、評價并在本土文化與異文化的比較中形成自己新的社會文化認同感。也就是說,任何時代、任何民族的文化與藝術都會在與世界的交流中不斷生成新的內容。跨文化的藝術交流與傳播,不同民族之間舞蹈的相互滲透、相互影響本來就是勢不可擋的必然趨勢。“民族藝術”并不在歷史中凝固,而是在時代中演變延續,不斷生發出新的內容,構成人類文明生生不息的脈絡。因此,中國舞蹈在不同時期被注入新的內容實屬正常現象。但是我們缺乏清醒的文化堅持意識,過分地強調異文化的導入,甚至漸漸被其同化,使自己的本土舞蹈文化面臨認同危機,則違背了跨文化交流的理念。
(二)科學引導中國舞蹈“走出去”,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
跨文化舞蹈交流與傳播研究對于中國舞蹈文化“走向世界”具有現實意義。通過分析文化與交流的關系,比較不同文化之間的異同,尋找“沖突點”并將其剝離,探討解決途徑,有助于中國舞蹈早日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舞蹈之林。通過研究分析筆者發現:
第一,在對外文化交流中,舞蹈題材的選擇至關重要。我們必須考慮到信息接收方對于中國文化的理解水平。利用人類共同審美情感與普適性價值引發“文化共鳴”。以中國芭蕾《二泉映月》和《末代皇帝》為例,遼寧芭蕾舞團外事部門的負責人馬林女士曾與筆者談起過遼芭這兩部鎮團之作的海外市場情況。《二泉映月》在國內演出上百場,海外演出為“零”,原因在于外國人看不懂。而《末代皇帝》則能夠滿足不同國家觀眾的審美需求,曾受邀出訪奧地利、法國、澳大利亞、西班牙、德國、意大利、韓國等目前演出場次50余場,受到普遍歡迎。
第二,“芭蕾”在跨文化藝術交流中具有天然的優勢,這一優勢一方面來自于其作為舞蹈藝術“非文字語言”的屬性,與“形式美感”的特征。它可以跨越不同國家之間語言理解的障礙。另一方面,芭蕾舞這種來自于西方的世界性藝術,本就具有各國觀眾均熟悉的國際通用的語言體系和審美標準。因此,它與其他舞種相比,更易于跨越審美習慣與文化的鴻溝,被世界各民族所普遍接受。中國芭蕾(中國題材的民族芭蕾舞劇)是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的最佳藝術媒介,有利于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因此,理應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國家戰略中受到更多的關注并發揮更大的作用。
綜上所述,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研究的是文化與交流的關系,特別是文化對交流所產生的影響。涉及到的主要方面有:比較兩種文化的異同,尋找“沖突點”提出解決途徑;文化的延續與變遷,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依附與文化自立等問題。其中,“文化差異”是影響跨文化交流的關鍵因素。文化與藝術的跨國家、跨民族傳播,難度主要來自于不同國家、民族之間存在著語言的障礙、審美和文化的鴻溝。舞蹈,作為一種承載著人類思想文明、民族文化結晶的身體語言。它具有“非文字語言”的屬性和“形式美感”的特征,易于克服由語言理解障礙和審美習慣差異所引發的文化鴻溝。因此,舞蹈藝術在跨文化交流與傳播中理應得到更多的關注,發揮更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歐建平.中外舞蹈交流30年[J].藝術評論,2008.12.15.
[2]歐建平.中外舞蹈交流中亟待解決的四大問題[J].藝術評論,2013.01.04.
[3]隋巖.全球化語境中的跨文化交流[J].國際關系學院學報 2001.09.10.
[4]關世杰.談傳播學的分支──跨文化交流學[J].新聞與傳播研究,
1996.03.30.
[5]姜琳.文化差異性對跨文化交流的影響[J].國際關系學院學報,
2008.09.20.
作者簡介:王子沂(1986—),女,碩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舞蹈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