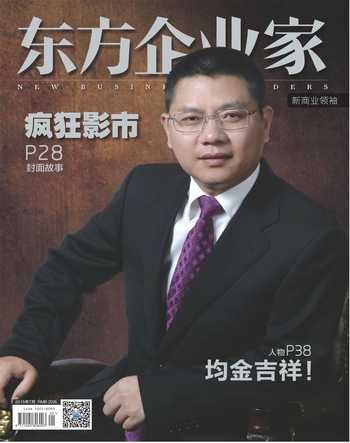當格瓦拉放棄賣電影票的利潤之后……
朱砂

觀眾的聲音通過平臺放大,能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可以給電影帶來很大的增量
走過5年之后,格瓦拉擁有了3500萬用戶;離開盛大文學沉寂了一年半之后,侯小強推出了“毒藥”;3年收獲28億流量的熱門網絡劇《屌絲男士》在這個暑期檔華麗轉身大銀幕……當飛速發展的互聯網擁抱高速成長的中國電影市場,新的路徑在我們眼前展開。
格瓦拉的五年:
見證電影市場對互聯網的接納
愛看電影的文藝青年們,不會不知道格瓦拉。想看哪部電影,直接在線購票、選座,既獲得優惠的票價,又十分方便。
回憶起格瓦拉起步的日子,創始人張學靜說,最初做格瓦拉的初衷只是因為覺得看電影太不方便。那時在網上連排片表都查不到。格瓦拉最初在網友們面前出現的時候,是一家電影排片網站。很快張學靜發現,光有影院的排片信息對于影迷來說用處不大——不少人看到排片表興沖沖地跑到電影院,卻發現票已經賣光,或者剩下的座位都很差。“我覺得既然提供服務,那就提供到底,隨后我們就做了在線選座。”張學靜說。
2009年前后的中國電影市場還未意識到互聯網的價值。影院經理們對格瓦拉這樣的互聯網平臺并不待見。當時,正逢邁克爾·杰克遜的《就是這樣》,張學靜他們在永華電影城包了四個廳的零點場,還請了電子樂隊和三十多個舞者現場打扮成杰克遜的模樣。當晚的活動做得很成功,“那次活動后,我們開始真正打入了上海的影院。”
格瓦拉成長的這五年,正是中國電影飛速發展的五年,“現在中國的電影產業結構正在發生改變,原來只注重拍,不注重賣,跟觀眾離得比較遠,他們無法直接給觀眾一個理由,我為什么要來看這部電影。”張學靜認為,這正是格瓦拉的機會。在積累了3500萬的注冊用戶之后,格瓦拉已經抓住了一批真正的“電影消費者”,從“在線選座”的切入口,到最終形成購買和觀影,格瓦拉占據了整個電影消費環節。
移動互聯網的迅速崛起,培養起了人們利用互聯網處理各種事務的習慣。如今,格瓦拉這樣互聯網+電影票的在線平臺,已被看做產業鏈上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我們實際上是處在一個多方的交叉口,制片會找到我們、發行會找到我們、院線也會找我們合作,而我們最大的鏈接對象是觀眾。我覺得,現在電影市場對互聯網的接納度是空前的。”巨大的市場吸引了更多的資本,觀眾們很快發現自己有了更多的選擇,比如貓眼、淘寶電影等。
和格瓦拉當初起步時的“不被接納”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今年5月上線的APP“毒藥”。5月19日,前盛大文學CEO侯小強在個人微博上發布了一篇《今夜,我去赴一場并不存在的約會》,宣布“毒藥”正式上線,作為“毒藥”創始人的他,這樣描述這款APP:“這是一款便捷地為你喜歡的電影和書打分和評價的工具。這里有中國最大的電影圖書數據庫。有不斷完善的電影票房和首次公布的圖書銷售數據。”上線一個月后“毒藥”已經擁有三十多萬用戶,“我沒花一分錢推廣,已經有許多大片的出品方、影視公司主動找到我,希望與‘毒藥合作,為他們的影視劇做宣發。”侯小強說。
線上社群:
推動電影營銷的細分
6月,上海國際電影節如期而至。這一次電影節選擇了和“淘寶電影”合作票務事宜。“無票可賣”的格瓦拉并不冷清,“電影不等于買票賣票。我們更希望為用戶營造一個全民參與的觀影氛圍,將上海國際電影節打造成整個城市的狂歡節,成為城市標簽。我們包下了一個咖啡館,作為影迷們的狂歡派對主陣地。”張學靜正是在這個咖啡館里,接受《東方企業家》的采訪的。他介紹說,“咖啡館里每天都有格瓦拉的小編在現場,影迷們可以在趕場看電影的間隙來到這里,和小編或者其他影迷聊天,分享觀影的感受。”
從在線選座賣票起家的格瓦拉正在“互聯網+影視”的大潮中,尋找自己新的方向。
“我之前說過,賣電影票利潤特別低,不是一個特別好的商業模式,但是不要緊,如果我賣50億元的電影票的話應該可以養活公司吧。我現在覺得,賣50億元的話還是養活不了公司。所以,我就不再想賣電影票的利潤這件事情了,我甚至還想直接按進價把電影票賣出去。我有用戶平臺,這些用戶是真金白銀買票看電影的用戶。”張學靜說。
不準備在電影票上獲取利潤,那么未來的營利方向何在?“第一,格瓦拉可以成為一些小成本電影的孵化平臺。第二,我們在創建、探尋電影未來的宣發模式。”張學靜說,“你覺得現在電影導演缺的是錢嗎?他們不缺錢。他們缺的是對影片的成熟的運作方式。市場應該做一個細分。比如《少女哪吒》,如果全國放映,上座率肯定很低,可是,如果每個城市只選兩家影院放映呢?上座率就不低了吧。”
張學靜發現,不同的影院適合不同的電影。文藝片在地處商業中心的電影院的晚場賣得好,在高校周邊的影院票房也很好,因為學生觀眾多。而動畫片則在社區影院票房最好。
影院的細分化決定了商業模式必須有細分,與之相關的當然是營銷方式的細分,也可以反過來說——電影觀眾和電影內容的溝通方式的細分。“大白”火爆銀幕的日子,有個格瓦拉的用戶寫了篇文章,說看完“大白”之后自己選擇了分手。那篇文章在格瓦拉被點擊回復了一萬多次。“一位同事提醒我,這個事情值得我們思考——為什么這個用戶不去朋友圈發,不去微博發,卻非要在格瓦拉發?”張學靜說,“朋友圈里的人各行各業,喜好不同,我每天發自己喜歡某部電影,對于那些沒興趣的人來說是一種騷擾。但是,在格瓦拉都是喜愛電影的人,可以獲得更好的共鳴。如果這種邏輯成立,那么觀眾的聲音通過平臺放大,能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可以給電影帶來很大的增量。”
張學靜的這個觀點和推出“毒藥”的侯小強不謀而合,“我現在選擇看哪部電影的時候,更愿意選熟悉的人推薦的,或是我同樣年紀的人推薦的。跟你有相同經歷的人的點評對你更有意義,這就是毒藥的定位——社群。”
在張學靜看來,未來電影的營銷和宣發模式一定是以互聯網為中心,“五年以后,電影發行經理還需要去影院談場次嗎,沒有必要。整個大數據的情況已經出來了,發行經理只要向影院經理溝通好這個電影適合哪些觀眾看,然后發行方需要做哪些工作就可以了。”
熱門網劇轉身大銀幕:
“互聯網+影視”新路徑正在形成
無論是格瓦拉,還是侯小強,在線上做著讓影迷交流的社交平臺的同時,都已經把觸角伸到了影視劇投資中。侯小強名下有一家影視公司,“我們有近二十人的團隊,每天看IP,刪選劇本,目前已經儲備了20個項目。這些IP幾乎都從網絡上來。”侯小強說。
在互聯網流量破28億的搜狐視頻的自制劇《屌絲男士》,在這個暑期檔以《煎餅俠》的面貌華麗轉身大銀幕,似乎印證著互聯網+影視的全新路徑,事實上在它之后另一部網絡紅劇《萬萬沒想到》也將登陸大銀幕。《煎餅俠》的導演同時也是主演大鵬,用一個宣發的細節說明了這部從互聯網走上大銀幕的電影與傳統電影的不同,“很多電影做宣傳時都會去學校做活動,我選擇的是藍翔技校,因為它在互聯網上很火。我們去藍翔技校宣傳的消息一出,馬上就登上了微博熱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