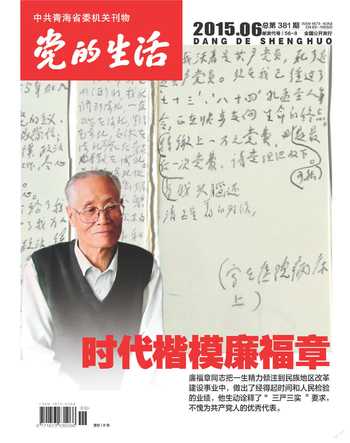《大美青海——青海省情教育讀本》選摘
第四講多元文化
第三節“花兒”為什么這樣紅
在蒼茫的大西北,在那遙遠的地方,自古就流傳著許多醇厚幽婉的民歌。其中,“花兒”以其悠久的歷史傳承、豐富的吟詠主題、獨特的演唱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成為一朵朵盛開于大山鄉野的奇葩。
青海是“花兒”的故鄉,河湟“花兒”更是西北“花兒”的精魂。最美的“花兒”就是由三江源頭的凈水澆灌出的圣潔之花。勤勞樸實的各族群眾,無論在田間勞作,山野放牧,趕赴廟會、外出打工,甚至在趕車的路上,一有閑暇,都要漫上幾句悠揚婉轉的“花兒”,以表心懷。在這里,人人都熟悉“花兒”的內容與唱法,人人都有一副唱“花兒”的好嗓子,男女老幼都遨游于“花兒”的海洋,盡情表達著他們對生活的認知和對理想的追求。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花兒”被視作是一種“野曲”,只適合在山川野外演唱,所以對它的記錄少之又少,僅靠民眾口頭傳承。正因如此,幾經歷史風云,“花兒”傳承至今而未失其真,未傷其神,雖“蓬首粗服”,卻“不掩國色”。加之傳唱于邊陲,文化上較少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染,使其保有相對的自足性和頑強的生命力,直到今天并未失其樸野之風。
作為一種民間歌謠,“花兒”是流行區域各民族共同創造和培育出的民間藝術之花;作為一種文化,“花兒”則完全跨越了族際界限而為各民族所共享。“花兒”是一種不同民族之間多元文化相互吸收、碰撞、融匯,逐漸整合而成的文化共同體。一般認為,“花兒”這種民間藝術形式成熟并流行于明代,傳承至今,可謂年代久遠。
就其詠唱的內容來看,“花兒”涵蓋的范圍是非常廣泛的,從神話傳說、歷史故事到宗教人文、民俗風情;從天文地理、自然風物到山川草木、花鳥魚蟲,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綜合來看,其基本主題大致有二:一是禮贊生命,歌唱青春;二是訴說衷腸,表達男女之間的深情愛意。此外,“花兒”還涉及出門人對家鄉的思念、親朋好友之間的深情厚誼、新社會時代風貌和生產生活中諸多美好或苦難片段,雖數量相對較少,但情真意切,聽來回味無窮。
比興是“花兒”在藝術上最突出的特點,在抒情過程中總是借助具體的物象來起興或作比喻,從而形成了和《詩經》類似的比興現象,“花兒”中的比興之物除了形式上的意義外,還具有特定的文化意蘊和特殊的象征意義。如牡丹、鳥、魚、云、雨等物象暗含有兩性相戀的意味。
“花兒”的唱法跟曲調有關,不同的曲調有著不同的“令”。據統計,河湟地區有上百種“令”。按流行地區分為“河州令”“湟源令”“川口令”“循化令”“互助令”“西寧令”等;按照演唱民族劃分為“土族令”“撒拉令”“保安令”“東鄉令”等;按照“花兒”的襯詞又可分為“白牡丹令”“尕馬兒令”“花花尕妹令”“好花兒令”“溜溜兒山令”“楊柳兒姐令”“水紅花令”“咿呀咿令”“沙燕兒繞令”等。每一種令都有其自身的唱腔和旋律。“花兒”這種“令”的形式又與古典文學中的元曲之曲牌極為相似。老百姓除了在余暇時間、勞作之際唱唱“花兒”外,民間自發形成的“花兒”會又為這種民間藝術提供了一處絕佳的表演空間。在“花兒”會場上,大家不分民族、不分區域。前來趕會的群眾不約而同,歡聚于一處,演唱“花兒”、交流情感,尤其是各種“花兒”擂臺賽,更是將民眾的注意力和他們的希冀串聯在一起,唱他們所喜,訴他們所悲。在青海,規模大小不一的“花兒”會數目甚眾,具有代表性的有西寧鳳凰山“花兒”會、民和縣峽門“花兒”會、民和縣七里寺“花兒”會、樂都縣瞿曇寺“花兒”會、互助五峰山“花兒”會、互助丹麻“花兒”會、還有大通縣六月六的老爺山“花兒”會。其中,大通老爺山“花兒”會、互助丹麻土族“花兒”會、民和七里寺“花兒”會和樂都瞿曇寺“花兒”會已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十分有趣的是,各地的“花兒”會,不僅風情各異,而且大多與美麗的傳說有關,與某些獨特習俗相連,更與普通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青柳垂絲夾野塘,農夫村女鋤田忙;輕鞭一揮芳徑去,漫聞花兒斷續長。”欲知“花兒”事,想觀“花兒”情,還得身臨其境,親自來采擷那些美麗的“花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