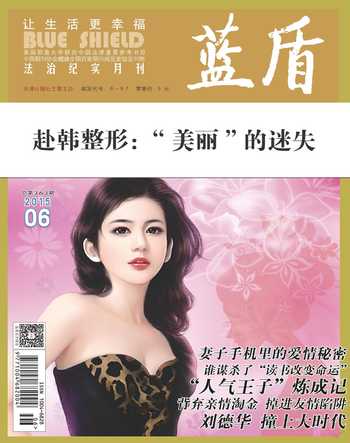該怎么證明我媽是我媽?
牛角
“該怎么證明我媽是我媽!”這是北京市民陳先生的一句感慨。聽起來有些好笑,卻是他的真實遭遇。陳先生一家三口準備出境旅游,需要明確一位親人為緊急聯絡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親。可問題來了,需要書面證明他和他母親是母子關系。可陳先生在北京的戶口簿,只顯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戶口簿,早就沒有了陳先生的信息。最終解決辦法是,陳先生向旅行社交了60塊,就不用再證明了(據4月8日《人民日報》)。
新聞里說,很多人在辦事過程中遇到過類似令人啼笑皆非的證明:要證明你爸是你爸,要證明你沒犯過罪,要證明你沒結過婚,要證明你沒有要過孩子,要證明你沒買過房……這樣那樣的證明,有的聽起來莫名其妙,辦起來更讓人東奔西跑還摸不著頭腦。
可能有人會問,為什么就不能夠更靈活地解決問題呢?簡單地回答這個問題就是,在現場解決問題的人沒這個權力,有這個權力的人離現場太遠。制度或是政策法規的運行,有的時候就像在電腦里運行一段程序,這程序被寫就運行起來,它就按照自己的邏輯行事了。如果程序遇到了不符合其邏輯的特殊情況時,程序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這就是bug。而在政策的執行中,就會出現“證明我媽是我媽”這樣的怪事。
這樣看起來,制度好像是有了生命一樣,按照自己的邏輯行事。還真就有這樣一種理論,看學者孫立平的文章介紹,英國著名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曾寫過一本書,叫做《制度是如何思維的》。這個書名就是有意告訴我們,制度是會思維的。當然這只是一種比喻,制度怎么會有思維,制度的邏輯背后其實就是人的邏輯。可能問題在于,當人們制定了制度之后,并不一定能完全預料到制度會帶來怎樣的結果,也不一定能預料到制度會遇到什么樣的特殊情況。
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機動車撞行人的責任認定,其中規定即便機動車完全沒有事故責任,也要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邏輯很簡單,行人是弱勢一方,所以要求駕駛員倍加小心。后來就出現了這樣的新聞,一個行人撞在了停在路邊的汽車上,車主按照規定需要進行賠償。車主太倒霉了,但沒辦法,法律只能考慮大多數情況,不能完全涵蓋特殊情況,遇上這種奇葩事兒,也只能按照既定法律辦。
還有前不久一個新聞,南方某市一個政府房產部門的打字員,居然貪污了400萬元巨款。許多人都來打字員那里打印資料,叫號排隊,而那些房地產的老板也不差錢,為了提前審批通過,賄賂打字員,而打字員則有權決定打印順序。打字員獲得尋租的機會,是因為這里是指定的打印材料地點,而這么規定的理由可能是因為該部門想收一點打印費吧。可就這樣一個小政策造就了一個巨貪,這是制度制定者沒有想到的。
當制度“活”了,開始運行起來的時候,想要阻止它、改變它就變得不那么容易了,而且系統越復雜難度就越大。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從事后來看,最直接的辦法當然是拿掉出問題的環節,處理犯錯誤的執行者。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應該從改變體系本身著手。首先,制度制定者要解決動機問題,就是制定這套制度法規是為了什么?我想答案應該是為了保障服務對象的權益。出境游客的權益就是辦理手續的合理性和效率,房地產商的權益就是審批的便捷。如果制度的設計者以自己的便捷甚至是獲利為目標,那么結果就肯定是給服務對象造成麻煩。
第二個改變是對體系的簡化。邏輯學上有一個很著名的原理叫做“奧卡姆剃刀”原理,其內容是“如無必要、勿增實體”。意思就是,用一把剃刀把系統中所有沒有必要的環節統統砍掉,簡單管理、提高效率。制度的設計也是這樣,越簡單、越透明、越靈活越好。就比如那個機動車撞人責任劃分問題,我們可能需要從立法層面才能做出改變。而執行案例法的國家,一個具體的判例就可以成為法律,相比之下靈活多了。
最后回到新聞,如何回答“該怎么證明我媽是我媽”這個問題?答案肯定不是讓人家去驗DNA,因為這個具體問題背后是系統性問題。對此我們的解決辦法只能是簡政放權。就像《人民日報》從這件新聞得出的結論:各級政府部門有必要結合簡政放權的時代要求,與時俱進地對需要當事人提供的材料事項進行梳理,能免的就免、能簡的就簡,從源頭上減少對證明的需求。
(摘自《新文化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