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對話的姿態和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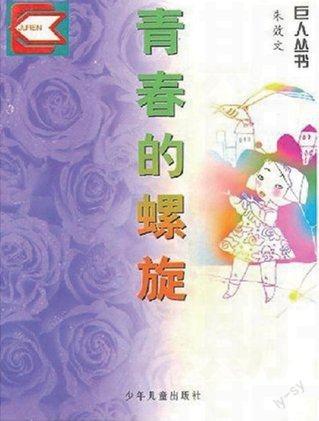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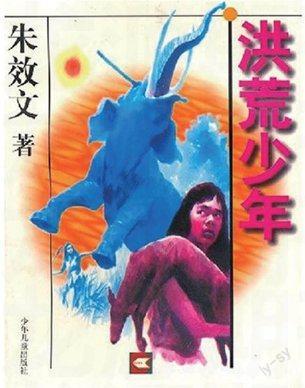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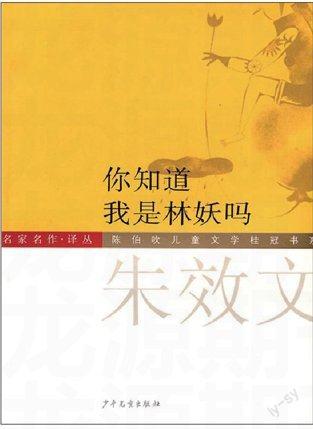
朱效文是30多年來中國重要的兒童文學編輯家、作家之一。改革開放初期,朱效文依托對科學倫理、社會規則以及人性的洞察、揶揄,形成了自己觀照情感世界與敘事的特色,構筑了一個在藝術上精微而到位的童話世界。在之后的創作、編輯生涯中,朱效文通過自己的創作,用情感和美的力量去消除敘事上的“程式”,推進童話敘事的變革,并取得了商業化出版環境下的藝術實績。
[作者簡介]齊童巍,博士,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朱效文是30多年來中國重要的兒童文學編輯家、作家之一,他在“《少年文藝》九年,《巨人》九年,《兒童文學選刊》九年”,被譽為“三個九年,串聯起中國原創兒童文學三十年的榮光與夢想”[1]。朱效文2010年在文匯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自選集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我似乎覺得,散文的紀實特性使作者不便于直接表達兒童的情感,而過多成人情感的抒發難免會使作品拉大與兒童讀者的距離。好多年后我才發現,這其實是一個誤解。兒童文學從根本上說,是成人作家與兒童讀者之間的精神對話。”[2]精神對話的定位化解了成人作者與兒童讀者之間的“鴻溝”,這可以看成是一個從事了近30年兒童文學寫作與編輯工作的作家,對兒童文學的至深“體悟”。朱效文創作、評論中的“精神對話”就是在其個人生命歷程和歷史的腳步中漸次展開的。
一
早年間孩子般的鄉間幻想和鄉村生活經歷,縈繞于朱效文的創作思想中,這似乎是他與時間上已經遙遠,但記憶里仍然清晰的鄉村生活之間的無盡對話。“孩子沒讀完初中,就去遠方偏僻的農村當了一個農民。他干起農活來很拼命。耕作之余,孩子喜歡一個人睡在渺無人煙的地頭,望著滿天變幻無窮的絢麗云霞,想象著它們是仙女的霓裳,是天神的戰馬,是鳳凰的羽翼,是游龍的鱗光。夜晚,孩子常常躺在谷場的草堆上,盡情地欣賞著在城市里從未見過的璀璨銀河,想象著它的流動,幻想著蘊藏在其中的神話般的天宮。”[3]這是朱效文2005年的作品,離“孩子”的地頭遐想已經過去了30多年,但是我們卻可以發現他回憶筆觸里的神往與幸福。也許只有在有文化的異鄉人眼里,或者在像《風景》里的雛燕、《船情多變》里的阿彤一樣有“知識”的農民眼里,鄉村才不只是貧瘠、愚鈍,還有如此的“風景”。就像朱效文在《鄉情》里訴說的,“綿綿的鄉情/是從瓦屋脊頭的煙囪里/縈縈裊裊升起來的/升起團團迷霧般的精靈故事/升起幾對愛扮精靈打仗的/淘氣娃/靜靜寒窗下/伴我苦讀的/是甜甜的鄉情/輾轉反側中/伴我入夢的是悠悠的鄉情”。
也正是“知識”加上下鄉也無法扼殺想象的“興趣”,成了朱效文進入兒童文學創作所依托的“資源”。《與敏豪生比吹牛》(《童話報》1985年第3期)算得上是朱效文最早的代表作了。朱效文借用《吹牛大王歷險記》的角色和敘述風格,衍生出一個充滿 “現代化”氣息的“互文性”文本。從朱效文對《吹牛大王歷險記》的贊揚中,我們可以明白文本的淵源。“這本小書里的幾乎每一個故事片段,都充滿著不可思議的智慧,它是智慧的集大成者。”[4]《吹牛大王新傳》(1990年)、《培克博士的奇跡》(1991年)等朱效文早期童話集中的作品,就大有“打破了孩子們心中習以為常的禁錮,粉碎了孩子們頭腦中被教科書和成人訓誡反復設置的條條框框,甚至打破了自然科學的某些所謂‘真理,使被長久抑制的想象力突然獲得解放”[4]的架勢。
這些以唐剛剛、敏豪生、大猩猩培克博士為主角的短篇在情節上相互“連綴”,敘事邏輯嚴密而又奔放,在不長的篇幅里騰挪出廣闊的想象空間。這些童話對“非生活本身形式”[5]的巧妙運用,所依托的是朱效文對科學倫理、社會規則以及人性的洞察、揶揄,同時,這些略帶諷刺的只言片語也是荒誕童話、狂想文字的底色。20世紀80年代末,朱效文在評論當時兒童散文創作時,痛心疾首地說,“小說和詩歌藝術的自由發展已把散文拋在后面。當散文忽然發現,自己竟成了最不自由的文體時,它就不會為失去讀者而感到疑惑了……藝術上的程式化、感情上的規范化和議論上的標準化,是和講求個性的散文完全對立的。”[6]像小說一樣敘事的童話,在藝術形式上與小說有相同之處。這樣,我們也就能理解這一時期的朱效文童話對“藝術上的程式化、感情上的規范化和議論上的標準化”的有意突破了。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是那一時代作家的共識,但朱效文卻是童話敘事營構的佼佼者。他童話創作的數量雖然不是特別多,卻形成了自己觀照情感世界與敘事的特色,構筑了一個藝術上精微而到位的童話世界。
二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朱效文進入兒童文學編輯崗位并進行兒童文學創作的時候,正是新的創作沖動在兒童文學作家們心中和筆下開始涌動、勃發的時期。朱效文贊賞張秋生的小巴掌童話是“在美學追求上的自由變化”,是“審美上的自由感”,是“表現深邃的人生哲理”“豐富的美學追求”,“讓孩子們在驚奇和歡笑中,悄悄地感受美,悄悄地認識世界和人生,悄悄地為即將聳立的人格大廈奠基”[7]。在自己的創作中,朱效文也正是用情感的、美的力量去消除敘事上的“程式”,推進童話敘事的變革。
朱效文說,“曾經有評論家把我的小說歸入‘問題小說之列。但在我看來,雖然我的小說中,有些題材和主題與現實比較貼近,反映了當下現實中存在的某些問題,但小說并不是用來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我只是想通過我的小說,如實地描繪現實中某些不太合理,不太有人性,甚至有些荒謬、有些無奈的現象,為孩子們點燃潛藏在他們心靈深處的光明火種。這不是在提出問題,而是在揭示某種被表象掩蓋的‘秘密;這不是在標示解決問題的具體路徑,而是在鼓舞孩子們擁有走出困境的勇氣,喚醒他們沉睡的激情”。[8]無論是長篇、中篇還是短篇,無論是現實生活題材的《青春的螺旋》(《巨人》1996年第4期),還是寫遠古祖先們的《洪荒少年》(《巨人》1996年第2期),我們都可以或隱或顯地看到朱效文這種“點燃潛藏在他們心靈深處光明的火種”“喚醒他們沉睡的激情”的努力。
這時的精神對話已經從朱效文早期短篇童話里略帶嘲諷的冷靜洞察,逐漸走向了更為寬厚的溫情。因此,也帶來了兩個方面的結果。一方面,長者的溫情是兒童文學需要的,它可以化解兒童角色、兒童讀者心中的陰云,鼓勵他們走向更為積極、明媚的境地。例如,《月牙島之夜》(《少年文藝》1985年第11期)、《破壞的欲望》(《兒童文學》2003年第12期)兩篇相隔18年之久的小說里,留著一大把花白胡子的老人和秋老師,分別成了鼓勵阿寧、文嫻走出精神困境的“具體”成人。而在《險灘》(《東方少年》1987年第3期)、《走出墓地》(《東方少年》1987年第12期)、《祭日》(《兒童文學》1987年第11期)、《傍晚的天池山》(《少年文藝》1986年第6期)這幾篇相對集中發表的小說里,雖然沒有具象的成人角色,可是我們發現其中主角精神對話的對象,既是主角自己,也是文本的敘述者。正是在這種有敘述者參與完成的“自省”中,主角們走出了人生的困境。在朱效文的校園抒情詩里,詩的意象貫通了成人和少年的心靈,“不用模仿別人的一切/不用把自己按群體的模樣復制/只有每棵小草都獨秀無比/世界的草地才會錦繡萬里”(《獨特的你》)。男孩和女孩也在他的筆下,變得容易理解和溝通,“于是當你的心被塵霧籠罩/你總愛望一眼這雙眼睛/讓她寧靜的光芒/滌蕩你心靈的污泥……你說這不是早戀/因為她的純凈的光/催動著你飛翔的羽翼/你永遠不會在幻覺中沉溺”(《不是早戀》)。因為詩意,朱效文的想象更加飛揚起來,在語態不一的詩作中,他的身心在時空之中穿梭,從“紫葡萄的藤蔓”、“愛哭的老師”的課堂、“校園寂寞的墻根”,走到“湖畔日落”里的“淡紫色的水杉林中”。這是朱效文與筆下少年攜手的心靈遨游。
另一方面,當筆者將朱效文的作品歸攏起來考量的時候發現,他在處理故事走向時,尤其在中長篇小說的后半部分,這種溫情的對話有的時候更容易出現。比如梁燕在《給翅膀一個方向——點評〈你知道我是林妖嗎〉》里對朱效文作品的評介,“即使面對心生報復,即使差點為虎作倀,田園依然在掙扎,她心底的那種善讓她在迷霧中看到光,看到方向。幫助別人,與人為善,這樣的念頭支撐著田園的信念,于是,飛翔有了向上的動力”[9]。當朱效文處理這種善的信念的時候,有時會些微打擾敘事本身的節奏,會讓不同的中、長篇小說的結尾走向同質化的溫情。當然,朱效文也在有意識地控制這種情況的出現。低幼童話里,作家與兒童的精神對話,融匯在了朱效文的講述口吻中和短小的篇幅里。因為“善”力量的引導,小動物身上一個個困境都得到了解除,換回的是各自的收獲與成長。由于低幼童話所面對的讀者對象,這種對話顯得更恰如其分。例如《袋鼠媽媽不見了》里,袋鼠媽媽的快速回歸,可以彌補小袋鼠的失落,也能照顧到幼兒讀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在《網絡趣事》里,朱效文更是調侃了家長們所謂的“關心”和“緊張”。
三
作為出版社的編輯,朱效文處于與市場“親密接觸”的第一線,他明白與兒童讀者“對話”的重要性。如他的“走出迷霧”(原名“走出地獄”)是2002年在《中文自修》雜志第1期開設的一個讓讀者參與的小說接龍欄目。欄目總共持續了12期,在最后一期,作家對小讀者的創作接龍做了點評,同時也刊登了作家原作的梗概。在微博、微信等網絡新媒體尚未普及或出現的2002年,設計這個不斷刊登接龍的互動欄目,是要有很大勇氣的,因為期刊的出版周期更長、發稿期更早。《走出迷霧》小說本身也和《曉凱的森林》一樣,顯示了朱效文在兒童生活中編織偵探故事的能力。
對市場的適應,似乎并不妨礙朱效文對“藝術性”的堅守。在出版社轉企改制,市場化改革日益深入,人們越來越相信、崇拜暢銷神話的今天,朱效文依然覺得“過分地把孩子的審美能力神圣化,把‘兒童本位極端化,其實是否定了孩子在精神上的成長需要,封殺了孩子本應擁有的巨大精神成長空間,助長了孩子在精神上自我膨脹的泡沫,使孩子的審美心理幼稚化……兒童文學批評應當有超脫于市場因素的獨立立場和獨立評判標準,這種評判標準中不光有藝術的標準、人文的標準,也應當包括‘兒童性的標準……兒童文學的藝術標準既是獨立的,又是與‘兒童性的標準相融合,相交錯的,它們共同構成判別兒童文學作品優劣的重要標尺”[10]。在《懷念——在沒有〈巨人〉的日子里》中,我們看到了他面對《巨人》停刊所流露的復雜且無奈的情緒。同時,在忙于編務的過程中,朱效文也積極地鼓勵、幫助青少年讀者和寫作者成長、成熟。比如在作家殷健靈眼中,“之于處于青蔥歲月的我,效文先生早已經超出了一個文學編輯的意義,他是我可以信賴的文學和人生導師、平等交流的大朋友。他讓懵懂的我日漸明白文學的真諦,什么樣的文學才是好的文學,什么樣的路才真正適合我”[11]。從中可以看到朱效文充分運用編輯崗位,憑借自己對文學的熱忱,為文學人才培養所付出的心血。
在《我想有個哥哥》(《巨人》2000年第6期)等作品里,也可以看到朱效文對“藝術性”的堅守。時尚充滿少年風致、人物個性的語言里,朱效文巧妙運用懸念,在緊張的考試氛圍中,在緊張的情節節奏中,在樂觀的情緒基調中,將少年心里的溝坎層層地袒露在讀者面前。如果說,《我想有個哥哥》是借助巧妙的書信讓心靈“放飛”的話,那么《“白瓊號”夢舟》里,朱效文則是借助多種敘述視角的切換,制造出讓心靈飛翔的廣闊天地。多變的藝術手法呼應了他在20世紀80年代就秉持的理念,即“審美上的自由感”“表現深邃的人生哲理”“豐富的美學追求” [7]。這種理念追求化作了商業化出版環境下的藝術實績。
作為近30年來中國兒童文學現實實踐的親歷者,朱效文回顧親身經歷的幾次爭鳴時認為,“現在回顧當年發生的那一次次不同觀點的交鋒,和引起交鋒的那一篇篇作品,我們沒有必要以現在的‘成熟去嘲笑當時某些觀點的‘幼稚,也沒有必要去過多地挑剔當時某些作品還存在的藝術瑕疵,而更應該在歷史發展的宏觀進程中,去分析考量這些爭鳴與探索在兒童文學發展史上的意義和價值,檢視它們給以后的兒童文學創作與研究所帶來的無數精神財富”[12]。這正是我們閱讀朱效文作品、閱讀中國兒童文學實踐時,應保持的歷史理解姿態,也是我們懷著恭敬的心態,與兒童文學歷史對話的開始。
[1]陸梅. 上海兒童文學界舉行金秋筆會 朱效文創作三十年研討會舉行[N]. 文學報,2012-11-08.
[2]朱效文. 冰雪竟然如此美麗[M]. 上海:文匯出版社,2010.
[3]朱效文. 伸展想象的翅膀[J]. 語文世界(小學版),2005(6).
[4]朱效文. 童話的智慧[N]. 文藝報,2009-09-26.
[5]吳其南. 童話的詩學[M]. 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
[6]朱效文. 散文貴在有個性[J]. 兒童文學選刊,1989(5).
[7] 朱效文. “小巴掌”——詩的境界[J]. 兒童文學選刊,1988(6).
[8]朱效文. 在沒人看見的時候[M]. 上海:文匯出版社,2010.
[9]梁燕. 給翅膀一個方向——點評《你知道我是林妖嗎》[J]. ?新讀寫,2009(6).
[10]朱效文. 什么是兒童文學的評價尺度?[N]. 文學報,2005-12-01.
[11]殷健靈. 恩師朱效文[N]. 文學報,2012-11-29.
[12]朱效文. 兒童文學在新時期的幾次爭鳴[N]. 文學報,2008-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