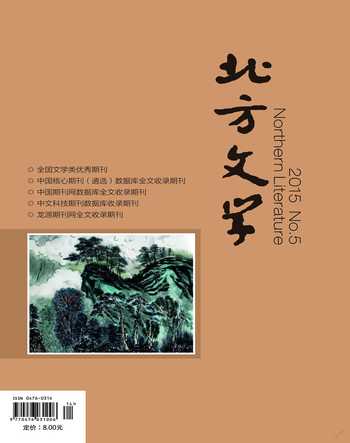一座啟蒙的城市
摘 要:白先勇幼年時期曾在桂林居住過七年時間,其中下層民眾的真實生活狀態、鐵佛寺古舊陰森的氛圍、桂劇的精妙恒生以及東風山腳下的花園時光,這四點對白先勇影響最為深刻。這些童年經驗如同基底,對白先勇的創作思維構成了一種潛藏性的影響,間接指引了其日后小說文思題材的創作方向。
關鍵詞:白先勇;桂林童年經驗啟蒙
從呱呱墜地的1937年到1944年,白先勇有七年的童年時光是在在桂林度過的,七年的時光雖短,但童年經驗對一個作家的成長及創作是尤為重要的,它是一個作家永不衰竭的創作寶庫,可以源源不斷地為其提供靈感,具體到白先勇創作過程,這種啟蒙作用可以概括為:一人、一寺、一戲以及一片花。
一、一人:形色的桂林人開啟人性的審美視覺
白先勇的小說只出現過四個桂林人,即傭人奶媽玉卿嫂,花橋榮記老板娘春夢婆,國文老師盧先生,以及當年雜貨店老板的女兒福生嫂。從數量上說,桂林的人和事確實只是白先勇小說中很小的一個部分,其實,桂林地域性對于白先勇創作的真正影響體現在一種內在的人文關懷情調的生成上。
這幾篇桂林人的小說都和下層民眾的生活有關,而一般的官宦之家往往等級森嚴,像老央這樣‘油漬斑斑的廚子是不允許和少爺小姐接近的,但因為白家家訓極嚴,不允許其子女歧視或虐待下人。所以,幼年的白先勇可以毫無距離地接觸到他們家的傭人以及形形色色的桂林當地人,真實感受生活窘迫狀態下人們的喜怒哀樂。而這種真實的切身感受正是一個作家所必須的,兒童“由于他們的心還未被世俗的種種利益所束縛,他們并不太關切事物的實用性和合目的性。這樣拿就會獲得一種不被世俗偏見所浸染的觀察力,從而把事物作為物自體來吸收。”①,白先勇之后走上創作道路之后,這一段童年的真實經歷更顯得尤為可貴,啟發了他以一種真實的眼光審視一切世事變幻,之后,這一種真實在創作中便上升為一種人性的眼光,如玉卿嫂那份畸形的愛戀代表的是人性中那種強烈占有欲,盧先生坎坷的戀愛與婚姻經歷,道出的是人對于命運無可奈何的恐懼感。當然,童年生活的影響并不是一觸而就的,人性觀察力的觸發還需要多重機制,但在桂七年的生活的確是白先勇創作的第一筆寶庫,是其開挖人性的第一把鑰匙,很難想象,如果這七年白先勇只沉浸于鐘鳴鼎食的繁華中,那么他以后的創作中是否有那種真實描寫,假設不可得知。
二、一寺:神秘的居住氛圍帶來形而上的感悟
白先勇對于時間虛無性的參悟是相當深刻的。歐陽子認為,“過去”與”現在”是《臺北人》的兩個主角,整部書就是在一種蒼茫的流逝感中參悟著人世變遷。可白先勇自己卻說,他對于時間的敏感是不自覺的。聯系白先勇在桂的生活經歷,這種敏感性可能和幼年鐵佛寺的生活經歷相關。
白先勇曾住在桂林鐵佛寺旁邊,“那是一座陰森古舊陳年老寺,鐵佛寺內有一尊大肚鐵佛,而殿內終日香煙繚繞,而鐵佛寺旁邊全是一棟陰森古舊的老屋,長滿了青苔的園子里,猛然會爬出半尺長的一條金邊蜈蚣來,墻上壁虎虎視眈眈,堂內蝙蝠亂飛”②,這里是神秘且恐怖的。試想在香煙繚繞的虛幻中,一群岌岌于生死邊緣的人群,參拜著高高在上的鐵面大佛,同時陰深的古宅像是一個個年邁的老人,悄無聲息地等待著死亡和新生的降臨,而一個還不知曉世事的孩童就整天在其中耳濡目染,接觸著一切關于生與死、未來與現在的神秘討問,很難想象他不會深受其影響。存在主義者克爾凱郭爾就曾認為,個人所有真正的發展“都是返回到我們的起源”,當他“將通過返回到他的起源而試圖去認識他自己;在同時,他將反過來展望它的未來而尋求自我認識。這樣,他將把他的過去和他的未來聯接在現在里。”③而這正是宗教意義的存在。再審視成年后的白先勇對于生命生與死、時間走與停的感悟,不難發現這確實和幼年鐵佛寺的生活存在一定的相通性。或許,正是鐵佛寺這一古舊陰深而又神秘恐怖的居住環境,在年幼的白先勇心中埋下了一個關于時間形而上思考的因子,成年之后一旦再來挖掘便成就了這份不知覺的敏感性。
三、一戲:精彩桂劇種下戲劇啟蒙的種子
白先勇鐘愛戲劇藝術,而這份鐘愛最初也和桂林相關。白先勇的大伯媽是桂戲的戲迷,不僅家里常常請小金鳳、露凝香等名角過來唱戲,他自己也常跑去高升戲院看戲,正是這一份好奇與熱愛,讓戲劇在白先勇的心底生了根發了芽。
首先,不少小時候看桂劇的經歷直接成為了其小說創作的素材,如小說《玉卿嫂》,其中不僅有名伶金燕飛的人物刻畫,“好新鮮好嫩的模樣,細細的腰肢,頭上簪了一大串閃亮的珠花,手掌心的胭脂涂得鮮紅”;有關于桂林人日常觀戲狀況的描寫,高升戲院唱大戲,“門口都是張燈結彩,紅紅綠綠”,而“鑼鼓聲響得叫人的耳朵都快振聾了”;還有名伶金飛燕和慶生的愛情故事,點亮了整個故事的主題框架。
其次,戲或是曲,常是作為結構元素串聯起整篇小說。它們有些是作為整個故事的中心意象,貫穿事件的起承轉合,如《游園驚夢》,小說不僅以“游園驚夢”作為小說題目,更用一支昆曲串聯起藍田玉的過去與現在。另外,戲曲以曲傳情的藝術手法后來常常被白先勇借鑒到其小說的創作當中,話語傳不盡的情,一曲唱詞便形神兼備地補充了其中的曲折婉轉。《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一曲“小親親”描摹了金大班曾有的清純,一種歲月無情的感慨躍然紙上。桂劇對白先勇的影響像是一顆種子,種下的是一種熱情,日后一經灌溉這個種子便長成了參天大樹。
四、一片花:花開花謝感受世事匆匆腳步
《臺北人》的結尾常會出現一些與花草有關的描寫:《秋思》和《梁父吟》寫了將謝之花的頹敗,那些素心蘭“枯褐的梗莖上,只剩下三五朵殘苞在幽幽地散發著一絲冷香”;《思舊賦》和《那片血一樣紅的杜鵑》借用植物的肅殺營造荒涼的環境氛圍,暮云沉沉的寒風里“那些荒蕪的蒿草都蕭蕭瑟瑟抖響起來”(《思舊賦》);《孤戀花》借一曲“青春樅誰人愛,變成落葉相思栽”間接傳達草木凋謝、花瓣枯謝之意,而《冬夜》則以蓮花凌波仙子為喻緬懷曾經的戀人。
這種與花相關的情懷在其自傳及回憶性散文《第六只手指》中有提到,那時白家剛搬到桂林東風山腳下,白先勇是被花環繞著的,新家的花園就在山腳下,種滿了芍藥、牡丹、菊花,同時,還種了一大片非常笨拙的雞冠花。而“當風東山的花開熱鬧了幾度,終于有一天,白崇禧打了勝仗”,“母親就在花園里擺酒宴客”,“母親從花叢中走出來,一條紅呢子的旗袍,使母親艷若群芳”④。可惜不久之后,肺癆讓白先勇過上了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再看百花盛開的時候,自己只能被困小屋,這和之前百花園中的眾星捧月形成了鮮明對比。幼小的白先勇提前感受到了繁華逝去的悲涼,而百花凋謝之后的肅殺正如同此刻被眾人遺棄的感覺。隨后,白先勇走遍了大半個中國,不過正如同匆匆的遷徙腳步,白先勇見證了更多匆匆的逝去和人世變遷的荒涼。于是,幼年時期關于花的情懷得到了升華,花開花謝作為基礎性創作元素進入了他的小說創作,映襯著人世間匆匆而來、匆匆而逝的美好繁華。
小說創作的技藝以及相關創作資源的開發,的確是白先勇在離桂后通過學習而獲得的,但是如果沒有桂林這座城市,沒有這些啟蒙的種子,白先勇的小說創作會走向何方,我們不得而知,至少這一座地理上的第一故鄉,對白先勇而言確實是一座啟蒙的城市。
注釋:
①童慶炳.作家童年經驗及其對創作的影響[J].文學評論,1993(04):54.
②白先勇.第六只手指,白先勇文集第四卷[M]. 廣州:花城出版社, 2000,4:57.
③[法]讓·華爾.存在哲學[M].北京:三聯書店,1987,77.
④王玲玲,徐浮明.最后的貴族[M]. 北京:團結出版社, 2001,1:39.
參考文獻:
[1]白先勇.白先勇文集 [M]. 廣州:花城出版社, 2000,4:58.
[2]王玲玲,徐浮明.最后的貴族[M]. 北京:團結出版社, 2001,1月.
[3]李詠梅.白先勇的”桂林情節“[J].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13(6):120.
作者簡介:梁盼(1990–),女,廣西梧州人,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2013級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