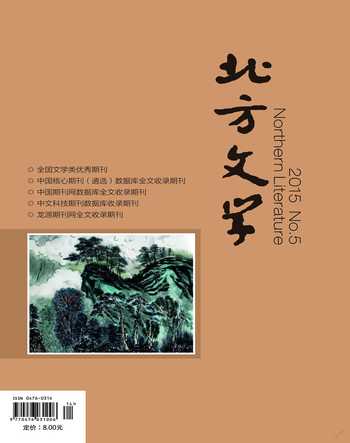《第四十圈》中的架“橋”之思
門瑩
摘 要:在邵麗的中篇小說《第四十圈》中,“橋”這一意象耐人尋味,不僅指小說中的“我”指揮建設的現實中的大橋,還有其深刻的象征意義:“我”作為掛職副縣長,試圖在官與民之間架“橋”,作為作家,努力在敘述者與故事之間架“橋”。作者通過這些象征意義揭示了小說的創作意圖。
關鍵詞:橋;官與民;敘述者與故事
作者邵麗在《第四十圈》的創作談中說道,她在寫完《劉萬福案件》之后原本發誓不再寫類似題材的小說,因為小說即使引起眾人的注意,這一類人的命運也不會被改變,“他們為生活的重軛所規定和壓迫,幾乎沒有翻身的能力。”[1]但是,當看到了齊光祿這個人物,作者決定再次拿起筆來,“顛覆自己的想法”。我認為,作者所說的“顛覆”不僅是指顛覆自己“不寫”的想法,更重要的,是顛覆過去的“寫”時的想法,如小說中的學弟所說,“一個小說家要有穿越情緒的能力,要找到苦澀背后真正的味道。”[2]17她在這部小說中,不再只是通過描寫苦難傳達同情,而是表達超越同情層面的更深層次的思考,思考原因,也思考解決的辦法。這種思考以“架橋”的形式在小說中出現。
一、現實之橋
先說現實中的“橋”。現實中的橋是和“建橋”這個項目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第一次出現是在小說的第三節,“我”作為下基層掛職鍛煉的機關干部,想辦一個有形的項目,司機劉師傅建議修一座縣城通往天中鎮的橋,但是因為齊光祿的案子,天中鎮人有了“不好惹”的名聲,修橋的事情就一直沒人辦。“我”決定前往天中鎮,一探究竟。第二次出現是在小說的第八節,縣政府常務委員會討論“我”提出的這個建橋的項目,天中縣官員對天中鎮的諱莫如深再次引起“我”的困惑,“我”第二次前往天中鎮。第三次出現是在小說的第12節,學弟作為上面負責項目的領導要來視察項目進展情況。最后一次出現是在小說的最后一節,在小說最后還要特別提到這座大橋,可見“橋”在作者心中必定是一個貫穿小說始終的重要的存在。“我”在離開天中縣的前一天來到這座剛剛通車不久的汝河大橋,在橋上感慨萬千,想到人類與河流的關系,想起墜子講的笑話,小說由此結束。前兩次“橋”的出現,都促使我走出政府,去往天中鎮,前三次“橋”的出現,都為我引出了對于齊光祿案的全新的敘述者,“橋”的出現有力地推動了情節的發展,最后一次“橋”出現之后“我”生發的感慨更是將小說主題作了一個深化。由此看出,“橋”在這部小說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橋”的象征意義。
雙重身份的“我”自覺擔負起了雙重的責任:作為掛職副縣長,她指揮建造縣城通往天中鎮的大橋,在建橋的過程中,她發現存在阻隔的不只是縣城與天中鎮的交通,還有政府官員與底層平民之間的溝通,她以親身經驗重新講述特定身份的人物,以期還原真實的生活,是在架一座“官民之橋”;作為作家,她對齊光祿的案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憑借職業敏感,她預感其中的張力可以構成一部好的小說,所以主動傾聽眾多不同身份的人的講述,力圖找到通往故事真相的道路,是在架一座“敘事之橋”。這兩種努力都是在架“橋”,是在兩相阻隔的事物之間尋求可以打破僵局、營造和諧的途徑。
二、官民之橋
《第四十圈》有兩個生存空間,一個是由政府官員組成的“官場”,另一個是由底層平民組成的“民間”。
描寫官員的小說在中國由來已久,在中國古典敘事中,官場小說多是揭露官場黑暗、權貴腐敗的文學作品,如《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等,它在眾多聽著貪官與清官故事長大的中國人心中種下了許多根深蒂固的念頭:貪官常見而清官難得、遇到冤情只能寄希望于清官的出現等等。這樣的集體無意識背后還潛藏著一種對待人的二元對立的判斷方法: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壞人。正如小說中所言:“誰有這么大的能力,說你不是好人,你立馬就變得不像好人了,這到底是怎么回事?”[3]19事實上,沒有誰是天生的好人或壞人,是我們的文化傳統或者一些錯誤的思維定勢引導出了這樣簡單粗暴的論斷。在民間,這樣的傳統意識尤其強烈,小說中牛大墜子的兩段唱詞都是取自包青天的故事,包青天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清官形象,寄寓著老百姓最樸素的依靠清官懲治貪官、伸張正義的愿望,上世紀九十年代,《抉擇》、《人間正道》和《蒼天在上》等反腐小說引起社會的極大關注,正是因為這些小說“依靠‘青天的力量完成了‘懲戒的實施,滿足了中國人自古及今一直固有的對‘青天的期待”。[4]牛大墜子一家的悲劇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們對官員的誤解造成的,比如牛光榮認定齊光祿被抓是政府勢力打擊報復,大叫“老天爺還不睜開眼嗎”跳樓自殺,再比如齊光祿將種種不幸歸咎于前派出所所長查衛東,犯下故意殺人的重罪。這其中反映出的不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誤解,而是來源于傳統文化的,整個民間對官員群體的誤解。
邵麗認為“官場是整個社會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是一種常態。官場生活和我們普通的市民生活有什么不一樣嗎?其實那些個官員,與我們從事任何行業的普通人一樣。一樣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樂,甚至是油鹽醬醋吃喝拉撒。”[5]所以在邵麗的筆下,“我”接觸到的和了解到的官員既沒有傳統敘事中那種十惡不赦的貪官污吏,也沒有像包青天那樣官場英雄般的可歌可泣的人物。小說中著墨比較多的的官員辦公室副主任趙偉中和“我”在發改委任職的副處長學弟,雖然給人一種圓滑世故的感覺,但是圓滑并不妨礙他們的善良,世故只是他們以其敏感與智慧熟悉規則之后在官場自保或者進取的一種生存方式。
“我”對官場空間的審視與描寫打破了傳統的敘事模式,呼喚民間對官員的重新認識,這是架構官民之橋的第一步。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官員對民間的態度問題,如果官員能夠在生存規則、法律原則與為民考慮之間建立一種平衡的話,小說中的悲劇或許也可以避免。
三、敘事之橋
《第四十圈》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文本,故事里面還有故事,簡單梳理文本中的情節,大致分兩個故事,一是齊光祿的殺人案,二是“我”來到天中縣之后一點點了解案件。殺人案在前,“我”的故事在后。但小說沒有采用常見的倒敘結構,而是采取了穿插并置的敘事形式。如果以A代表“我”聽故事的故事,B代表齊光祿殺人案,數字代表故事情節的推進,小說就是A1B1A2B2A3B3……式的結構。A故事里“我”打聽的故事正是B里面所講述的故事。那么B故事究竟是真相,還是A故事里眾人敘述的拼圖,或者只是與眾人敘述都不同的另一個版本而已?作者沒有告訴我們答案,她以這樣穿插并置的形式安排文本,就是想提醒我們注意,講述與真相并不是同一個東西,在兩者之間其實有一道我們常常忽略卻一直存在的鴻溝。故事越復雜,這道溝就越深。意識到鴻溝就是跨越的第一步,作者架橋的努力從這里開始。
A故事里的敘述有以下幾種聲音和態度:
司機劉師傅:以“狠”字評論齊光祿。認為既然張鶴天已經賠償了損失、政府作出了補償、相關官員也被免職,齊光祿就不應該再起事端。
天中鎮鎮長和書記:幾杯酒下肚,打開了話匣子,但卻是七嘴八舌地胡亂插話,“我”到末了也沒聽明白他們說什么。
天中縣縣政府的領導們:回避天中鎮的事情,生怕與那里有任何牽扯。
辦室副主任趙偉中:他一開始也是諱莫如深的態度,后來為我解釋了為什么副縣長們都不敢負責與天中鎮有關的事務,因為如果下面出了問題,分管領導就要負連帶責任,跟著受處理,他們回避是怕群眾上訪,受牽連。
天中鎮船工:大贊齊光祿的岳父牛大墜子,稱他這樣好的富人已經絕種了,慷慨助人、恩澤鄉親。
鄰縣掛職副縣長周友邦:(聽查衛東的同學說的)齊光祿家一家人都不好惹,被殺的派出所所長死得太冤枉。
趙偉中的小舅子(也是縣政協副主席的兒子、齊光祿的初中同學):齊光祿從小一根筋,出這種事是他的性格造成的。
因為各人身份立場不同,認識水平也有差別,所以同一件事才會有如此多不同的描述與反饋,通過梳理眾多聲音,這個道理顯而易見,然而故事中的眾人卻始終未得清醒。他們一直都拘囿在自己的認知里不肯回頭,終于離真相越來越遠。作者在文本中安排眾聲喧嘩,就是想在講述與真實之間搭一座橋,使人們明白,只局限在自己的偏見中是永遠無法抵達真相的。
參考文獻:
[1]邵麗.繼承與顛覆[J].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2014 (3):32.
[2][3]邵麗.第四十圈[J].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2014 (3): 4-32.
[4]王萌.新時期以來官場小說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2013:80.
[5]邵麗.我的生活質量[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