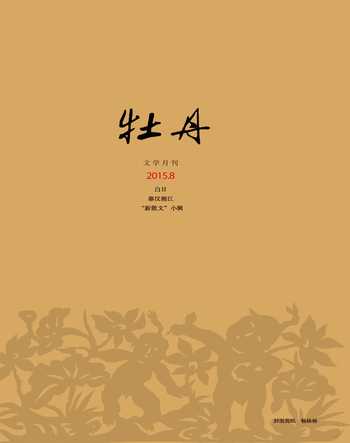蓬頭者,他站在另一個世界向你招手
慕眺
春夏之交,雨水變得充足,天空變得喜怒無常,剛才還是春光明媚,而現在已是大雨滂沱。晚上一場陣雨襲擊了小鎮。驅車路上,一切都裹進水光和燈光撐起的世界之中,令人容易產生幻覺。
掐指一算,他從一個地方遷移到這里,一呆就是九年。日子就如老家居住多年的廳堂,哪里擺舊皮沙發,哪里是水泥樓梯,閉目可知。必經之路旁邊的荒草雜地已經擺上樓房、公園、廣場、商鋪、人群。
一到晚上,城東的廣場上橫七豎八泊著許多小車、摩托車、自行車,幾處廣場舞的音樂此起彼伏地響著。道旁樹郁郁蔥蔥,個別枝丫瘋長,猶如許久未理發的頭顱。生活的經和緯織就的平面,猶如海面。海水漸漸淹沒頭顱,不知從何時起,他試圖不呼喊救命,而在水中呼吸——但這僅僅是奢望。雖漸至沉沒,卻還清醒,他一直在等待另一扇天窗被打開的時刻。這個時刻曾經隱約來臨,但又倏忽不見,猶如墜入海中的網索。曾經捕獲的星光,是否脫網而去?日子壓折了枝枝蔓蔓的感覺莊稼,只留下空荒的田野、麥茬,以及枯萎的稻草人。
雨時下時停,車子的雨刮發出嗚嗚的響聲,和著滴滴答答的雨聲。眼前的視線變得模糊,這讓他變得有點謹慎,不由地探頭盯著模糊的街道,深怕有車或者人從兩側躥出——冷不防,真的從左側綠化帶中探出一個蓬頭——一個瘦高的男子,頭如結痂,疑帶假發。原來,對面是一條窄胡同,這里的綠化帶被人開出個口子,白天眾人從綠化帶橫穿而過,進入胡同,此刻黑暗布滿其間。他心里一驚,不由地踩住剎車,車仍舊往前滑行兩步,車底發出沉悶的摩擦聲“哧哧哧”,在“蓬頭者”面前停步。
那個“蓬頭者”,對此險情似乎并不為意,側對著他,朝著路的對面,使勁地搖手,嘴里還說著什么,最后,還嗔怪似的笑了一下。他從對“蓬頭者”的厭惡和憤怒之中開始驚愕——“蓬頭者”旁若無人地招手。怪異的動作。他想起小時候看見的一個村人——一個因為高考失敗而精神失常者,人家都叫他“大學生”。“大學生”每天固定一個時間段從他家門口經過,拿著趕牛的細竹鞭或者斷樹枝,邊走邊打著道旁花枝招展的野菊花叢,口中囁嚅,俄而呵斥著什么。奔跑的狗會被他揮起的細竹鞭或者斷樹枝嚇一跳,躲在一旁汪汪汪地叫,覓食的母雞則咯咯咯地閃開了。“大學生”眼中無人,只是沉浸在自己破碎的(或者是完整的)世界里——極少的時候,“大學生”會朝他這邊瞪一下,但是,暑期負責看守父親小賣鋪的他無聊而安逸的心會突然一陣緊張——沉悶無趣的水里掉進一個恐懼的石頭,濺起水花。現在,他已并不感到懼怕,更多地覺得,是不是冥冥之中有某只手曾經伸出,活生生地掐斷“大學生”顯得不堪一擊的神經。
眼前的“蓬頭者”使勁地招手,面對黑色的胡同,仿佛里面有需要喚醒的人。
我們把“蓬頭者”、“大學生”放在“精神失常”的盒子里——人一旦被打上標簽,他基本上就在那個盒子里了。但是,反過來看,從這些“狂人”的變形窗口往外看,你是否被觸動,就如看車子后視鏡一般,一切總歸遠去,一切成了陌生的反面?曾經固若金湯的秩序、程序,在“蓬頭者”那里,是否一文不名?事物的固若金湯和灰飛煙滅之間只隔一道念想之藩籬?從這個角度看,看似正常的一切將變得破碎不堪、荒誕不已!
他又想起網絡上那個組建“聯合國部隊司令部”的農民騙子,他拿起自己鑄造的欺騙之矛刺向恐慌的街頭,流出真實的膿血,讓人看到污穢腥臊的腸子露在外面——善良的人們總是不愿意看到血淋淋的場面,認為明日太陽還得升起。“蓬頭者”、“大學生”,騙子像一扇被打變形的窗,時刻提醒我們,固有的秩序、程序之外還有未知的世界。而曾經纖纖如玉的我們只知參與此地的庸常乃至罪惡,且沉溺其中而不自知。
他下了車,居然有和“蓬頭者”握手的沖動。街上一個人也沒有,仿佛都可以聽見兩側樓房里酣睡的聲音。他上前一步,“蓬頭者”眼睛直直地對著他,他也盯著“蓬頭者”——他似乎要去握住“蓬頭者”內心的世界。而“蓬頭者”的目光已越過他,依舊使勁地往黑暗的胡同里招手。他有一種挫敗感……
雨夜易于致幻。等他回神過來,他的車已停在家門口了。雨已停歇,街上空無一人,他似乎聽見整棟高樓打鼾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