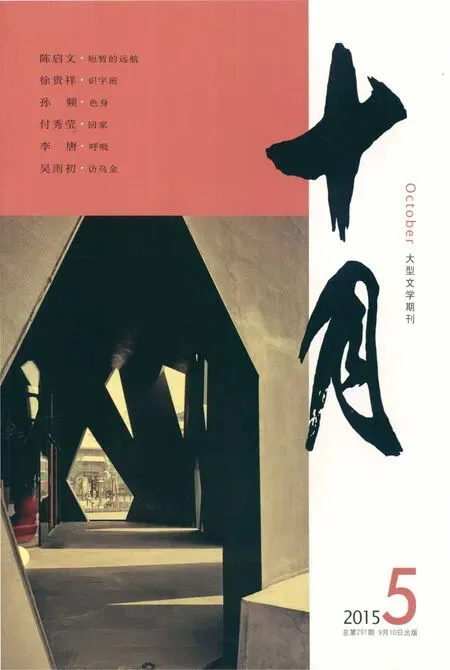靈魂放哪兒
龍冬
北京已是中午。太陽剛從拉薩河南岸寶瓶山頂升起不久,有如青春鮮活明亮,漸漸把我身體照暖。這是二〇一四年三月的最后一天,拉薩還在冬季里死熬硬撐。我媽的電話,問我在哪里。我說在拉薩建筑工地上。我爸感覺不大好。我哥的電話,問我在哪里。我說在拉薩的博物館工地上。我爸狀況不好。其實這十來年我爸身體狀況如同他的一生,總是一副不大好的樣子。甚至已經許多年,我的手機白天黑夜都是打開的,想到隨時都會接到他怎么了的電話。甚至許多年,我在失眠的長夜想到他已經離去了,體驗到孤獨寂寞的一絲文藝快感。
他在我回憶里走過,走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大院的樹蔭下,從學部大院(這個單位在孩子們嘴上還有一個稱謂:鞋鋪大院,就是今天中國社會科學院)六號樓文學所朝東的小門走出,腳底擦地,蹭蹭蹭,往北走到七號樓宗教所一間辦公室我們的臨時宿舍。他個頭小小的,微笑著熱情招呼迎面的熟人,有時也會站住跟一個同事一個上級比如詩人何其芳卞之琳學者吳曉鈴錢鐘書余冠英唐弢什么的正經友好說話。他看到我。我想他要訓我了,結果他卻小聲說,走,我們下館子去。有時,我想他要拉我下館子了,結果他突然沖過來暴怒,吼我混賬只知道惹禍搗蛋,只知道引火燒身。我對他情緒的判斷總歸用今天話講,不貼譜。
我終于感到了不安。交代完工作,匆匆駕車離開博物館工地駛過拉薩河柳梧大橋,趕回駐地。我老伴兒的電話,要我回京。我爸可能不行了。我想這下恐怕真的不妙。趕往貢嘎機場的路上,拉薩山山水水,景色如畫,可是我的喉嚨總被一股熱氣哽住,眼睛潮濕模糊。將要進入機場,我老伴兒又來電話,叮囑不用急,醫生都在,家人都在,還有高僧念經祈禱。家里有兩本《圣經》都是我爸給我的,他卻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他住在北京藏醫院,所以朋友熱心安排了僧人超度。后來我知道那時我爸已經走了。我推算,他走的時辰,我已出了拉薩市區,正由機場高速路第二個長長的隧洞通過。
此前十天,我到內地出差路過北京。最后,我對我爸含含糊糊說,你好好地養啊。他眼睛空洞無奈望著我,問我多久回來。在我轉身之后,他說,在外面小心,不要抽煙,不要喝酒。他的四川鄉音忽然加重。我回頭從虛掩的病房門縫看了看。他一身醫院的藍白條病號服,坐在輪椅上。
我童年對鄉村墳地墳頭很有興趣,特別對那些裂開深深口子的小窩頭墳堆充滿興趣。在國外,除了博物館舊貨店鋪,我只對墓地的寧靜和那些各種式樣美麗的墓碑好奇。我去過西藏的幾處天葬臺。我厭煩火葬場,只要一到火葬場告別什么人,就會惡心。但我并不恐懼。我厭煩的是那些痛苦的和并不怎么痛苦的告別儀式。我在世界上看過水邊露天火葬,也見過高僧真身塔藏。在火葬場,人家肅穆難過佇立鞠躬握手安慰,我卻心有旁騖,總想著到那邊或者半地下的火化爐前試試身手。有一年,我真就那么試了試,從頭到尾來了一個全套嘗試。如何把人平放到耐火石的焚燒床上,如何在人體下鋪墊一層錫紙,這讓我聯想到飯館的一盤菜,紙包魚。電鈕一按,那床沉沉縮進,再一按,聽動靜估計那床深深下降。然后,在我往外走的時候,隱約聽見背后轟然的烈火。不用一個小時,爐門打開。滾燙。晾晾。漸溫。雪白的,如同出土文化期高古玉器的雞骨白,只在盆骨那里殘留一點屎黃。那副骨架完整,指節散落,一根也不缺,頭顱與身體分離,毫無關聯地扭向一側,仿佛對自己的身體早已厭惡透頂。死亡非常干凈。火葬場的焚燒比告別儀式有趣,有活力,更接近再生。人,生命,唯有烈火能夠讓其凈化。人,生命,其實就是一泡水,壓碎裝進一只盒子里的鈣。水蒸發了,升到高空變成白云烏云,再變成水滴落回大地江河湖海。那些鈣融入泥土,生成新的泥土。
我爸火化后,因為工作,第二天我趕回西藏,飛越他的故鄉四川,擦邊飛過他的故園樂山。我替他在天空問候他的早已變成塵土的父母,傳達他們的兒子就要同他們相會了。
一個人,我坐在拉薩河谷水邊窗口,沒有任何聲音。眼睛越過一排小樓,看見拉薩谷地的大風揚起黃塵往光禿禿的山上漫去。白色水鳥在天空被風卷起拋下,如同幾只破爛的塑料袋。我忽然意識到自己噴出的沙啞悲傷聲音,就立刻收斂了。
我按季節和我爸火化那日北京的天氣測算,用衛星地圖查找,我爸那一泡水得到蒸發,向什么方向飄散,飛到了什么高度,飛到什么位置了,他能不能看見我。他在飛升,他已經可以看到他曾經生活走過的地方。他能看見我嗎?他還在飛升,他已經能夠看見從未去到的廣大世界,那些自由的與不自由的。我在深夜的河邊仰望星空,爸,爸,爸,爸。河流嘩嘩作響,其余都是空寂。我身邊帶著我爸的一點遺骨,有時候打開看看,卻不大清楚這是他的哪節肢體。他抱著我的時候,這節肢體觸碰到我身體的哪個部位。
我爸當然和我一樣姓熊,可是沒有多少人知道,一般人知道的是他的筆名。我爸幼年喪母,少小離家在米店當學徒。他讀過私塾,讀過一年正規中學。他的文學寫作完全依靠自修。他寫過詩歌,寫過散文小說,寫過話劇。他的作品總量少得可憐,質量卻還說得過去。我十五歲那年他開始教我寫作,要我寫兩篇文章,一篇每個段落結束的標點必須都在格子外,一篇每個段落結束的標點都要在格子里;教我在飯館里觀察那些食客,分別說出他們的職業,他們此時的情緒,他們家庭關系是否和睦;教我看相算命。我被他訓練成今天的樣子,陌生人分辨我,大體是個刑偵警察。他是一個典型的被社會環境推動的知識分子。關于知識分子,我們小時候喜歡稱之為“吃屎分子”。他這輩子,就是中國普普通通“吃屎分子”中的一員。他在國民黨時代掙扎求生,抗戰,國共戰亂,屬于進步積極的熱血青年。重慶渣滓洞蹲過兩年之后,借國共為渡長江談判之機,作為談判條件他被民主黨派營救出獄。緊跟著談判失敗,共產黨非要打過長江,他又一次成為國民黨搜捕對象,東躲西藏。不久,共產黨軍隊解放了重慶。他得到了解放,專職文學寫作,后來風光地來到北京。“肅反”擴大,他又被戴上手銬重鐐押解回川。那時入川從北京火車到武漢,再從長江乘船逆流而上,多少天,手銬腳鐐拉屎都不給解開。有一回,我爸當游戲教我用雙手擦屁股,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到了重慶,他被臨時關押在朝天門碼頭江邊的房子里一夜,通宵聽到有人投江的落水聲,感到十分恐懼。尤其晚年,幾乎每個深夜他在夢中驚恐喊叫,以致家人都得不到安寧。我爸并非膽小怕死,問題清晰之前,他在北京看押期間有過上吊,幸虧沒有被人發現,否則罪行加重,更要把別人笑死。他完全沒有上吊經驗,只知道吊兩三條毛巾,把下巴輕輕勒了一下。上吊,那毛巾是要在脖子上繞兩圈才好。我在小說里寫過一位老知識分子,他百思不得其解,不怕自己被拉出去槍斃,卻十分害怕被扇嘴巴子,害怕臉上被吐口水。他沒有問題了,終于又回到偉大祖國的心臟。
我爸喜歡北京。他喜歡干燥陽光,喜歡天際博大,喜歡寬廣的大街,喜歡天安門觀禮臺,喜歡人民大會堂的請柬。他喜歡涮羊肉,喜歡莫斯科餐廳和新橋飯店的西餐。他喜歡四個兜兜的干部制服。他喜歡圖書館,喜歡琉璃廠,喜歡燈市口舊書店,喜歡劇院戲場子。他喜歡人與人之間的大氣,喜歡首都的人才濟濟。他受不了“小地方”那些“文人相輕”“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狹窄逼仄。他說過,他死后不回老家。
他在作家協會工作,雖然也曾被楊朔那類人物訓斥,但是楊朔也會被丁玲那個婆娘訓斥。他談到這些總是顯得異常高興。天不冷,那些作家(他是點名說的)頭上都戴個皮棉帽,效仿照片上的蘇聯知名作家。丁玲的大衣不穿上,總是披著,好不威風。他生前聊到這些。我聽說過,那都是一群傻逼啊。他大笑,很生硬別扭地學我粗口。然后他又講,也不能籠統那么說。
他的心我想永遠到死都在文學寫作里浸泡著,可他的確又是被歷史裹挾的一個典型的“吃屎分子”。他必須放棄文學寫作。他不能用自己的腦袋去換取幾篇破小說。首先,打倒非黨文學,他那時還非黨員,這就在資格上沒戲了,至少是矮人一大截。再者,身邊寫作者自殺的流放的抬不起頭走路的,完蛋屁的太多了。此外,隨著年齡增長和閱讀歷史,他的工作業務也轉移到中國古代作家研究。我小時候,只看到他訂閱借閱《參考消息》和《文物》。他對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那個老太婆充滿興趣,時常談到那老太婆臨終前吃過甜瓜,談到她彈性十足的皮膚,談到她衣服的紋飾。
我爸比較早地認識到環境的殘酷,所以他以一個小說家的人情練達和敏感的觀察判斷,認識到自己這一生注定歇菜,注定過客。柔弱勝剛強。反右,他躲過去了。四清,我出生,他下鄉去了。“文革”,他險些完蛋,閃了。五七干校,他又下鄉去了。“文革”后期,他先從干校返京。批林批孔批鄧,我印象中他一天到晚總在開會學習。我媽那時還在干校鄉下。我的童年真像一陣輕風。我一生最大的自由快樂就是大人們這些“吃屎分子”們牛鬼蛇神們都被工農兵抓去,老師們都像嚴寒里的縮頭烏龜,我們小孩成天不用上學,成天讀自己喜歡的讀物,成天爬到房頂煙囪上遠望,成天吊在樹干上吹風胡思亂想,成天打架點燃垃圾站算計打碎誰家的玻璃窗拔掉誰家自行車的氣門芯。猛然,毛澤東死了。偉大的萬壽無疆的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會說話了。我十一歲。那天下午,我的耳朵似乎被棉花堵住,什么聲音也聽不到,沒有留下聲音的記憶。不對,有聲音記憶,也是唯一的聲音記憶。那時候長安街靠近護城河(今天的東二環)不知什么工程,巨大的氣錘整天咚咚作響,一分鐘咚咚四五下,震撼大地。
氣錘的聲音是毛主席逝世時北京最好的畫外音,當然也不能少了北京站鐘聲叮叮當當敲響的《東方紅》樂曲。很快,我爸突然開始寫小說了。記憶里,他寫作可成了我們全家大事,如同一個女人臨產和坐月子。他甚至派我騎上自行車從日壇路到東單為他買散裝啤酒喝。我要創作了。你爸要創作了。這是我常常聽到的家庭話語,以致我發明把上廁所拉屎叫作“創作”。發表兩三篇,突然,他又停止了寫作。當時,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他的小說已經在美國澳洲都有翻譯。他那時若多寫幾篇,不用多,兩三個短篇,或者一個短短的長篇,我想他一定會是時髦的有影響的作家。他甚至還可以調回作家協會,那么他一定會有國內外走動機會,排泄出更多的創作。自然,這一代作家,多數無論有多大名聲和多么多的作品,也是天定沒有價值的。這一點,他當時就看明白了。他雖然心里放不下寫作,買很多外國小說讀,偶爾讀讀國內熟人朋友的作品,但他對當代文學并不看好,簡單說,是看不起。還有,在學術研究機構,我爸寫小說,別人看你就不正經,文學創作屬于不務正業。我爸他還能干什么呢?搞研究,時代變了,就連學術語詞都在急遽變化。他一不是科班出身,二不懂外語,三是固執到底。他大肆嘲笑學術文章里出現什么“集團效應”“突圍”“架構”等等,他認為這些表述不能算真正學問,奇奇怪怪的嚇唬人。我爸他認真了。他把學術把事業比人生看得還要認真。他研究蒲松齡,研究宋代作家交游,時有文章發表。他說文章不在短長,短而有內容,有獨到的考證和結論,要干貨才見真功夫。他教我寫作,可是他又不希望我將來從事當代文學工作。他說,當代文學最危險,學學古典文學,哪怕學學修手表,將來還可以混口飯吃,不至于被打倒進監獄或者流放。他似乎對自己被趕出北京始終心懷焦慮和恐懼。他購買定制了許多件老棉襖和許多條老棉褲,說這些將來到鄉下會有用,遲早是要被驅逐出京。
我爸這代人,新中國成立后,年紀多在三十歲上下,正是可以做事施展才干的年華。比他們大幾歲的,在國民黨舊社會已經奠定了個人的專業名分。比我爸小幾歲的,“文革”后還正當年。“文革”后,我爸已經年近六十。上有老專家,下有小學者,哪還能輪上他啊。時勢造英雄。不以成敗論英雄。我爸時常感嘆。當然他自身也有不愉快的懶散。事情是不能說清楚的。能說清楚嗎?今天的中國還能出個毛澤東嗎?我爸那個年齡段的人,統計一下,各個行業估計沒有幾個做出什么成績的,除了淘大糞的時傳祥和賣糖果的張秉貴他們。所以我爸重視我學點手藝。我沒有聽從他的話去學修手表。否則今天的我一定是個古董鐘表鑒定師,我會對別人有用,也非常非常有錢,過著體面自在的生活。我最終還是從事了當代文學工作。
一個人的認真,倒要叫你喪失尊嚴。未來更不可測。人在一個特定環境里,也許做什么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不做什么,也許這也是生命的一種智慧。
我爸最好的年華就是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是個什么局面?我爸那時真若有為,恐怕也活不到將近九十一歲了。多辱者壽,自然界是均衡的。他曾經到上海組稿,那時的姚文元到飯店見他,非常虛心謙卑。姚文元的確寫了不少,算是成績出眾。
我爸離休后又拿起了文學創作之筆。可這時候他的文筆生硬干澀。他甚至有一天拿個什么破表格填寫,讓我幫忙看看他的行文是否通順。那次我是真的很難過。
照我這么寫下去,若貼近點文藝表達,動用一些真偽細節,一不留心,我自信會寫出個很好的長篇小說。我不寫,偏不寫。因為那個時代還遠遠沒有到來,那縷金燦燦的有如青春的光芒還沒有天天照來。我的任何寫作都是充滿著局限的。我的膽怯,我的虛偽,我天生血液里的規避真實,我的拘謹拘束,我情感表達的煞有介事,和我爸沒有兩樣。甚至,我還遠遠不如他那么認真。寫作,并非玩玩語言、結構和翻檢一些別人文本那點小兒科的事情。
我爸火化那天,我們家人都在。我沒有讓我媽來,要她在家休養。我山東的表弟代表我舅舅一家來了。我爸一個老同事的女兒來了。
單位老干部處的一個工作人員來了,我和他閑聊幾句,他給我的印象是經常出現在這樣的場合,例行公事,熟能生巧,游刃有余。他遞給我幾張A4紙頭,上面復印了一面我爸生平。讓我看看有什么問題。我說謝謝,謝謝。問我們有什么要求。我說沒有沒有。因為我媽說了,從簡,隨便。我可是一個從業近三十年的老編輯了。第一行文字,就是一處硬傷。我爸三十一號去世。那紙頭上卻印著三十號去世。活活給我爸來了個提前一天執行。假如緩期一天,他們會不會寫上我爸在三月三十二日逝世?想到這里,我笑笑,再次表示謝意。我爸在國共兩黨監獄受難經歷,只字未提。其他訛誤也懶得糾正。隨便。
沈從文老人生前親口對我講,悼詞寫不出一個人的歷史,寫不出一個人的生活。
一切都應當忘記。我主張忘記。忘記那些骯臟的一團亂麻樣的破爛歷史,因為這樣的環境人生如同糞便,不值得品嘗分析。
現在是,我爸生前說過不回故鄉,也不要墳地。他隨意說過丟到海里。可是他和大海沒有絲毫關系。我們曾經議論過順馬桶沖掉,他笑出眼淚說不要不要,那也太那個了。現在,他還在家里,因為他住院后只想回家。可是不能總放在家里啊。他一生閱讀喜愛蒲松齡。那么好了,就把他送到青島嶗山去吧。
我們水泡的蒸發,將來總要在天庭相見。我們的鈣化物質,遲早會同地球一道粉碎。
責任編輯 宗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