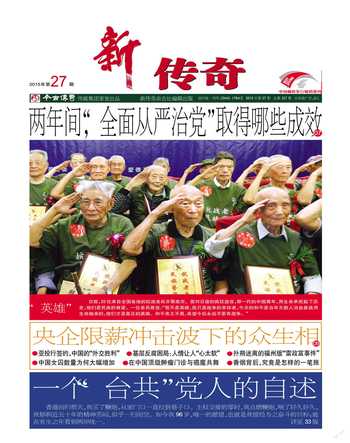在中國頂級腫瘤門診與癌魔共舞
信任與了解可能是當下醫院里最稀少和昂貴的東西,卻又是戰勝癌癥的必需品。在這個人類疾病史上最令人畏懼的魔鬼面前,這樣的必需品往往會影響病患對治療的選擇,進而決定他們生死的方向。
中國每天確診癌癥患者數近萬人,每分鐘約有6人被診斷為癌癥。這是最近數年的中國腫瘤年報顯示的數字,且還在繼續增長。據負責發布年報的“全國腫瘤”登記中心預計,到2020年,每年新增癌癥患病總數將達到660萬人。
提高患者生存率,有一系列問題待解,包括提高公共衛生水平。而對于個人,最重要的莫過于選擇正確的治療方式。了解腫瘤醫生的日常工作,知曉他們的行醫過程,或許可以讓許多站在腫瘤治療岔口的人們,不再徘徊。
中國的頂級腫瘤門診
根據復旦大學醫院管理所的一項排名,中國最好的5家腫瘤醫院集中在北上廣津。最近5年的“中國醫院最佳專科聲譽排行榜”腫瘤學專科排名中,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穩居第1名,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均入前5名。此外,還有上海的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廣州的中山大學腫瘤醫院,以及天津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榜單上的醫院幾乎和國際先進醫療技術達到同步——它們匯集了大陸腫瘤領域最優秀的醫生和最先進的治療手段。
“不敢說我們在所有腫瘤領域都是國內領先,但我們的消化道腫瘤,尤其是上消化道腫瘤,比如食管癌、胃癌的治療,絕不比其他發達國家差。所有各個方面,我們都沒有差距。”北大腫瘤醫院消化內科主任醫師張曉東告訴記者。能體現張曉東自信的,是北大腫瘤醫院消化內科的多學科綜合治療模式(簡稱MDT)。這是一種由臨床多個學科一起會診的工作模式。據中國結直腸腫瘤領域最富聲望的大夫之一顧晉介紹,在歐美發達國家,結直腸癌的治療已從單一的手術治療發展到多學科綜合治療。多學科包括外科醫師、內科醫生、放療科醫生和醫學影像科醫生,以及造口護士、病理學醫生,必要時還有婦科、胸外科醫生。
“這一模式是治療結直腸癌的最佳組合。多學科協作能確保讓腫瘤病人得到最佳方案的治療。”顧晉說,對付腫瘤往往需要采用多種治療手段,傳統的就診模式要求患者自己去不同科室就診。面對科室間治療方案的差異,患者往往無所適從。而MDT方便專家們相互協商,患者得到的是大家一致認同的診療方案。這種模式還可以涵蓋整個腫瘤的評估、各階段治療以及各種治療之間的銜接,避免專科醫師對其他專科知識更新不足帶來的局限。
不過,中國腫瘤治療也有現實因素,據2014年報道,在中國,由于地區間發展嚴重不平衡,用于癌癥病人的床位,城市里每千人有6.24張,而農村則只有2.8張。為了可以獲得更好的醫療設施,很多病人不得不跋涉到大城市看病,既延長了診斷和治療的時間,也增加了病人治療的自付費用。此外中國缺乏足夠的腫瘤專科醫生,也是中國癌癥治療的一個重要問題。
張曉東認為,中國大陸的腫瘤患者整體上很難得到規范的治療。北京協和醫院婦科腫瘤副教授劉海元也認為,涉及到醫生培訓,不同醫院的中國醫生水準亦有較大差異。“一些醫院的醫生缺乏這種長期培訓,很少有學術活動,醫生知識的更新就很差。病人也就沒法從中獲益。”
“雖然從2005年開始,衛生部、中華醫學會和中國抗癌協會就聯合制訂了《臨床診療指南——腫瘤分冊》,但普及工作卻是遠遠不夠。各地經濟、醫學發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即使了解規范,也很難推廣。”首都醫科大學肺癌診療中心主任支修益教授甚至直言,很多指南都成了醫生書架上的擺設、鎖在抽屜里的收藏品。
“晚期”癌癥有藥可醫
許多環境下,一旦一個人被診斷癌癥,就等于被判了死刑。這種宿命論的情緒,嚴重影響了癌癥的有效治療。
其實,近年來,新涌現的靶向藥物也不斷令癌癥患者獲益。支修益解釋,最近十年,對于癌癥,尤其肺癌的認識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癌癥不是一種疾病,而是由不同基因改變引起的一系列不同疾病。一些療效確切、毒副作用低的分子靶向藥物已經改變了肺癌的診療思維,顯著延長了患者的生存時間,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質量。
事實上,癌癥僅根據不同類型、部位就有100多個種類。每種癌癥的治療效果都是不同的。雖然仍有一部分癌癥,如胰腺癌,直到今天,治療仍然十分棘手。但相當多的癌癥已經能得到很好的控制,甚至一部分已經能達到治愈的效果。
“現代醫學認為,大部分晚期癌癥可以治療,放棄才是錯誤的,放棄正規治療去接受非主流療法,則是錯上加錯。”腫瘤科醫生“希波拉克底門徒”(網名)建議,腫瘤病人應該堅持走標準療法:手術、放療、化療。
“腫瘤的生物學行為太差,容易復發轉移。不知道誰可能得癌,誰能不能治好,”張曉東說,好的腫瘤醫生是在總的經驗基礎上,能夠結合最新的醫學知識,在最初治療的3個月到半年之間,比如觀察腫瘤病人對化療的反應,有效或無效,繼而判斷是否可能治好。是否能夠準確判斷病情,區分病人,這仰仗醫生的經驗,甚至有時會出現令醫生意外的奇跡。
對患者誠實可救命
在醫生田吉順的經驗中,最難的是與病人或者家屬溝通。“因為在他們的信念里,全都是關于癌癥負面的想法和信息,告訴他們診斷,只會引起更多不必要的擔心,從而帶來不良的結局。”盡管很大一部分癌癥可以得到治愈,但由于缺乏準確認知,人們往往容易陷入盲目的恐慌,影響心態和治療。因而在中國,很多癌癥病人的家屬向病患隱瞞了病情。
一位癌癥患者的家屬曾帶著病歷找到北京協和醫院婦科腫瘤領域的教授萬希潤。這是一例宮頸癌I期的中年女性患者。病人在外地醫院做了宮頸癌根治術及盆腔淋巴結切除術,保留了卵巢。這屬于宮頸癌I期患者的標準治療,符合治療指南。手術病理結果提示,淋巴結有轉移癌,按照治療指南應當予以放療。“但是,這位患者卻采用了并無循證依據的中藥化療。”萬希潤撰文記述下了這個病例,“之后,腫瘤復發——化療——各種毒副反應——無望,患者來到了協和。”萬希潤熟悉病歷上的外地醫院,也熟悉該院的幾位大夫。他心存疑問,一度怪罪到該院的大夫:都是搞腫瘤的,怎么可以如此不規范呢?他開始試圖斟詞酌句,告訴家屬有關患者的現狀和建議:“這種患者的治療,通常在我們醫院是要在術后進行放療的……”
然而,家屬打斷了他:“大夫是讓我們放療來著,我們怕病人受不了。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這病,我們告訴她是良性的。我們怕放療損害太大了,而且她會知道是惡性的,心情不好會加重病情。我們就沒同意放療。后來,有個病友說中藥HC素化療效果好,我們就去打了4個療程HC素”。
“這種家屬實在是太常見了。從看病的一開始,就想方設法瞞哄患者,讓患者對于自己的病情懵里懵懂,摒患者于自己的治療決策之外,慘忍地剝奪患者對于自己命運僅剩的些許把握。”萬希潤感嘆:“如果那位患者是知情的,能夠和醫生良好溝通,也許她會選擇符合循證的治療,也許其結局就將完全不同,起碼她可以自己選擇人生。”
告知癌癥病情是一項溝通技術活兒。萬希潤也認為,具體到病情告知上確實需要一定的技巧,要循序漸進,讓患者了解病情又不至于驚恐萬狀甚至完全悲觀絕望。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剝奪患者的知情權和決策權。患者不了解病情,更加難以配合抗腫瘤治療。
“逐漸地把壞消息傳遞給病人可能更有利于臨床的治療。健康的心理造成了康復的病人。”顧晉認為,“當人們坦然面對腫瘤的時候,原來的壓力就已經變成了戰勝腫瘤的動力了。”這一點得到了一些癌癥病人的認可。
當然,也會有無奈。每當門診碰到預判生存時間極為有限的病例,張曉東仍不得不建議病人家屬放棄進一步化療的念想。癌癥就是一個吃錢的怪物,沒完沒了,至死方休。考慮到病人家庭的經濟實力,對于一些普通家庭而言,避免過度治療,“在家休養”、“服用止痛藥物”似乎是更明智的選擇。
“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這是美國撒拉納克湖畔特魯多醫生的墓志銘上的一段話,很多中國的腫瘤醫生也喜歡引用這段銘言。人類對抗腫瘤的道路依舊漫長,即使重生的希望,也伴隨著痛苦艱難。因而幫助與安慰的價值常常超越了治療本身,帶去更多的動力和溫度。
(《鳳凰周刊》 2015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