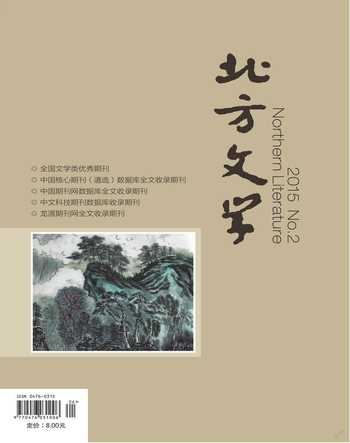淺析魯迅的父親情結與創作心態
摘 要:“父親情結”貫穿魯迅一生,他對父親既愛又恨,父親去世等童年遭遇影響到創作心態,堅定了他與傳統文化決裂的決心,使得“父親”這一意象有了更深層次的意義。
關鍵詞:魯迅;父親情結;創作心態
在魯迅的文本中,“父親”是一個若即若離的話題,他很少在作品中涉及自己父親,卻有意無意塑造出形貌不一的父親形象,并承擔起不同的文化內涵。究竟是怎樣的童年歷程導致了他言而半隱的敘述策略,影響到他的創作心態?
魯迅出生于紹興一個封建大家族,童年時其父周伯宜臥病不起,身為長子的他每天出入于藥鋪與當鋪之間,為父親的身體操勞,他在《<吶喊>自序》中寫道:
藥店的柜臺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污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
然而父親還是離去了,享年36歲。喪父之后家道衰敗讓幼小的魯迅飽受世態炎涼,“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1]于是他決定“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生”。早年喪父的經歷對魯迅后來的創作道路影響很大,成為他觀照傳統文化的窗口。他的作品中充滿對父親矛盾的情感:既愛也憎,既敬又怕。
魯迅對父親的愛主要定位于血緣關系的父子之愛,在《我的種痘》(1933年8月1日上海《文學》月刊)中他就曾寫道:
這一天,就舉行了種痘的儀式,堂屋中央擺了一張方桌子,系上紅桌帷,還點了香和蠟燭,我的父親抱了我,坐在桌旁邊……我所高興的是父親送了我兩樣可愛的玩具……一樣玩具是朱熹所謂“持其柄而搖之,則兩耳還自擊”的鼗鼓,最可愛的是另外的一樣,叫作“萬花筒”,是一個小小的長圓筒,外糊花紙,兩端嵌著玻璃,從孔子較小的一端向明一望,那可真是猗歟休哉……
時隔近50年,魯迅在回憶起他最初的種痘經歷時仍然歷歷在目,而父親送他的萬花筒也成為他心愛的玩物。在洋文化初傳中國,遭受國人抵制的那個時代,敢為風氣之先率先為愛子種痘的父親,思想之開明舐犢之情深,也可見一斑了。《我的第一個師父》也構成了魯迅對父回憶中相對溫暖的場景,“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養不大,不到一歲,便須到長慶寺去,拜了一個和尚為師了。”
然而魯迅表達對父親喜愛的文字較少,更多的是對父親的批判。在魯迅的文化體系中父親是父權文化的代表,要進行國民性批判就要反抗父親權威,而這一切是從對自己父親的批判開始的,收錄于《朝花夕拾》中的《五猖會》,寫出了魯迅的父親專制保守不近人情的一面:
“給我讀熟。背不出,就不準去看會。”
他說完,便站起來,走進房里去了。
我似乎從頭上澆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讀著,讀著,強記著,——而且要背出來。
逛廟會事件反映出父子態度差異,父親浸染封建傳統文化,他與魯迅形成了尖銳的“父子沖突”,這種代際文化鴻溝的形成是進入現代以來典型的文化心態,可以說新舊文化的沖突與變革不可避免。當父親的形象與舊文化相聯系起來,就更多的反映出魯迅對其“父”的憎惡之感,其實魯迅對父親的憎,是出于兩個立場,兩種文化的對立。歸根到底,是新文化與舊文化的對抗在家庭中的體現。
父親的去世還讓他看清了中醫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弊病,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父親的病》,似乎用更多的筆墨去暗諷為父親看病的那些昏庸中醫,久治未愈的父親在聆聽庸醫闡述之后更多的是無奈:
“我有一種丹,”有一回陳蓮河先生說,“點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見效。因為舌乃心之靈苗……價錢也并不貴,只要兩塊錢一盒……”
我父親沉思了一會,搖搖頭。
不能醫好父親,甚至不能讓他平靜地離去,父親去世就像一個咒語,讓魯迅背負著內疚捱過一生。李歐梵和日本學者竹內好都認為魯迅的創作是來自某種贖罪感,但魯迅在事情已過去二十五年以后選取這樣一種心理的角度來寫,本身就很有意義,說明父親的病和死一定向青年魯迅的頭腦里帶來他兒時世界的全部“黑暗力量”,從而促進了他的心理危機。[2]
魯迅對父親的回憶著重在他的疾病上,“久病”和“孱弱”是父親帶給魯迅最大的印象,而這樣的境遇與當時的中國國情不謀而合,封建儒家文化破爛不堪,淪為鉗制人們思想的枷鎖,積貧積弱的中國早已病入膏肓,回天乏術了。
父親去世對魯迅創作心態的影響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形成冷峻的性格與文風。因為父親的病死,魯迅奔走忙碌,飽受冷眼。他成年之后形成的潑辣犀利的文風,對敵人不留情面的嘲諷謾罵,與年少喪父過早接觸社會也有關。那時為救治父親家庭拮據幾乎到了舉債無門的地步,仰人鼻息艱難度日。正如魯迅自己所言:“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里,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3]李長之就看出:“從小康家庭而墮入困頓,當然要受不少的奚落和嘲諷,這也是使魯迅所受的印象特別深的。在他的作品里,幾乎常常是這樣的字:奚落,嘲諷,或者是一片哄笑。”[4]
第二,長子心態的形成。魯迅承擔起了父親去世后家里的重擔。對于兩個幼弟他亦父亦兄,對于寡母他極盡孝道。正如李歐梵所說,“魯迅作為家庭的長子,按照習俗,已經被置于一種負有責任的地位,被期望去完成祖、父輩的未竟之志而重振家聲。在父親死去之后,他更等于是充當了兩個弟弟的年輕父親角色。”[5]而孤兒寡母在宗法家族中被邊緣化,生存空間受到進一步擠壓,魯迅在父親去世后便遭到了族人的排擠,“父親去世后,魯迅就代表自己的一家和族中的十多戶人家議事。這些名分上是長輩的人們,常常譏諷和欺侮魯迅。有時候,當大家公議這一房中的重大事情時,往往逼著魯迅表態。”[6]這樣的人生體驗讓他看清人生的真面貌,也為其文學創作提供了人生閱歷情感體驗和理性反思等多方面支撐。
第三,洞察到包括中醫在內的封建文化的虛偽與脆弱。魯迅在對父亡的沉痛反思中把目光射向整個中國,由想醫好父親的病擴大至去醫好國民的苦痛。魯迅的學醫經歷也與父親疾病和死亡的深刻記憶有關,1904年魯迅前往仙臺學醫,學醫的目的很耐人尋味:“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7]而“幻燈片事件”則更讓他清醒,“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示出麻木的神情”“圍著的便是來鑒賞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8]。這深深刺傷了魯迅的心,他痛感國民性的愚昧,精神上的療救比身體上的要來得更緊迫,憤而棄醫從文,從醫治人的肉體走向醫治人的精神。
第四,文本中“疾病”隱喻的大量出現。魯迅作品中某些作為核心情節的“病”的描寫,這些都間接或直接地跟父親的肺病扯上關系。《藥》中對華小栓的描寫就是對“肺癆”的獨特表述“大粒的汗,從額上滾下,夾襖也帖住了脊心,兩塊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個洋文的‘八‘字”,“兩手按住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飯,泡上熱水,坐下便吃……吃的滿頭流汗,頭上都冒出蒸氣來”。《明天》中的寶兒“緋紅里帶一點青,熱,氣喘”也是肺炎的癥狀。《弟兄》中的弟弟是“猩紅熱”,它極易引起肺炎;《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到一個多月前,這才聽到他吐過幾回血,但似乎也沒有看醫生,后來就躺倒了;死去的前三天,就啞了喉嚨。”“也有人說有些生癆病死的人是要說不出話來”,由此可知,仍然是肺癆。并不是魯迅偏愛肺病,而是父親的病和年少的記憶對他影響太深,在文字上找到了排遣的出口,對中醫的厭惡、對父亡的執著、對生死的叩問,潛意識里已融化為情感體驗和創作素材。
對魯迅來說,“父親”是一個充滿痛苦與依戀、悲傷又排斥的復雜矛盾的意象。無論在價值理性上對父權文化的批判,還是在感性層面上對父親深沉的思念,父親情結都無比回避,這種獨特的心理體驗內化為魯迅的處世哲學,映射在文本中則有更為深沉的表達,并在潛意識中決定了他文本的基本走向,影響到他的創作心態。魯迅倡導的新文化運動多從家庭變革入手,這其中魯迅父親的影響不言而喻。
參考文獻:
[1][8]魯迅:《吶喊·自序》,漓江出版社,1999.
[2][5]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3]魯迅:《父親的病》,《朝花夕拾》,漓江出版社,2001.
[4]李長之:《魯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
[6]林非、劉再復:《魯迅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7]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作者簡介:高夢菲(1993-),女,濱州人,魯東大學文學院2011級本科生;秦彬(1983-),男,五蓮人,魯東大學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