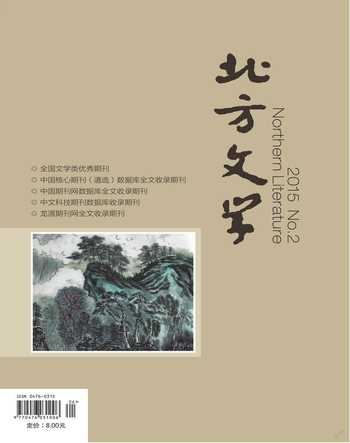延續(xù)苦難與溫情
摘 要:“苦難”與“溫情”是余華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的兩大母題,從最初的《十八歲出門遠(yuǎn)行》到最近的《第七天》,這兩大母題始終貫穿在余華的作品中。本文試圖從《第七天》尋找“苦難”與“溫情”的影子,分析《第七天》如何體現(xiàn)余華小說(shuō)的創(chuàng)作母題。
關(guān)鍵詞:苦難;溫情;創(chuàng)作母題;《第七天》
“苦難”與“溫情”的創(chuàng)作母題最早由夏忠義、富華提出:“不妨用兩個(gè)詞來(lái)指稱余華母題:‘苦難與‘溫情。縱觀新時(shí)期小說(shuō),委實(shí)沒有比余華更敏感于‘苦難中的溫情,也沒有比余華更神往乃至贊美‘溫情地受難的了。”[1]《第七天》中在延續(xù)了余華“苦難”與“溫情”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母題的同時(shí),又表現(xiàn)出一些與以往作品不一樣的地方。基于夏忠義教授對(duì)余華小說(shuō)創(chuàng)作母題的研究,結(jié)合余華以往的經(jīng)典作品,本文將從“苦難”和“溫情”兩個(gè)方面闡述《第七天》如何體現(xiàn)其小說(shuō)的創(chuàng)作母題,并分析《第七天》在表現(xiàn)這一問(wèn)題上與以往作品的異同。
一、苦難:不平等的現(xiàn)實(shí)
《第七天》以死者的視角來(lái)觀察生者的世界,使得本以苦難的世界倍顯殘酷和荒誕。在接受記者提問(wèn)時(shí),余華說(shuō):“《第七天》是我距離現(xiàn)實(shí)最近的一次寫作,以后可能不會(huì)這么近了,因?yàn)槲矣X得不會(huì)再找到這樣既近又遠(yuǎn)的方式。”《第七天》的確是余華“距離現(xiàn)實(shí)最近的一次寫作”,以致被許多批評(píng)者斥為“新聞串燒”,但是細(xì)細(xì)讀來(lái),無(wú)論是在對(duì)苦難的表現(xiàn)力度上,還是在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注度上,較之余華之前的作品,《第七天》在更深層次上揭示了底層民眾的苦難源自不平等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
《第七天》中的人物,抑或死于自殺,抑或死于事故,實(shí)際上,他們是死于絕望而無(wú)奈的不平的現(xiàn)實(shí)。與《活著》中的福貴相比,他們死得都太過(guò)“輕率”了,然而畢竟他們生活的時(shí)代已然不是福貴所生活的時(shí)代。這個(gè)時(shí)代有著更多的險(xiǎn)惡和不平等,他們無(wú)法“在苦難的極限處,在生與死的邊緣頑強(qiáng)的生存,善待生命”[2]。在這個(gè)世界上,人生而不平等,死后也不平等。在通往陰界入口處的殯儀館,連候燒大廳分都要為等級(jí)森嚴(yán)的兩個(gè)區(qū)域:由沙發(fā)圍成的貴賓候燒區(qū)和由塑料椅子排成的普通候燒區(qū)。那些沒有墓地、骨灰盒的絕對(duì)的貧困者,死后只能進(jìn)入“死無(wú)葬身之地”,在那里,他們享受到了絕對(duì)的平等。死者世界還有公平、自由、溫情,而生者世界(現(xiàn)實(shí)世界)則只剩殘酷、荒誕、苦難。“面對(duì)暴力與喧囂,文明只不過(guò)是一條標(biāo)語(yǔ),制度僅僅是裝飾品。”[3]面對(duì)殘酷的現(xiàn)實(shí),余華對(duì)文明和制度已經(jīng)不抱任何幻想,溫情也被排擠到世界的邊緣——“死無(wú)葬身之地”!
《第七天》對(duì)現(xiàn)實(shí)苦難的“人世之惡”表現(xiàn)的更加完整,它也回答了《許三觀賣血記》留給我們的困惑:底層民眾苦難源自不平等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從這個(gè)層面而言,《第七天》延續(xù)了余華“苦難”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母題。
二、溫情:遙遠(yuǎn)的烏托邦
不平等的現(xiàn)實(shí)世界令人痛苦,人們便把希望寄托于人性中的溫情,以為它能夠改變現(xiàn)實(shí)。然而它不僅沒有改變現(xiàn)實(shí),反而遭遇現(xiàn)實(shí)的阻擊。絕望之際,《第七天》虛構(gòu)了一個(gè)溫情美好的死者世界。“死亡葬身之地”則成為作者幻想中的烏托邦。
余華是這樣描述他的烏托邦的:那里沒有貧賤也沒有富貴,沒有悲傷也沒有疼痛,沒有仇也沒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他問(wèn):“那是什么地方?”我說(shuō):“死無(wú)葬身之地。”[4]“死無(wú)葬身之地”原意是孤魂野鬼的荒涼之地,余華變換語(yǔ)義,將其轉(zhuǎn)換為美好世界,一個(gè)人人死而平等的世界。這個(gè)世界與真實(shí)的世界之間隔著殯儀館,真實(shí)世界充滿著荒誕般的苦難,對(duì)活著的人來(lái)說(shuō),“烏托邦”是不可望也不可及的虛幻,大多數(shù)人死后會(huì)經(jīng)由殯儀館進(jìn)入“安息之地”,而只有一部分沒有墓地和骨灰盒的死者才會(huì)進(jìn)入“死無(wú)葬身之地”。所以說(shuō),那個(gè)充滿溫情的烏托邦世界只是一個(gè)遙遠(yuǎn)的“存在”。
綜觀余華的作品,無(wú)論是幻想中的烏托邦世界,還是充滿苦難的現(xiàn)實(shí)世界,都不乏對(duì)溫情的描寫。在最早的《十八歲出門遠(yuǎn)行》中,“溫情”是寒冷中得以安身的駕駛室。在《第七天》里,“溫情”是鼠妹在“死無(wú)葬身之地”得到的最后的關(guān)愛,這正是鼠妹在真實(shí)的世界所苦苦尋覓而不得的溫情。《第七天》的“溫情”敘寫一如既往的感傷溫暖,與“苦難”敘寫并行而成為貫穿小說(shuō)的另一條主線。個(gè)人認(rèn)為,余華在對(duì)“溫情”的表現(xiàn)上總是不及“苦難”表達(dá)的完整和深入,也許這與“余華曾癡迷暴力描寫”[5]有關(guān)。《第七天》中余華似乎試圖平衡兩者的表現(xiàn)力度,描繪了楊金彪與楊飛的父子之愛、鼠妹和伍超黨的戀人之情,但是總體看來(lái)“苦難”依舊大于“溫情”。
對(duì)“苦難”的殘酷雕琢,對(duì)“溫情”的心馳神往,不平等的現(xiàn)實(shí)令人絕望,遙遠(yuǎn)的烏托邦又無(wú)法企及,放縱苦難卻流入死亡,渴望溫情而難以得到:《第七天》延續(xù)著余華“苦難”與“溫情”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母題。雖然《第七天》有許多不足之處,但是在這個(gè)浮躁的商業(yè)化寫作的社會(huì),余華依然能夠關(guān)注“苦難”的社會(huì)和“苦難”社會(huì)里的底層民眾,并給予“溫情”地關(guān)照,這是《第七天》最有價(jià)值的地方。正如文章一開始提到的,余華稱“《第七天》是離現(xiàn)實(shí)最近的一次寫作”,因而其苦難也更接近真實(shí),溫情也更打動(dòng)人心。
注釋:
[1]夏中義、富華:《苦難中的溫情與溫情地受難——論余華小說(shuō)的母題演化》,《南方文壇》2001年第4期。
[2]王達(dá)敏:《一部關(guān)于平等的小說(shuō)——余華長(zhǎng)篇小說(shuō)〈第七天〉》,《揚(yáng)子江評(píng)論》2013年第4期。
[3]余華:《虛偽的作品》,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頁(yè)。
[4]余華:《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頁(yè)。
[5]陳曉明:《論〈在細(xì)雨中呼喊〉》,《文藝爭(zhēng)鳴:理論綜合版》2008年第2期。
作者簡(jiǎn)介:李云秀,黑龍江大學(xué)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