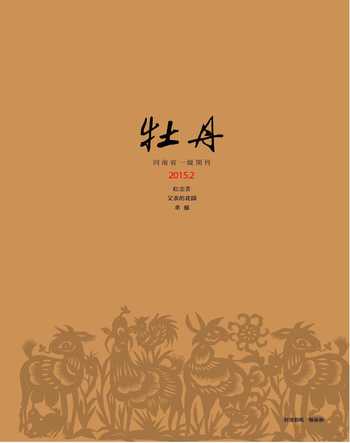存在之困與精神之殤
吳佳燕
《魔氣》是曹軍慶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與他素來擅寫的短篇小說中的冷峻、骨感、緊張相比,這部長篇多了一些從容的筆調、主體的情感和溫暖的底色。它有著廣闊的時間跨度——從1961年到2011年,而這五十年正是中國社會發生巨大震蕩與裂變的時期。然而,小說并沒用走慣常的宏大敘事之路,而是聚焦于湖北的一個小山村——煙燈村,寫它的閉塞與沖決,寫生活其中的不同人物的時代命運,以及一名身份不明的闖入者激起的層層波瀾。
是的,管素珍無疑是這篇小說最大的主角,她是不明身份的逃離者(本來應叫何紅梅,卻用管素珍的名字生活了大半輩子),她是從天而降的闖入者,她還是一個年輕貌美的瘋女人(魔氣)和小說中的一個重要視角。作為男性的作者對這個女人傾注了極大的情感,以致在文本中幾次跳出已有的第三人稱敘述視角,讓管素珍以第一人稱的方式發出自己“狂人日記”般的驚天囈語,或者清醒后平靜而有條理的理性回憶。在曹軍慶筆下,管素珍是美與善的化身,她有著豐沛的學養,有著驚人的生命力和生存本領,她的魔氣可以讓她親歷著卻游離于時代之外,她渾沌無知而又散發著讓周遭各懷心事的男人無法抗拒的魅力。她是串起一顆顆人、事之珠的一根線,同時也是一名偷窺者——因為“魔氣”這層面具,也許可以她讓洞穿諸多世事和人性的真相。這樣一個幾近完美的瘋女人寄寓著作者精神世界的諸多理想,也奠定了小說兩性關系的一個敘述基調:他是如此了解男人,而又不免美化著女人。相比曹軍慶以前小說中對待男女關系的陰郁與悲觀,性別視野中的《魔氣》多了一絲熱烈與溫情。
欲望纏身的男人
《魔氣》對鄉村社會的觀照是建立在一個個家族故事之上的。小說沒有像傳統的家族小說那樣向一個大家族內部進行縱深挖掘,而是以特定時空(五十年間的煙燈村)為切口,對王家、高家、劉家等一個個小單元家庭的內外關系展開盤根錯節的復雜敘述。而主導這樣一個以家庭結構為單位的基層社會的,是關乎幾個家庭的兩代男人。他們在治理或參與著這個小型社會各種活動的同時,又被自身的各種欲望深深纏繞。
小說中讓人印象深刻的首先是一群光棍漢。從湛結巴到王光忠、吳大福、高道安,這些大齡男人無邊的性苦悶令人吃驚。湛結巴40多歲了還沒有女人,好不容易從人販子那買來個女人,饑渴而兇猛的他竟然把原本打算好好過日子的女人嚇跑了;王光忠的解決方式是“搓”,以致當管素珍睡在旁邊的時候他首先做的也是“搓”而不是上女人的身;高道安的做法有些觸目驚心:往死里干活或在手臂扎針放血,他以這樣一種幾乎自虐的方式來緩解內心升騰的欲望;到了吳大福那里,就有些變態了,他解決的辦法是轉移,通過殘忍地展示殺狗來進行釋放。也許還應該有高義友。這個曾經的地主家長工在走狗屎運般與地主老婆通奸后,面對女人的離去和卷土重來的性苦悶,選擇的是以故意虐待他們親生兒子的方式來折磨彼此。也許還可以算上向海濤,這個被社會運動沖昏頭腦的公社干部,在對戀人提出進一步要求而不得的時候,竟然向對方暴露自己的下體表明自己的苦悶。也許先天的生理條件讓男人更容易被性欲纏繞,但是這些饑渴難耐的光棍漢們帶來的最重要的拷問是:為什么他們不能享受到應有的性權利和性資源?對于身處社會底層的他們而言,物質的貧困與生理的煎熬也許是互為因果的。
還有權力欲,對政治和權力的熱衷似乎是男人的本性。這種熱衷也體現在對煙燈村基層權力的追逐上。當上煙燈村村長可以說是劉勝利一生的夢想。這個過繼給殘缺的劉駝子夫婦并改名換姓的男人一生都深陷于自卑與自尊交織的泥潭:“既然你們都瞧不起我,我偏要做個狠人給你們瞧瞧。”他要通過這種權力欲的滿足來獲得一種嶄新的身份認同,以此厭棄讓他感到不堪的養父母,蔑視那些不把他放在眼里的人。以及慰藉從管素珍那里感受到的愛而無望的挫敗感。在這里,極富象征意義的是他隨身攜帶的賬本。它可以用來記賬、記工分、記事件,也可以用來記隱私、把柄、污點,它是權力的象征,是切割人心的軟刀子,讓人敬畏恐懼,也讓人人自危。劉勝利愈是切身感受到賬本帶給他的諸多好處,想要統治煙燈村的欲望就愈強烈,即便自己最終未能如愿,也要讓兒子完成自己的心愿。當劉勝利處心積慮地讓兒子看他制造的搜查現場對其進行政治啟蒙,并設計讓他沒考上大學時,我們看到的已經不是一名父親,而是一個完全被權力異化的人。
另一個被權力異化的人是向海濤。這個曾經單純熱烈、滿口誓言的師范生,在當了公社干部以后,社會運動的裹挾以及對權力的迷戀把他蛻變成一個六親不認、不擇手段往上爬的狂熱之徒。如果說之前在管素珍面前的暴露只是出于男人的性本能的話,那么當他得知管素珍寫信檢舉他在饑餓年代的不當做法后,把管素珍打倒在地并對著她暴露、撒尿的時候,這種赤裸裸的侮辱之舉完全宣告了他對愛情的決絕和與權力的茍合。雖然這多少有點外強中干,但只有把事情做絕,他才能獲得一種政治上安全感——而在權力斗爭中,只有當你不再愛了、不再仁慈的時候,你才可能強大,成為最終的贏家。與之相反的是另外一個公社干部黃冬明。這個對管素珍一見鐘情、始知情為何物的男人一邊暗自驚嘆歡喜,一邊尋找著合適的機會跟這個女人接近。遺憾的是,在為管素珍外出治病的長沙之行中,黃冬明精心策劃著想跟這個女人好好談一場戀愛,結果卻淪落為一出可笑的強奸未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黃冬明因為對這個“魔氣”女人的愛意導致他在仕途的一路失意——這種冥冥之中的對比,是命運的無常,還是對時代的指涉?
這種理論同樣可以在劉如虎身上驗證。當從部隊回來的劉如虎在教室里向王子紅示愛遭到羞辱之后,放棄愛情的他娶了自己最討厭的女人。憑著這種無情和狠勁,他子承父愿當上了煙燈村的村長,在新的時代中變得更加貪婪無恥并且如魚得水。自小在父親的啟蒙下熟諳各種斗爭法則和社會規則的劉如虎,一方面把鄉村的城鎮化建設搞得風生水起,令王光忠這樣的忠厚善良的長輩和前任都感到佩服,另一方面又中飽私囊,個人生活過得無比墮落與奢侈。這時候的劉如虎,已經如同一具被物化的行尸走肉。
當然,除了性欲、權力欲、物欲的相互撕咬與糾結,小說中還有不少普通男人,跟所有的老百姓一樣,在動亂年代、饑荒年代還要飽受著食欲之苦,連最起碼的生存需要都無法滿足。我們要深思的是,這些被欲望纏身的男人,他們的痛苦是如何造成的?是男人的本性,外在的施壓,還是歷史時代的使然?好的時代是可以激發人性之善的,而惡的時代也會把人性之惡誘發得無以復加。
難以救贖的女人
如果說曹軍慶在《魔氣》中對于男人更多的是關注他們的下半身,對于他們的欲望和困境有著深刻的理解與悲憫;那么,對于女人,他則只止于上半身,對她們有著美好的期待和智性的表述。這種策略也許可以觸摸到作者的一絲寫作理想:他想讓女人來安撫或拯救困境中的男人。
小說中的大多數女性有著美好善良的一面。管素珍自不必說,她的美麗高潔及文化涵養讓她可以在時代動蕩中出淤泥而不染;終年囚居暗室的白毛婆婆雖然雙目失明,但是能夠洞悉世事、明察事理,并且她的故事屋里有著恢弘的想象和生活的智慧,長年的冥思與孤獨讓目不識丁的她也可以抵達思想與真理的某些深處;即便是當過“破鞋”的賈文翠,也有著墮落之后的清醒與澄明,可以用草藥為村人行醫;真正的管素珍雖然背叛了何紅梅的友情,她的選擇是受到了愛情、恐懼與欲望的多重擠壓,似乎也有著身不由己可以理解之處。而對于王子紅,為了尋找一個好的棲身之所,她一直在理性地選擇,堅強地活著,只不過命運對她的青睞太少而已。
小說涉及不少偷情故事,然而曹軍慶并沒有對其進行單純地道德評判,在他筆下,偷情并不顯得多么不齒或不堪,它看上去也可以是一件自然而然發生的、還有些許美好的事情。這一方面由復雜的人性使然:余小芬的喝藥自殺不是源于肚子的饑餓,而是因為害怕東窗事發再也享受不到偷情的快樂;原來的管素珍與向海濤的偷情是因為“她在性里面不光有懼怕,不光有報恩,同時還有背叛的快樂。背叛是一種邪惡的快樂”;另一方面,對于那些壓抑的光棍漢而言,偷情是舒緩他們生理情緒的最佳出口。
所以,雖然《魔氣》中的男人對女人其實都有不同程度生理或精神上的強奸、壓迫,但是它也實現了女人對男人的安撫或慰藉。如王光忠撿著了管素珍;管素珍在月夜夢游中與高道安發生關系并誕下一子;吳大福與匡有元的老婆偷情后與弟妹私奔;余德發與夏光平老婆柳不煙偷情;地主婆肖桂花與高義友同居并育有一子……作者以這種出軌乃至亂倫的畸形方式給飽受煎熬的底層男人一絲撫慰,有的還可以藉此延續香火,目的是維持鄉村性資源和生命力的相對平衡,并讓人從中獲得某種拯救或歸屬感。
還有一些溫暖的場面和美好的東西。劉駝子和白毛婆婆雖然都是殘缺之人,但一輩子恩愛和睦,劉駝子死后,白毛婆婆收拾好跟丈夫穿在同一件衣褲里面,坦然赴死;王光忠為了給裸身夢游的管素珍祛邪,用桃枝在她身上抽出一朵朵艷麗的桃花;還有楊店半樹花開半樹枯的神奇桃樹以及與之相關的癡男怨女的凄美傳說,都為小說中的女性和男女關系披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
然而,這些女人不但拯救不了男人,連她們自身都難以救贖。管素珍逃離了愛情與友情的背叛現場,闖入作為避難所的煙燈村后,常常被視為一個異類,有劉勝利的加害,光棍漢的覬覦,而王光忠一輩子都想治好她的病卻只能抱憾而終;管素珍在夫喪子亡、這個家快要塌下來的時候不得已清醒過來進行支撐;白毛婆婆與劉駝子恩愛一生卻沒有子嗣,深明事理的她也有著濃郁的香火觀念,結果雖然有了兒孫卻要承受兒子帶給她的更多的精神痛苦;賈文翠雖然后來從良從醫,但是再也不能擁有自己的孩子;私生子高道文的小兒麻痹癥和偷偷摸摸的母子相會讓肖桂花一生都在困擾和贖罪;要強的王子紅為了過上一種體面而富裕的生活舍棄了愛情與親情,兜兜轉轉仍是白忙一場、難逃命運的捉弄。她們的難以救贖,一方面來自男權社會的不同壓迫和自身弱點,另一方面來自歷史時代對人的命運的深重影響。所以,她們是美的化身,她們是被寄予厚望的拯救者,但她們也是置身其中的受害者,是作者遙遠而空洞的幻想。
生而為人的困與殤
中國人歷來是相信因果報應的,在農村尤甚,近乎一種樸素的信仰。這種信仰可以讓他們在生活中為了積德或對惡果的恐懼而多多行善。這為小說中發生的一些詭異的事情提供了依據:如秦忠義因放牛時在白龍寺對著菩薩撒尿而得了怪病,只能爬行,鬧饑荒時吃一根黃瓜即將嗆死時卻可以站立起來了;銀杏古樹對湛結巴女人的庇護和多年后女人歸來的守候;劉駝子一生駝背,死了之后背卻神奇地變直了;管素珍魔氣了近五十年,突然在家庭需要她的時候不治自愈;劉勝利晚年散財行善,對兒子的成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這樣一種冥冥之中的自有安排昭示著人的生而有罪,應該對自然神靈葆有敬畏之心,而死亡是人獲得解脫和救贖的重要途徑。所以,王光忠和劉勝利這對基層的“政敵”,管素珍和王子紅這對母女的隔膜,因為王光忠的死亡達成了一種和解。
但是到了劉如虎執掌的21世紀的煙燈村,這種樸素的信仰不但沒被現實所驗證,還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觀念。正如小說中所說:“因果報應就是一個創口貼,對指頭上破點皮、出點血這類事它管用。對內臟和腦子里大出血、大手術,創口貼一點也派不上用場。”劉如虎以非正常手段對權力與財富的掌控正起著一種不良的示范效應,外表光鮮的鄉村包裹著日益衰敗的內核。時代在變,價值觀念也在變,但一些惡質化的東西卻與文革時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檢舉、揭短、告密,捉人之柄要挾其人,這些慣用的伎倆,在向海濤、劉勝利與高道文身上,在劉勝利與劉如虎之間,你會發現兩個不同的時代有著相通的惡疾,兩代人也有著共同的人性弱點。所以,魔氣的管素珍在五十年后清醒過來,發現她所處的世界跟她瘋之前的世界并沒有多少改變。她依然貧困,她的子輩孫輩也并沒有因為時代的前進獲得一個好的歸宿,一如大多數農民的命運;她依然有諸多看不懂,她依然只能眼睜睜看著。也許,面對一個個時代的魔氣,只有自身成為魔氣,才能保全自我。
見證時代變遷的,除了管素珍這雙魔氣的眼睛,還有一棵銀杏樹。這棵千年古樹在這五十年間猶如圖騰一樣折射出人們性觀念的演變,以及欲望與精神的糾結。先是代表著一種傳統的香火觀念與生殖崇拜,被湛結巴的母親燒香叩拜,希望可以為兒子找到一位女人延續子嗣;再是意味著對女性的庇佑和拯救——讓湛結巴的女人可以逃出他的性壓迫;接著是女人的歸來與守候,喻示對神靈的敬畏;后來是旅游開發后現代人的膜拜,折射出現代人原始生命力的衰敗;然而,最后,銀杏樹死了,這意味著人的最后一根精神稻草的倒塌,好的文化在現代一些惡質的侵蝕下,傳不下去了,人成了精神上的光棍漢與絕戶頭。
所以,小說首先反思的是五十年間的歷史與時代。當高道文喜歡寫作維持不了生計而靠寫匿名信、訴狀和家譜可以活得有滋有味的時候,我們可以感受到歷史的荒誕與反復,原來現實的制造者與歷史的敘述者都是那么隨意而荒誕不經。管素珍其實是何紅梅,她用仇人的名字生活了大半輩子,而何紅梅這個名字又被她賜給了自己的孫女。在時代的風云更迭與人的代際承傳中,究竟有哪些東西在消逝,哪些東西在生長?而保留下來的,哪些是優質的遺產,哪些是沖刷不掉的惡質的痼疾?這是每一個時代中人都要思考和分辨的問題。
小說最終指向的是人的存在之困與精神之殤,指向的是時代與人性雙重夾擊中人的精神疑難。人活著會有多難?有生存環境的制約,有自身欲望的糾纏,更何況它加諸的是轉型期社會分化中最底層的那一群,生而為人的悲劇性存在會更為濃烈。曹軍慶曾稱這部小說是他對以前鄉土寫作的總結,對自己童年生活的回望,無怪乎《魔氣》中會有一些美好的、溫暖的回憶、想象與寄寓。這種總結與回望更像是一種告別與憑吊,鄉村的兩性世界構筑的是半個世紀以來底層人的生存圖景與精神困境,除了少許劉如虎們享受著官商同謀后的優裕與空虛,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正默默承受著身與心的雙重折磨。作者投射其上的悲憫深切而又憂心忡忡的目光,就如管素珍注目下的那棵銀杏樹,明知道它有被困死掉的危險卻又只能眼睜睜地看著。
責任編輯 婧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