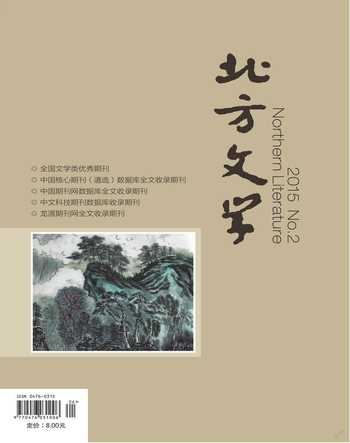同性戀題材電影中的性角色及其權(quán)力關(guān)系
上世紀(jì)七十年代伊始,同性戀題材的電影被華人導(dǎo)演陸續(xù)搬上熒幕,從早期楚原導(dǎo)演的奇情武俠片《愛奴》,到九十年代初期的《喜宴》和《霸王別姬》,再到第六代導(dǎo)演張元的《東宮西宮》和千禧年后李安導(dǎo)演的又一力作《斷背山》,在不停流轉(zhuǎn)的時代背景下,導(dǎo)演們以一個同性戀者的心態(tài),用不同的敘事手法去創(chuàng)作和演繹,讓這一特殊題材不斷的沖擊著我們的視野。
1996年,關(guān)錦鵬應(yīng)英國電影學(xué)會邀請,制作了紀(jì)念世界電影一百周年的紀(jì)錄片《男生女相:中國導(dǎo)演之性別》,并借此片向媒體非正式的公開了他的同性戀身份。在一次采訪中,他對這部影片的意義做了這樣的闡釋:“它變成了我自己現(xiàn)身說法的一部作品,對我來講,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為如果性取向這個東西都可以不避諱,那么我自己的創(chuàng)作也就沒有什么包袱了。”此后,關(guān)錦鵬逐漸把對女性電影的關(guān)注,轉(zhuǎn)移和參與到同性戀題材電影的創(chuàng)作中來。1998年的情人節(jié),他的新片《愈快樂愈墮落》在香港舉行首映,關(guān)錦鵬同時正式向外界公布了自己的“同志”身份,而該片也是關(guān)錦鵬不再借女性題材的作品,進行隱秘的身份認(rèn)同后,首次對同性戀題材的嘗試。它講述了幾對關(guān)系錯綜復(fù)雜的同性戀、異性戀和雙性戀企圖用肉體的放縱來解決自己心靈的饑渴,卻因此陷入了更加迷茫困惑的境地的故事。如果說在這部電影中導(dǎo)演對主人公的同性戀意識的描寫還是曖昧的、模糊的,那么時隔三年后的男同影片《藍(lán)宇》中的主人公,則是在經(jīng)歷了一系列的現(xiàn)實阻礙后,最終得以坦然面對自己的同性取向和情感。這部以網(wǎng)絡(luò)小說《北京故事》為藍(lán)本改編的影片描寫了北京富商捍東和貧困的大學(xué)生藍(lán)宇,由一夜情的相識發(fā)展到患難與共時的相愛,最終卻以悲劇結(jié)尾的故事。由于片中涉及大尺度的裸露鏡頭和導(dǎo)演對同性戀者間真摯愛情的直白表現(xiàn),使影片在上映后引起一片嘩然,也正因為關(guān)錦鵬試圖以同性戀者間的真愛來打動觀眾,突破了傳統(tǒng)同性戀題材的敘事表達(dá),在當(dāng)年臺灣電影金馬獎上一舉斬獲包括最佳導(dǎo)演獎在內(nèi)的五項大獎。
誠然,關(guān)錦鵬自己的“同志”身份,是他在執(zhí)導(dǎo)這部影片時與生俱來的優(yōu)勢,他可以將更多個人的情感經(jīng)驗加入影片中,增加情節(jié)的張力,讓人物更為鮮活,甚至可以把這種不符合主流價值觀的同性之愛,升華為無性別之見的共性情感,從而水到渠成的詮釋同性間的美好愛情。但是,在同性間的美好愛情背后,往往易被人們忽視的就是同性戀之間的性角色(sexual role)[1],它不同于性別角色(gender role)[2],以《藍(lán)宇》為例,捍東和藍(lán)宇的性別角色均為男性,但是在他們的同性性行為中,捍東的性角色是男性,而藍(lán)宇的性角色是女性,從影片開篇,導(dǎo)演便通過鏡頭語言、場面調(diào)度以及人物的表演,確立他們的性角色,為同性性關(guān)系的進一步發(fā)展和確立做好鋪墊。黑白色調(diào)的人物開場將時空倒敘,鏡像中呈現(xiàn)出一群地道的北京高干子弟,玩世不恭的說著京腔十足的北京話。兩極鏡頭的景別轉(zhuǎn)換,畫面由主人公的近景拉出,室內(nèi)的暗調(diào)氛圍通過微揚的多人鏡頭的調(diào)度,強化了奢糜生活的昏暗和主人公略有權(quán)勢的身份地位。在同服務(wù)生對話時,高大健碩的捍東位于畫面前景的暗光區(qū),導(dǎo)演運用過肩鏡頭從他的肩背借位俯拍,使得后景的服務(wù)生矮小干瘦,而這種隱喻性的框中框構(gòu)圖在引導(dǎo)受眾去看身份地位渺小的服務(wù)生的同時,也是對捍東這一有家世背景的“官二代”形象的反襯。經(jīng)發(fā)小劉征的介紹,捍東認(rèn)識了在京讀書的東北大學(xué)生藍(lán)宇,劉征作為這個故事的引發(fā)者,他藍(lán)色的衣著鋪墊了繼之而來的藍(lán)色悲情。藍(lán)宇在臺球廳的這場戲中并沒有真正出現(xiàn),他是一個弱小的人物,無論是在劉征口中,還是在捍東眼里,以及影像的交代中都是弱小的。當(dāng)鏡頭特寫一張滿眼寫著理想,卻迫于無奈向現(xiàn)實妥協(xié)的臉孔時,一檔正在介紹美國的電視節(jié)目,清楚的交代了鏡頭前的藍(lán)宇,迫于對理想的渴求,不得已通過出賣自己的肉體,來換取金錢的原因。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性被賦予了兩種意義,分別是生育和娛樂,顯然,同性戀的生理特征使得性賦予的生育意義無法完成,因此這場出于金錢關(guān)系而發(fā)生的性交易,只是以捍東的娛樂為目的的。鏡頭由藍(lán)宇的面部特寫跳切至全景,身著黃色襯衣的藍(lán)宇坐在以藍(lán)色墻壁的浴室為背景的畫面中,色相上的反差立刻產(chǎn)生一種神秘未知的緊張感。此時,下半身裹著藍(lán)色浴巾的捍東從浴室走出,藍(lán)色被編碼為充滿情色意味的性暗示符號[3],藍(lán)宇躺在藍(lán)色的床上,就像于藍(lán)色中情不自禁和無法自拔,屋內(nèi)兩盞黃光的臺燈在大面積藍(lán)調(diào)的包裹下格外微弱,這微弱的光恰好映照在藍(lán)宇的臉頰上,而坐在床尾抽煙的捍東儼然一副同性關(guān)系中的男性角色,到此,導(dǎo)演完成了這對非情感性的同性性行為在影像上的性角色的確立。然而,第二次藍(lán)宇和捍東在春節(jié)前的街頭偶遇,卻使得單純的同性性行為發(fā)生了向同性戀者身份認(rèn)同的轉(zhuǎn)向。“昨天剛好四個月……”從藍(lán)宇脫口而出的這句話中,可以感受到這個人物的細(xì)膩,也只有正在在乎一個人,才會把日子算得這么清楚。捍東看藍(lán)宇衣著單薄,便將自己的圍巾替藍(lán)宇套上,導(dǎo)演一連用了五六個鏡頭來切換這個動作,圍巾在這里是情感與社會的枷鎖的象征,誰也無法擺脫,誰也不能擺脫,藍(lán)宇從這一刻起初步確認(rèn)了自己的感情,并認(rèn)識到自己當(dāng)初不是為了金錢而跟捍東發(fā)生關(guān)系,這一夜他們重溫了初夜的激情。隔日,捍東請藍(lán)宇到一間日式料理店用餐,藍(lán)宇坦露了自己對捍東的愛是情不自禁的,畫面中藍(lán)宇身后的那面墻是隔開了兩位主人公與其他食客的精神世界、價值觀和與眾不同的同性關(guān)系的屏障。但捍東并不承認(rèn)他們之間的感情,在車上,他對藍(lán)宇說“玩這個的不能太熟悉了,否則就散了”,藍(lán)宇急切的反問“我們還不是太熟吧”,可見,藍(lán)宇在精神上對捍東的依賴,就像一個依附于男人臂膀下的小女人,無條件的順從。可是,捍東依然依仗著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經(jīng)濟能力,習(xí)慣于同性間的性行為的玩樂中。
直到1989年,一個權(quán)力受到質(zhì)疑和反抗的年頭,捍東才真正放棄自己的強者姿態(tài)。他開車前往廣場,在所有人慌張亂跑時,在晃動的自行車和手牽著手的人堆中間,和藍(lán)宇終于確認(rèn)了彼此間曖昧不清的關(guān)系。可平靜而快樂的日子并不長久,當(dāng)同志間的玩弄變?yōu)檎嬲膼矍椋伺c人之間的身份達(dá)到了一種統(tǒng)一的時候,社會的力量又開始阻撓兩人的關(guān)系。林靜平的出現(xiàn),讓捍東覺得自己是可以讓女人幸福的男人,便決定回歸正常的性別角色,做符合社會主流期待的事,和靜平在眾人的祝福聲中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可是靜平有別于中國傳統(tǒng)女性對男人的依附,十足獨立的女強人氣場,消解了柔弱的女性特質(zhì)。畫面中的靜平總是位于前景處的光區(qū)位置,同背對著鏡頭、穿著深藍(lán)色睡衣的捍東,構(gòu)成女強男弱的家庭地位,這意味著捍東在靜平面前的話語權(quán)的頓然消失。靜平每晚敷著面膜,照著鏡子,彷佛面膜成了面具,它象征著變化與隔閡,暗示靜平內(nèi)心的矛盾正在逐漸放大。鏡像的運用,也表明了兩人關(guān)系的疏遠(yuǎn),如同鏡中花、水中月,走向離婚的結(jié)局是難以逃脫的。美國女性主義者凱特·米利特在她的博士論文中提出“性政治”這一概念,“性政治”中的“政治”,是指一群人可用于支配另一群人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和組合,而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開會或者選舉。凱特認(rèn)為男女之間的這種性別關(guān)系在父權(quán)制社會和文化背景下,是由男性對女性實行全面控制與支配的,這種全面控制與支配在本質(zhì)上與不同種族或階層間的控制與支配并無差別。所以,如果我們把種族或階層間的關(guān)系稱為一種政治關(guān)系,那么凱特便認(rèn)為,性別關(guān)系同樣也是一種政治關(guān)系。既然在傳統(tǒng)的兩性關(guān)系中,也存在這樣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并且以男性是權(quán)力的掌控者,女性是受控制與支配的群體這樣的定式,使兩性關(guān)系得以長期穩(wěn)固,那么,捍東和靜平的婚姻之所以無法維持下去便也有了最好的注解。經(jīng)歷了一場三年的婚姻生活后,捍東開始意識到了自己真正的性取向和感情的歸屬。
再次遇見藍(lán)宇是在飛機的停車場,此時的藍(lán)宇已經(jīng)是一個成熟的男性,而捍東的父親剛?cè)ナ啦痪茫?jīng)作為高干子弟的捍東已無任何靠山了,即便從捍東的身上無利可圖,他還是義無反顧的愛著這個男人。在捍東遭受婚姻的打擊后,藍(lán)宇就像一副療傷的藥,兩人舊情復(fù)燃,一再反復(fù)的讓兩人的關(guān)系像彈簧般伸縮變化。捍東的公司因涉嫌非法走私被調(diào)查,他本人被拘捕,在被捕前捍東幫藍(lán)宇辦好了去美國的護照,而藍(lán)宇卻不假思索的放棄了出國讀書的夢想。原本他是為金錢而出賣身體,現(xiàn)在轉(zhuǎn)而為愛情而放棄理想,導(dǎo)演似乎想將藍(lán)宇單純的愛塑造到極值。他賣掉了捍東送給自己的豪宅、再加上自己多年的積蓄和捍東其他親戚朋友的幫忙,一起把捍東從獄里弄了出來。出獄后的第一頓飯是在家里,藍(lán)宇起初并沒有在飯桌上聊著天、劃著拳、等著上菜,而是和捍東的妹妹在廚房忙活,可以看出他的身上具有女性這一欲望客體的存在。飯桌上,藍(lán)宇深情的凝視著捍東,像女人般愛憐的目光中透出一絲欣慰。一夜的纏綿過后,是一段捍東的畫外音“你知道嗎?在獄中的這幾個月里,我終于弄明白了一件事情,我跟你是天生注定得走在一起的”。至此,完成了對自我是同性戀者身份的認(rèn)同。畫面中,捍東和藍(lán)宇正在共浴,導(dǎo)演從門縫間拍攝兩人的狀態(tài)時,始終是被擠壓的,這也暗示著他們的同性關(guān)系是為社會所排斥和不允許的,戀情是處于夾縫求生的狀態(tài),是岌岌可危的,深藍(lán)色的門框是悲情元素的蔓延。又是一個寒冬的早晨,這也是藍(lán)宇最后一次離開家,關(guān)門時,門后出現(xiàn)了一個畫框,是曾經(jīng)那棟別墅的照片,同當(dāng)年他們第一次看房時相擁的場景一樣,在上一次的分手中,閃回了這個畫面,而再次出現(xiàn)這張照片,無疑是對兩人再度分離的預(yù)示。捍東在接到藍(lán)宇意外死亡的電話時,百葉窗前的剪影效果,低落和難以言表的悲傷瞬間涌出,窗外的光線照不進捍東的辦公室,更照不進他的心里,他完全處在一個孤立無助、悲慟欲絕的黑洞里。記得他們在搬進新房時,捍東曾說“毛主席去世時,自己哭了個稀里嘩啦,就連自己的父親去世時也沒流過這么多眼淚”,然而站在藍(lán)宇冰冷的尸體前,他卻歇斯底里的哭了。
同性戀面對社會主流文化的壓力和排擠,始終是無根的、漂泊的,而藍(lán)宇作為同性戀關(guān)系中的女性角色的象征,他的死似乎也是對性政治男女權(quán)力關(guān)系中,受壓迫與支配的女性有某種程度上的契合。關(guān)錦鵬導(dǎo)演借同性戀題材分別講了三件事:其一,盡管同性戀和異性戀的本質(zhì)都是愛情,但在異性戀為主導(dǎo)的價值觀的社會中,同性戀需要承受更大的社會風(fēng)險,處于更敵對的環(huán)境中;其二,男同性戀關(guān)系中,扮演女性角色的一方,同異性戀中的女性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會面對男性對女性/女性角色的絕對掌控和支配的局面,在影片《藍(lán)宇》,靜平雖然是以女強人的形象出現(xiàn)的,但離婚的事實表明,因為她沒有遵守兩性關(guān)系中固有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所以才無法擁有完美的婚姻,所以離婚對她而言,并不意味著女權(quán)主義者的勝利,真正的勝利者,是存在于兩性關(guān)系中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其三,同性戀影像生產(chǎn)的性快感從表面上解構(gòu)了異性戀這一男女兩分的性別結(jié)構(gòu),打破了主流電影中,女性作為被觀看的客體,讓男性取而代之成為欲望對象的展現(xiàn),但其實質(zhì)仍然是對男同性行為關(guān)系中人物所扮演的性角色的投射,并非該人物的性別角色,換言之,受眾在觀影過程中,享受的不是該人物作為性別角色(男性),而是該人物的性角色(女性)所帶來的視聽快感,可見,其本源還是傳統(tǒng)看與被看關(guān)系中對女性/女性身體的凝視。
“每次路過你出事的地方,我都會停下來,但是心里卻很平靜,因為總覺得你根本就沒有走”,捍東從車窗向外望去,工地上破破爛爛的藍(lán)色鐵皮護板隨著車速的加快,如同閃爍的電影膠片般,一格一格的流過,逐漸形成了一種連續(xù)的影像,一段留痕的回憶。
注釋:
[1]注釋:性角色是指個體在性行為中扮演的某種行為角色。
[2]注釋:性別角色是指社會公認(rèn)的某一性別應(yīng)具有的行為與心理特征。
[3]注釋:藍(lán)宇與同性戀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紀(jì)五十年代,現(xiàn)在的俄語俚語中,同性戀是用“藍(lán)色”(blue)來表示的。
參考文獻(xiàn):
[1]孫慰川,《關(guān)錦鵬的電影世界》[J],《電影新作》,2002年。
[2]黑格爾著,朱光潛譯,《美學(xué)》,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3年。
[3]焦雄屏,《男生女相:中國電影之性別——關(guān)錦鵬個人影史的投射》,《映像中國》,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
[4]張美君,《關(guān)錦鵬的光影記憶》,香港三聯(lián)書店,2007年。
作者簡介:郜杏,香港中文大學(xué)研究生院文宗系視覺文化專業(yè)在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