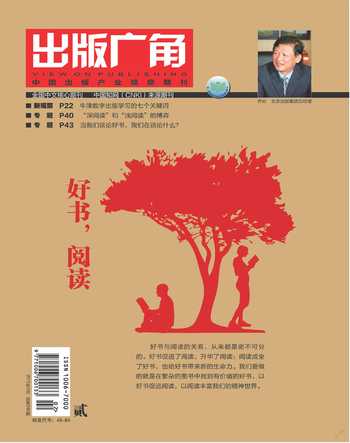“深閱讀”和“淺閱讀”的博弈
劉云霞
我們不得不承認“淺閱讀”的發展適合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我們需要做的應該是如何正確理解“淺閱讀”的概念,以及在“淺閱讀”中如何造就“深閱讀”的生存空間。
在全媒體時代下,平面媒體與網絡媒體、手機媒體等相互融合,使得各種傳媒力量形成合力,多平臺、多落點、多形態的傳播格局形成,這些條件為“淺閱讀”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平臺。“淺閱讀”最大的特征就是讓讀者在工作間隙期吸取海量的信息,用快速、簡潔、便捷、隨意、概要等方式閱讀,這種閱讀方式儼然成為閱讀的主流形態。
一場有關“深閱讀”和“淺閱讀”的舌戰,曾經在網絡上鬧得沸沸揚揚,隨著時間推移,這場爭論沒有一個真正的結果。隨著數字閱讀的普及化,“淺閱讀”的潮流更加猛烈。在當今社會中,更多人已經習慣在排隊、坐車的時候使用平板電腦、手機隨意、隨時、便捷地閱讀,甚至連那些經典的文化也通過“淺閱讀”的推廣路線走入大眾群體。例如,《百家講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各路學者用自己簡單的理解方式,將中華五千年的文化進行篩選解讀。這樣加工過的經典文化,通過大眾化的傳播方式,更容易被普通群眾接受。在這樣的事實面前,我們不得不承認“淺閱讀”的發展適合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我們需要做的應該是如何正確理解“淺閱讀”的概念,以及在“淺閱讀”中如何造就“深閱讀”的生存空間。
一、“淺閱讀”的生存空間有多大?
隨著數字出版產業的快速發展,利用電子閱讀工具進行閱讀成為“淺閱讀”的主要方式。傳統閱讀的堅守者總是覺得“淺閱讀”存在不需要思考、跳躍式的閱讀沒法記憶等缺陷,但是在社會物質轉變、人們生活壓力劇增、精神生活改變等種種因素影響下,“淺閱讀”對社會的發展來說并非一件壞事。“淺閱讀”代表讀者普遍的休閑需求,它是符合社會發展軌跡的生活方式。筆者認為“淺閱讀”的發展離不開人們的閱讀方式轉變和數字出版產業快速發展這兩個主要因素。
第一,理解閱讀給生活帶來的作用。閱讀是我們生活中重要的部分,“深閱讀”“淺閱讀”和“不閱讀”帶來的生活狀態都是不一樣的。我們應該在“淺閱讀”與“深閱讀”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深閱讀”是主體,但“淺閱讀”也不可少,要把“深閱讀”建立在“淺閱讀”的基礎上,研究、分析、架構思想體系。沒有廣泛的“淺閱讀”,怎么能尋找到“深閱讀”的內容呢?現代社會,年輕人和中年人的生活壓力較大,處理事物的方式多以簡單、便捷為主,因此,他們把“淺閱讀”作為生活中的主要閱讀方式并非壞事。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人習慣“淺閱讀”,就否定了他們對知識文化的追求。“淺閱讀”是廣見聞、拓視野、增加知識點的便利方法,而“深閱讀”則是打基礎、拓深度、建構知識體系的有效途徑。成年人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適當調整閱讀比例,而未成年人則需要在家長、老師的引導下進行“深閱讀”,養成閱讀的良好的習慣。
第二,正確認識數字出版對“淺閱讀”的推動。由于數字出版存在內容更新滯后、內容試用閱讀、內容付費閱讀等,很多人往往是對一本書、一本期刊進行粗略的了解,沒有興趣的話就放棄繼續閱讀,久而久之就形成 “淺閱讀”的方式。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的過渡,在某種程度上講,促使人們的閱讀習慣由“深閱讀”向“淺閱讀”改變。雖然目前全球的數字出版產業發展還處在摸索階段,但是我們對數字出版的發展給人們生活帶來的質變是必須要承認的。數字出版產業的快速發展,讓“淺閱讀”找到更多立足的領域,例如,在手機閱讀領域里,更多電子圖書適合當作“淺閱讀”的平臺;在網絡出版領域,網絡文學內容本來就不具備“深閱讀”的潛質;在平板電腦平臺里,微博、微信等軟件的碎片化信息更適合“淺閱讀”。那是不是數字出版就一定代表著“淺閱讀”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只能說數字出版的快速發展為“淺閱讀”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人們如果沒有很好地適應數字出版的內容,轉變閱讀思維,那么養成“淺閱讀”的習慣也就不足以為奇了。
二、出版轉型下“深閱讀”何去何從?
近年來,關于拯救“深閱讀”,提倡“深閱讀”等話題總能出現在人民的視野,那么,“深閱讀”到底是一個什么概念呢?是深度的精神閱讀方式,還是閱讀之后的深度思考?恐怕沒有一位專業人士能夠給予準確解答。然而,我們卻不得不尷尬地面對一個現實問題,那就是在圖書市場化的今天,不少的出版社盲目追求碼洋,在創造經濟效益之時,棄守社會效益的天平。失去了圖書的社會效益,那么這樣的出版物又如何能夠讓讀者“深閱讀”呢?與其說是現代人主動放棄“深閱讀”,還不如說是出版業在轉型中,讓“淺閱讀”有了更廣闊的生存空間。如何保留“深閱讀”的火種,筆者認為出版機構在未來發展中有三個方面的工作需要正確對待。
第一,圖書精品化出版。圖書傳承著人類的精神文化成果,支撐著人類的精神文化生活。閱讀將文化傳承、解構、再建設,也決定著一個民族思維的深度和廣度,對個人發展、社會發展、國家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國民閱讀也是出版業生產質量的風向標,圖書的品質決定了讀者選擇的閱讀方式。圖書帶有精神文化屬性,是特殊的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倘若出版社只注重經濟效益的發展,對圖書市場的產品缺乏精品化的追求,出版社沒有好書出版,那么讀者為什么要“深閱讀”呢?在傳統出版中,供給和需求之間的信息有太大的不對稱,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因此,出版社應注重圖書精品的出版,通過精品引導大眾讀者回歸“深閱讀”的道路。時代造就了很多暢銷書,而暢銷書帶給讀者多少價值,我們不得而知,出版社在造就暢銷書的時候,不應該只對作者負責,同樣需要對讀者負責。每一本暢銷書都應該成為“深閱讀”發芽的種子,真正種在讀者心中。
第二,注重學齡人群閱讀的引導。各種數據統計顯示,我國青少年閱讀在教育部門的推動下,正在向好的方向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圖書出版持續走高,青少年圖書成為整個圖書零售市場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總體份額已經占到圖書零售市場的12%。按理說,青少年圖書出版的快速發展應體現出我國青少年閱讀水平很高,但事實卻是相反的。青少年閱讀的功利化,導致青少年圖書出版缺乏規范的市場,從而直接影響我國青少年的閱讀水平。從教育環境看,雖然課堂內外的閱讀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但依然存在排斥課外閱讀的觀念;一些教師對兒童讀物知之甚少,無法對學生的課外閱讀進行自覺和有效的引導;學生課業負擔繁重,無法進行自主自由的課外閱讀。出版社應根據分級閱讀來出版青少年讀物在出版界已經不是什么新鮮的事情,但是這個關系多方的事情卻一直沒有形成有效的體系,從而導致學齡人群的閱讀方式存在偏差。特別是在數字閱讀興起的今天,如何正確引導學齡人群養成“深閱讀”的習慣是一件值得出版人深思的事情。
第三,重視圖書的推廣作用。近年來國民閱讀率不斷走低,吶喊閱讀的聲音一聲高過一聲,特別是大學生不閱讀的話題,似乎成了各路專家討伐的主陣地。究其原因是不是如此呢?我們發現我國的閱讀推廣工作根本沒有做到位,出版社、圖書館、書店、媒體等相關行業沒有重視對圖書的推廣工作,以至于“讀什么”成為一個難題。如果一個人不知道該讀什么,那么“深閱讀”又從何談起呢?與其糾結于“深閱讀”的內容,不如在“淺閱讀”中找到“深閱讀”的興趣點。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么會有出版社推出十大最難懂的圖書、讀也讀不懂的名著之類的民意調查。由于每年圖書品種繁多,沒有一個圖書推廣的平臺,很多讀者無從選擇對自己有價值的圖書,那只能放棄“深閱讀”。
三、誰才是王道閱讀方式?
在數字產業快速的發展下,“淺閱讀”是一把雙刃劍,其正負效應的發揮主要取決于我們能否辯證地看待“淺閱讀”與“深閱讀”的關系。如果過分凸顯“淺閱讀”的功能,則某些功能會異化;如果尊重其對“深閱讀”的正面意義,則可以最大化發揮其正能量。我們如何做好“深”“淺”互補,魚與熊掌兼得,這是一個新課題。筆者認為,只要做好數字出版產業的普及,“深閱讀”和“淺閱讀”之間的縫隙將會逐漸彌合,屆時人們對閱讀的選擇將更加自由,“深”“淺”之戰也就不會再有。
第一,倡導全民閱讀,提高國民素質。一個民族的素質決定了民族的未來,而閱讀是提高民族素質的重要途徑。無論是“淺閱讀”,還是“深閱讀”,只要國民對閱讀有正確的認識,那么對提高國民素質是百利無害的。可怕的是因為浮躁,國民對閱讀直接或間接地表現出無奈與反感,將閱讀從生活中剝離出去。在閱讀的過程中,尋找一個已逝的世界和一個未來的世界,能最大限度地接近與擁有這個現在的世界。因為直指心靈的閱讀與思考,能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快樂。目前,還沒有調查顯示“淺閱讀”沒辦法給人民帶來閱讀享受,因此,我們應該“重閱讀”,而不是要探討誰改變誰。
第二,尋找“深閱讀”和“淺閱讀”的平衡點。“淺閱讀”的正負效應并非永久固化的,如何通過“淺閱讀”尋找到自己“深閱讀”的路徑,政府、媒體、出版機構、閱讀推廣群體應該有所擔當,充分發揮引導作用,推動“淺閱讀”向“深閱讀”的轉化。我們自身要做到內心堅守、有所追求,充分利用數字技術的便捷,而非沉溺于娛樂至死的網絡;要嘗試定期遠離網絡,創造深度閱讀的狹小空間;要少讀而精讀,充分把握“深”與“淺”的平衡。在浮躁的社會環境下,我們一味地對“淺閱讀”追求過度快餐化、低俗化等負能量的指責是不正確的,這種批判是對閱讀發展規律認識的缺失。我們在“淺閱讀”盛行的年代,更要注重適當比例的“深閱讀”,避免“淺閱讀”過度、“深閱讀”不足。以“深閱讀”的思維力、評判力、觀察力,提高閱讀者去偽存真、去粗存精的能力,使得“淺閱讀”也能洗凈鉛華,返璞歸真。
第三,“淺閱讀”不代表沒有思考。“淺閱讀”能“輕裝上陣”,那就代表著內容能精煉,這就要求閱讀者有很高的閱讀的水平。“淺閱讀”的出現改變了我們傳統的生活方式,如何避免閱讀者成為被動的接收器,讓閱讀者具備更高的理性思維和判斷能力去接收洶涌而至的信息,真正成為信息的主人,這正是“淺閱讀”的魅力所在。無論“淺閱讀”如何快速地發展,它終究只是一個路徑,只有加入深度思考的要素,才能在閱讀過程中積累知識,養成閱讀的優良品質。只有“深”“淺”思考的有效結合,才能完善個人的知識庫,實現閱讀的意義。
(作者單位:河南科技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