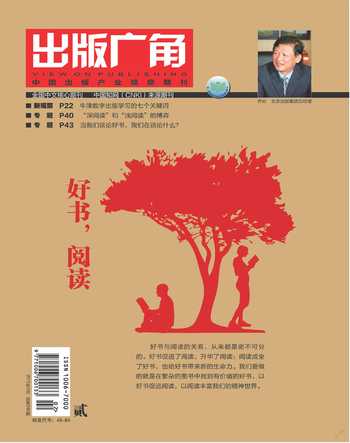再看編輯與讀者的關系
廖佳平
單個讀者的心理難以捉摸,但不是不可捉摸;分析讀者群的心理亦有章可循,即通過記錄和研究讀者的喜好、習慣、行為等信息,進行定位分析,這就是目前流行的精準營銷的基礎。
人心即市場的彼岸,出版人不能不了解讀者,尤其是出版社的編輯們,作為出版產品的“研發者”,所有的工作都應該建立在了解讀者的基礎之上。但人心難以捉摸,尤其是對作為個體的編輯來說,以個人之力來真正了解讀者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是強人所難的。
一、從讀者的角度看,閱讀是私人行為,難以捉摸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周年社慶的時候曾出版過一本《人心即市場的彼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年經營案例集》,筆者認為這個書名很好地闡釋了出版社/編輯與讀者的關系,也說明了讀者的重要性。“處理不好與讀者的關系,就做不出好書”,但恰如之前談到的,人心難以琢磨,而閱讀,恰恰是一種私人行為,充滿個性化。讀者是一個個的個體,差異性太大。所以才有這么一種說法:看看你的書架上有什么書,就大致可以了解你是什么樣的人。
網絡書店上再冷門的圖書都有需求,甚至數量還不少——據統計,亞馬遜網絡書店的圖書銷售額中,有四分之一來自排名10萬以后的書籍,而且這些冷門書籍的銷售比例還在高速增長——長尾理論在圖書出版領域得到了有效論證,其實也恰恰反映了閱讀是難以捉摸的。還有“二八理論”在書店的印證,有人說書店只賣那80%的讀者需要的那20%的圖書就可以了,但是徐沖在《做書店》一書中說,浙江圖書大廈某年動銷的品種數占全部品種數量的81%,沒有發生銷售的占19%,是否就不需要那19%的品種呢?作為書店,還真的需要這么多品種,因為書店也不能判斷哪些品種在這81%中,哪些又屬于其余的19%,為了這19%,書店必須準備100%。對出版社的編輯來說也是一樣,有時候讀者的閱讀喜好是不好判斷的。消費者心理學里提到的購買動機就有幾十種,縮小到圖書的消費里也有十幾種,想要識別實在不易。
二、從編輯的個人角度看,編輯對讀者的了解有可能是主觀的,與現實割裂的
從編輯的角色認定來看,編輯是把關者,是信息過濾者,編輯和出版社在某種程度上代替讀者行使選擇權(值得一提的是,這權力卻并非讀者授予的,在我國尤其如此)。同時,做書的過程是一項個性化的操作——同一部書稿,不同的編輯(團隊)、不同的出版社、不同的做書思路,最后的成書有可能截然不同。一般情況下,編輯和出版社在選題論證的過程中判斷一本書的出版價值和讀者對象、確定圖書的基本形態,會參考以往的經驗、外部評論、本社的出版方向、其他地區的銷售狀況和讀者意見,但是不可避免地會摻雜有編輯個人的喜好、經驗、社會經歷。特別在實際工作中,大部分圖書項目由責編獨立承擔,在這種情況下,編輯個人設想中的讀者對象和讀者的喜好,基本可以說是主觀的,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是編輯自我意識的投影,與現實是割裂的。在選題策劃階段所做的一些讀者調查,往往是不完整、不全面的,范圍窄,樣本數量少,得到的信息很難完整地反映目標讀者群。所以我們說編輯對讀者的劃分大多處于自我想象中,缺乏相應的依據。當然,也有少數編輯擁有靈敏的嗅覺、敏銳的眼光、精準的判斷、豐富的經驗,于是,主觀的讀者和客觀的讀者能夠基本重合。
三、了解讀者是一項系統工程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大部分情況下,大部分讀者是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的,或者說,對圖書的判斷力有限。因此,討好讀者、影響讀者、引導讀者是編輯和出版社的重要工作之一。
討好讀者、影響讀者、引導讀者的方式和途徑很多,目前使用得比較多的方法是影響和引導傳統媒體、輿論環境,利用社會熱點、政策形勢、意見領袖、話語權掌握者,間接作用于讀者。他們無法代表讀者,卻對讀者影響巨大。這也是平時圖書營銷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但現在傳統媒體也存在問題,大家會發現傳統媒體的宣傳越來越不能直接拉動銷售了。因為不論是報紙期刊還是電視廣播,這些傳統媒體傳播的都是單向信息,缺乏與讀者的雙向互動,即使有也僅限于滯后一期的讀者來信或者直播電話一類的,信息量有限,實時互動也有限。
現在,隨著微博、微信等社交類自媒體的出現,具備上網功能的智能手機也承載了越來越多的社交功能,這意味著信息的流動不再是單向的了,讀者可以多渠道地獲得信息,同時自己也成為信息的發布者,圖書營銷工作逐漸開始直接面對讀者。這更需要編輯了解,我們面對的是什么樣的讀者,因為讀者更多地相信和自己站在一起的人,而不是讓他從口袋掏錢的人。
單個讀者的心理難以捉摸,但不是不可捉摸;分析讀者群的心理亦有章可循,通過記錄和研究讀者的喜好、習慣、行為等信息,進行定位分析,這就是目前流行的精準營銷的基礎。真正地了解讀者,需要建立在對海量數據的分析、挖掘和整合的基礎上,在“大數據時代”,這個問題迎刃而解。不過話說回來,即使是拍腦袋和經驗主義也算是數據分析的低級形式,是編輯的一項功力。
現實情況是,編輯甚至出版社都無法得到海量的數據——銷售數量不夠龐大(大部分圖書印數三五千冊就沒有下文了,加印都是奢談),或者銷售行為無法記錄、收集和分析(多數出版社的發行系統只能監測到出貨數量,對實際銷售的情況只能靠經銷商提供的數據或者依靠開卷公司的數據進行估測,而且準確性需要仔細分析考證)。即使是目前書業數據分析的龍頭開卷公司,十多年來也只能做到收集國內重要書店的銷售信息進行趨勢分析。
在信息時代,真正了解讀者或者說消費者的,是豆瓣、百度、淘寶、天貓、當當、亞馬遜、京東等,他們才掌握著海量真實精準的數據,并且建立了可衡量的數據體系,能通過消費者的反饋來確認所做定位是否準確有效。從這個意義上看,了解作者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
值得一提的是,被寄予厚望的出版社天貓旗艦店不僅開拓了一條新的銷售渠道,還承擔著收集讀者數據的重要職能——調取后臺的數據,可以清楚地看到,入口分布(從微博轉入,從二維碼接入,網站檢索,等等)和轉化率(最終實現購買)等信息。希望一段時間之后,這些信息能夠產生積極的作用。雖然數據量和樣本不及當當、亞馬遜等網上書店,但出版社自身的天貓旗艦店的客戶信息更精準一些。因為出版社除讀者服務部外,很少面對面接觸讀者個體,信息多數需要通過另外的渠道比如經銷商傳達回來,天貓旗艦店提供了一個渠道。這些在出版社天貓旗艦店購買過書的讀者,其實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赤裸裸”地把個人信息透露給了出版社,這些信息不僅對營銷發行人員有用,對編輯也同樣具有參考意義。
另外,編輯常常想知道讀者對已出圖書的意見和反饋,以便今后的選題策劃更具有針對性,于是在書中附上讀者問卷調查或夾帶小書簽等方式直到現在還大量應用,但由于反饋機制低效(因為需要通過一定的發送手段,比如郵寄、傳真),這些過時的方式在驗證編輯對讀者需求的猜想和假設中所起的作用十分微小。微博營銷構建了編輯與讀者便捷溝通的機制,不過因為粉絲隊伍的混雜,也很難確認粉絲是否讀過或買過某本書,為編輯分析反饋數據增加了障礙,但如果出版社的官方微博粉絲數量大,互動頻繁,也不失為一個有效的途徑。印在書上的二維碼在讀者調查的營銷設置中將占有優勢,它對精準的目標讀者進行定位和適時跟蹤,會讓編輯需要獲得的反饋變得更加真實和可信,這需要在二維碼鏈接對應的后臺程序(比如讀者調查)才有效果。
出版社是企業,但其生存基礎卻存在不確定因素——讀者是上帝,其購買力不確定;作者是衣食父母,其創作力不確定,甚至版權到期能否續約都不確定。編輯能夠把握的就是把手上確定的圖書踏踏實實地做好,這是對出版社、對作者、對讀者、對自己負責的表現,也是編輯鑒別、統籌、運作、審美等綜合能力的體現。
(作者單位: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