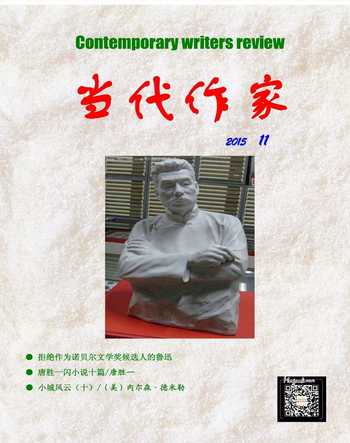尖山子上的背老二
郝明森
尖山子不高,千百年來一直安靜地橫臥在川陜交界東南面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里。因為不起眼,它很少受到外界的干擾;因為不起眼,也很少有外人知道它的存在。其實啊,這里的風景絕好,有各色的松樹林,有大片的野竹林,在松竹之間,還有潺潺的流水,山勢雖不陡峭,卻有舞動之流溪;松竹雖樸實,卻又能能聽得松濤陣陣,品得竹韻無窮,真算得上是一個臥藏在大巴山腹地的風水寶地。
尖山子腳下有一個居住著百多戶人口的村莊,村子里李姓居多,人們習慣地稱之為李家村。村里只有婦女和老人留守種地,男人紛紛背起背架上山當背老二。背老二又稱之為“背二哥”,是指以背運東西為生的人,見于一些交通不便的山區。山上源源不斷的礦產要靠人背下山,堆放在有公路的地方,山上的日常生活用品也是靠人力背上山。因此,尖山子的背老二是大巴山區一道獨有的風景。
背老二的背運工具十分簡單:一副背架子,一個打杵子,一兩只大麻布口袋和一根草繩子而已。這便是他們獨有的背運工具,看似簡單普通平淡無奇,卻極為方便切實耐用,它是山里人實踐的總結,經驗的提升,在山高林密、溝壑縱橫、山路崎嶇、難于運輸的大巴山區,實在無任何背運工具可以與之媲美。
背架子約模四尺來長,通常采用紫柏木做成下寬上窄梯子狀的背架,下寬不超過肩膀的寬度,上窄不超過人頭的寬度,且上部略帶一定的弧度。據此形狀,尖山子一帶人常把背微駝之人戲稱為“背架子”。
打杵子,約模二尺來長,通常選用硬雜木制作成呈“丁”字形狀。打杵子形制雖然簡單,但用途良多:其一,主要用于支撐背架子,讓背老二在長途長時的背運過程中,隨時隨地隨意得以喘息歇氣;其二,用以探路,大山里路況十分復雜,背老二在爬山涉水的背運途中,為做到心中有數,常以“打杵問路”的方式來探明路的虛實,水的深淺,以便正確應對;其三,用以防身,山高常有野物,林深多有毒蛇,大巴山散居的人戶亦常有護院惡狗,為防止遭到出奇不意的傷害,背老二的打杵子往往能起到防身的作用。
麻布口袋主要用來盛裝糧食、鹽巴、藥材、山貨、百貨等零散貨物,而水泥、化肥、油料、煙酒等有固定包裝的,則不需用。一個精壯的或有經驗的背老二,一次能背運二、三百斤,一天能行走六、七十里山路,渴了,喝一口山泉水,餓了,吃一點冷干糧,衣衫濕了又干,干了又濕,朝著既定的目的地,一步一個腳印的前進……你不能不為大山里的背老二這種吃苦耐勞的毅力和韌勁深深折服,發出由衷的贊美和感慨。
草繩是用來將貨物在背架子上栓固牢靠后,有意從背架子的頂端預留下一截繩子,特意做成一個用于輕松夠得著的繩圈,其用途是,當背運歇息時,為防止貨物重心的偏移,背老二常以手握繩圈加以調控,以防因重心的偏離對人身帶來的意外傷害和貨物的毀壞。這看似小小的環節,實在是大山里背老二在勞動實踐中的絕妙創造。
我記得人民公社時期,當時以生產隊為基礎的集體勞動,在生產隊或交公糧或購化肥、或買水泥的日子,全隊幾十號精壯勞力一齊上陣,幾十副背架子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形成了一字長龍,人多了,后面的往往看不見前面的路況,他們便憑藉著祖輩傳承下來的背運經驗,讓一位老成持重、恢諧幽默、富有經驗的打頭領路。
集體背運中,領路者無疑就是群雁之領,群羊之頭,雖十分榮耀,但責任委實不小;他一是要有意識的調控背運的行進速度,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快容易造成力氣的過分耗散而難以持久,也容易造成后面的跟不上趟而無法彼此照應;太慢則會失去應有的勞動激情,讓人感到越背越沉重,越背越吃力。
他二是要較合理的把握打尖歇腳的距離,間距過長,負重背運難以為繼。領路者往往選擇路面較寬地勢較緩的地方,將打杵子往背架子下一支,從心底發出長長的一聲“咿——呀——”,一身的疲勞隨之頓消。后面的一聽,便知道是打尖歇腳了。緊接著,便是那一聲接一聲的“咿——呀——”,然后領頭唱起山歌:
“尖山子的河,尖山子的坡,
我是尖山子林的背二哥;
太陽送我上山坡,
月亮背我過小河,
打一杵來唱首歌?;
人家說我好快樂,
何曾有過快樂處?,
半輩子未出尖山子坡。”
這邊的一唱,對面的也跟著唱起來,有時兩邊一唱一和,相互調侃很有趣:
這邊問:“背二哥?”
那邊答:“哎!喊啥子嘛!”
這邊吆喝:“上山羅!”
那邊眾應:“來羅!”
相互打過招呼,前面的找一個開闊平坦,或有大樹遮蔭,或有山泉溪流之地,放下背架子,用打杵子支穩后,全身心放松休息,喝喝水,抽抽煙,吃點自備干糧,相互吹牛沖殼子,有說有笑地唱歌解乏:
“叫聲腿桿你莫粑,上坎就到風門埡,
店老板娘等著你,敞開胸膛在喂娃娃,
你要想吃她那熱饅頭,你就慢步慢步往上爬!”
歌聲此起彼伏,在山谷中回蕩,久久不息。
領頭人三是要隨時隨地觀察道路情況,如遇爬坡坎,拐急彎、路濕滑窄,有行人或障礙等等情況,及時唱報給后面的知曉,后面的聽報后,一面采取應對措施,一面隨聲唱答表示知道。這種帶有一定韻味的“一報一答”形式,是背老二在勞動實踐中自然形成的,也是山區人所特有的。有人把它稱為“背運歌”,也有人把它叫做“背運號子”。
山區背運,爬坡下坎是常有的事,當遇到爬陡坡和下高坎時,領路者不僅要提請后面的注意,而且要激發大家的激情。爬陡坡時,前喊道“山路高——喲!”后答道:“使勁攀——啰!”前又喊:“前是弓啊!”后又答:“后是箭喲!”前再喊:“腳踩穩吶!”后再答:“腿不彎嘛!”下高坎時,前囑咐:“低頭下坎坎——”后答應:“眼睛把細點——”又囑咐:“腿桿莫打閃——”后答應:“心里莫著急——”
在大山里行走,即使是再偏僻的地方,也總有行人相遇讓道情況發生。這時,領路者首先就要判斷告知,如果路面較寬讓得過時,他就說:“大路朝天,”后面就答:“各走一邊,”雙方便相讓而過;如果路窄難讓時,他就說:“干脆打尖讓為先。”后面就答:“背架支起靠一邊。”的確,山里人歷來就有“禮讓為先”的傳統,這或許是歷史的傳承,或許是淳樸民風的使然。他們往往是人多的讓人少的,下坡的讓上坡的,背輕的讓背重的,背小件的讓背大件的。在相互禮讓的同時,還不忘互致問候和囑咐:“老哥,走得好快喲!”“老哥,小心!路滑要走穩啰!”“兄弟,走路過細喔!”說得實實在在,聽得高高興興。
在山區交通運輸得到根本改善的今天,我下鄉路過尖山子,看見通村公路繞到家家戶戶的門口,那一條條平坦寬敞的公路上早已不見了背老二的身影,他們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大巴山區的遺跡和歷史。是遺跡,就應該保存;是歷史,當有所載記。讓后來的人們知道,只有大山才造就了背老二,只有背老二才能創造出那獨有的背運工具和獨特的背運文化。此時,我無意中看見一農家房檐下掛著的背架,仿佛聽到背老二那首歌謠在耳邊回響:
“背老二,好不苦,
一副肩,三打杵。
黃家溪,吃晌午,
三個苞谷粑,
兩碗菜豆腐,
脹得狗日的眼睛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