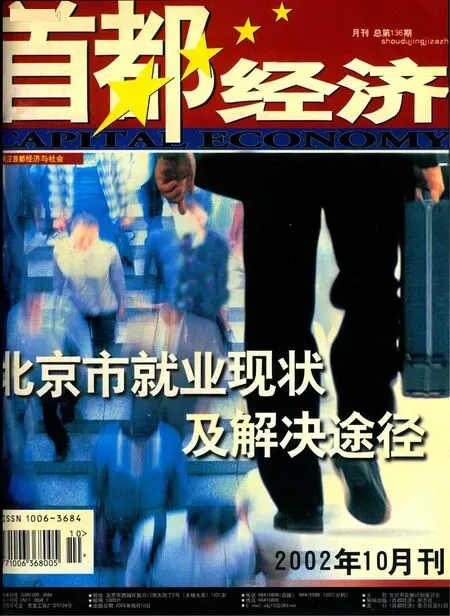“中國奇跡”沒有終結
梅新育

“中國奇跡”終結了嗎?隨著其它幾乎所有新興市場經濟體相繼發生大規模經濟震蕩,隨著中國經濟第一、二季度增長率下降到1990年以來的最低點,隨著這些時候中國股市的震蕩波及全球市場,隨著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下調與中國股市震蕩成為8月下旬全球匯市、股市、初級產品市場大震蕩的由頭,……國際市場“唱空中國”的聲浪似乎比十年來任何一年都要強烈,西方主流咨詢機構聲稱俄羅斯投資環境超過中國,波士頓咨詢公司報告聲稱中國制造成本直逼美國,《紐約時報》重頭報道中國棉紡企業登陸美國,印度政府和機構不斷放言將借助廉價勞動力優勢趕超中國制造,……甚至估計將出現人民幣匯率崩盤、資本外逃失控。
然而,只要全面冷靜客觀審視,就不難發現,從當前來看,中國經濟基本面仍然比其它經濟大國和新興市場要好,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程度被大大夸大了,中國經濟“保增長”的空間比其它國家要大得多;從中長期來看,中國商業環境和競爭力的基礎優于其它主要經濟大國和新興市場;從穩定市場來看,中國沒有動機挑起一場競相貶值的“貨幣戰爭”,更有能力保證人民幣匯率站穩。
“保增長”空間廣大
當前中國經濟基本面相對仍然較好,而且中國政府宏觀調控“保增長”的空間要比其它大多數國家大得多。
一般說來,一國央行意欲放松貨幣政策以求“保增長”時,最大的約束條件在于“保增長”和“抑通脹”兩項目標之間可能發生沖突,因為旨在“保增長”而放松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將加大通貨膨脹壓力,只有在通貨膨脹壓力較小或正在趨向減輕之時,放松貨幣政策方才不至于引發通貨膨脹大幅度上升的后果。可以確定,中國經濟基本面給央行放松貨幣政策創造了較為寬松的空間,央行此時如此操作,無須擔憂通貨膨脹急劇上升。
如此判斷不僅僅因為此前相當長一段時期以來中國通貨膨脹一直在低位運行,而且作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和外貿依存度僅次于德國的經濟大國,中國通貨膨脹壓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外部輸入,特別是通過進口原料、能源、糧食等大宗初級產品和制成品價格變動而輸入,全球初級產品市場已經陷入深度熊市并將持續相當一段時間,決定了我們當前和未來相當一段時間里面臨的不是通貨膨脹壓力,而是通貨緊縮壓力,豬肉等少數商品價格上漲雖然引人注目,但并不能全面扭轉這一點。
倘若本幣對美元匯率暴跌,以本幣計價的初級產品價格仍然可能上漲,但這種情況可以出現在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卻不能出現在中國。因為中國存在持續的貿易順差和經常項目收支順差,這一點對人民幣匯率構成了最強有力的支持,決定了人民幣匯率即使對美元有所貶值,貶值幅度也較小。
相比之下,巴西等存在持續貿易逆差和經常項目收支逆差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此時深陷窘境:虛弱的貿易收支和經常項目收支給市場參與者創造看空其本幣匯率的理由,從而抽逃資本,進而形成“資本外逃——本幣對美元匯率貶值——資本加劇外逃”的預期自我實現的惡性循環。
正因如此,我們看到了央行于8月25日再度放松了貨幣政策,速度、力度均超過預期,不是僅僅降低利率,而是利率、準備率“雙降”。
中國優勢長在
從中長期來看,決定中國經濟、制造業和外貿發展前景的基本面仍然有著鞏固的優勢,這一點不因西方和其它一些國家的某些輿論、不因某些個案而改變。
以成本優勢衰減為例。不錯,中國國民收入已經大幅度提升并將繼續提升,昔日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已經一去不復返,這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且中國政府也要努力讓最廣大的國民分享發展的成果,不會長久將勞動者低收入作為國際競爭中的一項“優勢”。但在這個昔日優勢衰減消失的同時,新的優勢正在應運而生:
隨著中國國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長,中國國內市場規模空前擴大。對于面向中國國內銷售市場的投資者而言,他們的機會空前廣大。
隨著中國國民收入增長,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躍居世界第二,而且有望未來趕超美國,而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中國實際GDP規模去年就已經超過了美國。較大的經濟規模意味著更高的宏觀經濟穩定性,意味著中國政府在實施宏觀調控、穩定經濟增長時有著更廣闊的空間。
不必拿前些天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約5%說事,因為人民幣對歐元、日元匯率一直強勁,人民幣匯率變動的根本原因不是人民幣疲軟,而是美元太強。至于其它新興市場貨幣穩定性更不能與人民幣同日而語,須知近一個月來,在24種交易最廣泛的新興市場貨幣中,已有20種程度不同地貶值,俄羅斯盧布、智利比索、巴西雷亞爾5月以來貶值幅度都超過了10%,印度盧比已經貶到17年來最低水平,南非蘭特、巴西雷亞爾匯率貶到了13年、12年來最低水平。
不僅如此,外部渲染的其它國家某些“優勢”只是暫時的,或是被其它因素徹底抵銷了。
以能源成本為例。波士頓咨詢公司《全球制造業的經濟大挪移》報告聲稱,若以美國制造成本為100,中國大陸制造成本已經上升到96,而能源成本上漲是一個重要原因。對于赴美投資的中國棉紡和其它制造業企業而言,美國廉價的能源有著強大的吸引力。問題是美國的廉價能源優勢來自新世紀的“頁巖革命”與原油、天然氣出口管制相結合,這樣才使得美國能源價格在近年的初級產品牛市期間比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東亞地區都要低很多。可是,去年6月以來國際市場油價雪崩,整個初級產品市場從2012年起步入可能延續10—15年的熊市,美國國內能源成本優勢已經大大縮小,美國政府放松原油和天然氣出口管制將進一步縮小、消除這個優勢,奧巴馬力推的《清潔能源計劃》甚至可能將美國國內能源成本提高到東亞之上。在這個大趨勢下,渲染、指望中國的這些劣勢能長期延續,不切實際。
即使是某些力圖趕超中國制造的發展中國家,他們相對于中國制造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也被其它方面的缺陷抵銷了很多,而且這些缺陷往往植根于其基本制度而難以改觀。印度勞動力薪酬比中國低很多,但即使不考慮兩國勞動力素質、生產率和質量等方面的差異,印度高昂的征地成本也要在很大程度上抵銷其勞動力成本的優勢,須知發展中國家要發展,必須要發展非農產業,修建基礎設施;而發展非農產業和修建基礎設施離不開征用土地。
距離40余萬人口的印度小城馬圖拉市13公里的農村,近日爆出頗為轟動的兩萬五千印度農民向總統慕克吉請求準許自殺的新聞,其征地成本居然達到了武漢市緊鄰市區農地的征地補償標準,是長三角百萬人口縣級市常熟的4倍還多,而武漢市人口千萬、人均GDP是印度的10倍,常熟人均GDP更高達印度的13倍以上。從更大背景上考察,一個發展中國家倘若征地過難,非農產業難以發展,將形成“征地難——非農產業難以發展——非農就業機會少——農民更加死守耕地、征地補償要求更高——征地更加難”的惡性循環,整個國家深陷泥潭無從實現起飛。
再考慮到中國在基礎設施、產業配套、公共服務、人力資源素質等方面的優勢,以及中國政府、國民不斷改善的決心努力,我們可以相信中國商業環境、制造業和外貿仍能長期保持相對優勢。
中國有能力保持匯率穩定
中國經濟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幣匯率連續大幅度貶值,中國經濟決策者沒有挑起競爭貨幣貶值的動機,人民幣匯率應該站穩,也必然會站穩。
經濟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幣匯率連續大幅度貶值,只要擺脫非理性恐慌情緒影響,就不難看清這一點。這不僅僅因為中國經濟增長率雖然與自己以往紀錄縱向比較有所降低,但與別國橫向比較仍然高不少;也因為中國仍然保持著貨物貿易和經常項目收支順差,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規模也保持在高位。中國財政收支和負債狀況在全世界經濟大國中也屬于相對較好水平。
同時,無論是中短期還是長期,中國經濟決策者也沒有放任、乃至激勵人民幣大幅度貶值的動機,更無意于挑起以鄰為壑的競爭性匯率貶值。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短期內,人民幣匯率大幅度貶值必將惡化持有美元負債的中國企業的資產負債結構,而且,能夠在此前數年從國際金融市場上借入低利率美元債務的中國企業都是品質較好的企業,其中不乏中國各個產業的骨干,他們資產負債結構倘若顯著惡化,對中國國民經濟穩定將帶來何種沖擊,不言而喻。
從長期來看,中國如果輪番出現“金融市場震蕩——人民幣大幅度貶值”局面,那就是已經陷入了經濟起飛后的發展停滯,或者說“拉美化”。這種處境對中國沒有任何吸引力,也是中國多年前就開始警惕防范的。
新興市場在中國外貿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也決定了中國對競爭性匯率貶值沒有興趣,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新興市場在對華貿易中所占份額都超過了50%。因為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高度依賴初級產品,而正如這些天市場動蕩顯示的那樣,中國經濟利空和人民幣匯率下調對初級產品出口國經濟及其貨幣匯率是更大的利空,競爭性匯率貶值實質上等于損害中國的外需。
中國無意挑起以鄰為壑的競爭性匯率貶值,同樣可以從貿易政策走勢得到側面旁證。1930年代大危機期間競爭性貨幣貶值浪潮期間各國政府配套采取的是什么?是限制進口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特別是美國國會1930年通過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雖然遭到了36個國家的抗議和美國國內1028名經濟學家的聯名上書反對,還是得到了胡佛總統的簽署生效,從而一舉將美國平均進口關稅率提高到53.2%,1932年達到59%的峰值,觸發了60個國家相繼提高關稅的關稅戰,導致全球貿易急劇下降,美國1932年進口只有1929年的31%,出口降幅更大。但中國采取的是什么措施呢?在近兩年中國經濟、外貿減速的同時,中國采取的措施是擴大進口,設立和擴大自貿區。
中國更有能力在投機性貨幣攻擊壓力下維持人民幣匯率大體穩定。這不僅僅是因為近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賦予中國全世界無與倫比的匯率“維穩”能力,也由于中國經濟、金融資產巨大的規模本身就決定了恐慌性和投機性資本外逃無法發展到足以動搖全局的地步,其它主要經濟體政府和中央銀行也有強烈的內在動機主動與中國協調。
大規模資本外逃或資本流動逆轉是新興市場貨幣匯率大幅度貶值的重要原因,對于規模較小的經濟體而言,資本流出總量尚不足以對美元匯率和美國資產價格產生根本性影響時,就已經足以觸發該國匯率大幅度貶值了。但中國經濟和金融資產規模巨大,足以觸發人民幣匯率大幅度貶值的資本外逃規模也足以大幅度抬高美元匯率和美國資產價格,不僅使得資本外逃、逃向美元不再合算反而風險重重,也會對美國實體經濟部門和金融市場造成破壞性的混亂。
倘若出現過大規模的資本流入,過度抬高美元匯率,對美國制造業的競爭力更是毀滅性打擊。屆時,美國經濟決策者們愿意看到這樣的局面嗎?歐洲需要中國的市場和投資以擺脫衰退,因此他們的領導人沒有對中國經濟惡語相加,相反,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奧朗德等歐元區主要領導人主動表態對中國經濟有信心,甚至在貌似與中國無關的烏克蘭問題三方會晤新聞發布會上也這樣表示,國際經濟組織相繼表態對中國經濟有信心,美國遲早也會認識到這一點的意義。
同時,由于中國市場的震蕩引發全球市場大動蕩,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系統重要性和宏觀穩定性相對優勢反而凸顯,這樣也會削弱資本逃向美元的動機,增強資本回流中國的動機。如果說此前很多人對中國經濟的系統重要性認識還不夠充分,那么,經過這次震蕩,大部分市場參與者已經認識到了。國際知名財經專業電視臺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調查顯示,截至北京時間8月27日上午9點47分,投票者中最關注美聯儲者占比45%,而最關注中國人民銀行者占比55%。盡管這可能只是小范圍的非正式網上投票調查,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市場參與者們的認識和情緒。
從更大背景上考察,對于一個新興大國而言,一時的經濟震蕩未必就意味著其上升勢頭夭折,反而也有可能藉此展現出其經濟影響力和開展必要的改革。美國制造業1880年代初已經躍居世界第一;1913年,美國工業生產總量等于英、德、法、日四國總和,占全世界1/3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躍居世界最大債權國。即使到那時,美國仍然不是對國際經濟、金融及其規則影響最大的國家,美國經濟、金融真正展現出其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卻是在1929年美股崩盤蔓延世界之后。羅斯福的“新政”對大危機中暴露出來的問題進行深刻的改革,確保了美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地位上升趨勢沒有被這場起源于美國的危機打斷,隨后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躍居資本主義世界無可爭議的霸主。
(作者: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