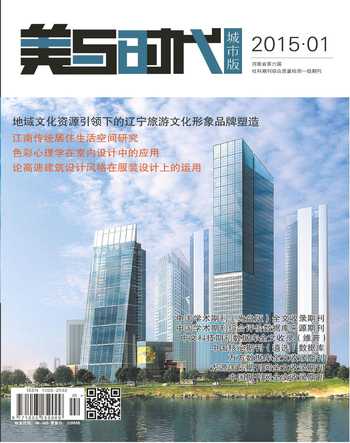攝影中的情感表達
何江江
摘要:通過分析攝影中情感的來源,剖析了東西方文化給攝影家帶來的不同情感表達方式,追問東西方攝影中情感表達的大同,探討了當代攝影藝術中的情感表達方式的一些探索。
近百年來,從干版、濕版、膠片再到數碼,攝影經歷了一個不斷被改寫的歷程,攝影的含義也在變化。如今,數碼技術使攝影的技術門檻大大降低,許多照片在喪失了攝影最初的儀式感后變得毫無感情和生命力。攝影不僅是技術和器材的載體,更是文化和情感的載體。攝影家通過攝影作品把情感傳達給讀者,在觀者心里激起情感的波瀾和啟示。
攝影師的情感首先來源于個人的成長經歷,而一個時代獨特的意識形態同樣在攝影作品中留下了時代的烙印。60年代的美國攝影作品中有大量的體現搖滾樂、嬉皮士、無政府主義、祈盼理想重生等時代主題,記錄了瘋狂而自由的社會氛圍。中國80年代則是重新啟蒙與情感復蘇的年代,探索、實驗、思索成為那個年代尋找社會本相的攝影家的心志。時代改變,攝影作品中的情感也隨之改變。在這個意義上,攝影史就是一部人類的感情史。而在當代中國,在消費社會的沖擊下,人開始迷失,大部分攝影作品的情感都趨于追問人的身份問題,表達一種對時代的莫名的情緒。所以攝影師了解社會的變化,把握其情感的走向十分重要。
在中國文人山水畫中,意境是靈魂。中國文化審美意境作用于攝影,可以理解為攝影作品中的景與情交融,帶給觀者情感共鳴,傳達出寫意的,天人合一的美學精神。老子的"大象無形"到作用于攝影上:虛化的影像給人帶來超現實意味的、強烈的視覺感受,即所謂的形遁而魂見。——心象之映虛,乃精神之紀實,東方許多攝影師以“虛”來傳達主觀的情感宣泄。禪宗里面的“空寂”則完全排除“物”的世界,建立在“無”的美學基礎上,是“主客泯滅”、“物我兩忘”的境界。“不是我在拍照片,而是照片在拍我”的攝影觀念便是代表。
西方文化重理性,強調精確地再現對象,給觀者以冷靜理性的感受。本雅明在《明室》中提到攝影的瘋狂之處就在于通過照片觀者立刻就能相信照片中的事物從前存在過,在攝影、瘋狂、和某種不知其名的東西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西方傳統文化尊重個人的價值和權力。在攝影表達上表現為對人的問題的關注,攝影師發現并揭露各種問題對人的影響,充當人性的見證者。罪感文化中負罪感的產生預示了人的一生要不斷的與深不可測的生命生命本身抗爭,以此來確認自己,在攝影藝術上表現為對惡和痛苦的展示,以此來承認惡的意義,作品一般都充斥著強烈的情感。
東方文化背景下的攝影的情感表達趨向于模糊,并沒有明確的指向性;表現為一種寫意性,注重人物感情的抒發;情感表達內斂且感性居多。而西方文化導向下的攝影容納批判精神、矛盾的人類社會和自然社會理念、強烈的個人體驗表達以及西方哲學思辨性;其情感表達傾向于精確,理性較多;對生命、死亡的痛苦的追問,導致沖突、厚重的情感較多;濃厚的人道主義情感較多。
然而攝影的情感表達必然有跨越東西方文化鴻溝的大同。不管來自東方還是西方,很多攝影師都以自己的一生來“見證生命,融入被攝者的生活”,以宗教般的虔誠對生命和人類的情感做了一次偉大的詮釋。攝影見證了近一個世紀里時代的種種悲劇,充滿了被戰爭蹂躪、被虛無包圍、被犯罪腐化、被自我的傷感侵蝕的人性,卻缺少生活中甘美面。而臺灣攝影師阮義忠說,“攝影不是暴露不好的東西,而是一種對好的肯定。”他的攝影就是在捕捉整個時代的鄉愁和情感,那些充滿泥土味的照片能填補現代人心靈的空缺,帶給人們心靈上的慰藉。法國攝影師拉蒂格一直用童貞快樂之心和對生活的真誠來攝影,提醒人們在美好的時光原是存在過的。這兩位攝影師都以直接溫暖細膩的方式來記錄自己的家鄉,記錄了人世間最美好的回憶。攝影雖然受文化、地域的影響,但人的感情才是最具主導性的,它能安排人與物作為被提純的符號進入畫面,從而進入到對影像最本質的表達中。攝影師需要在與其它文化的交往、比較、對抗中建構自己的身份,更需要在與諸多力量的交織互動中建構自己的身份,只有這樣攝影中的情感表達才能進入人類學的范疇與歷史的維度,從而把個人的情感融入時代發展的軌跡里面。這種整體把握世界的方式是當代攝影藝術情感表達的一個趨勢。
當代攝影藝術家開始尋找在不同文化、不同媒介中攝影所展示的一種微妙、模糊的情感,以此通向對攝影本體語言、攝影身份的一種抽象思考,藝術家以自身獨特的藝術理念去重新建構這個世界,通向對攝影情感表達中新的闡釋中。在國家、宗教、身份、記憶、身體、社會性別、欲望等各種敏感議題展開討論,其情感表達朝著更為豐富更為自由的方向發展。當代攝影藝術家中還有一部分回歸到攝影最本質的記錄功能,讓攝影盡可能自然的表達,盡量減少攝影師有目的的干預所造成的痕跡,以此來使照片擁有任何主題,在觀眾面前開放了一種與無限互動的可能。
藝術作品存在的價值在于:當一個人被一件作品感動時,他會開始聽到藝術家創作伊始所蒙受的真理的召喚。在中國當代的攝影藝術中,有許多創作者還停留在形式的創新上,沒有深入個人與民族情感經驗的深處,而是按著西方的審美標準去制造一種模式化了的攝影,攝影師的自我情感往往被遮蔽,其作品很難有說服力。這種浮躁的趨勢會對國內的攝影文化不利,也會對后來的攝影師造成誤導。攝影的主旋律應該是面對,最大限度的面對真實的自我。中國當代攝影要有一種使命感與責任感,對長期植根于這塊土地上的情感要去追尋與探索,讓更多的人能從中得到情感上的認同與心理的慰藉。
當代的中國是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速度感容易使人盲目,但也帶來了可能性。作為當代中國的攝影師,需要向民族的內核與自我的經歷不斷深潛,使作品有情感上的說服力;需要在與其它文化和其它媒介的交叉碰撞中不斷更新對攝影語言形式上的探索,找到其中的微妙的契合點,使作品有情感上的創新;并需要在與現實社會的對話中來不斷更新,鍛煉把握時代脈搏的靈敏度與力度;也需要探索攝影和其他藝術形式之間的實驗性交融,從而拓展攝影的可能性。
【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