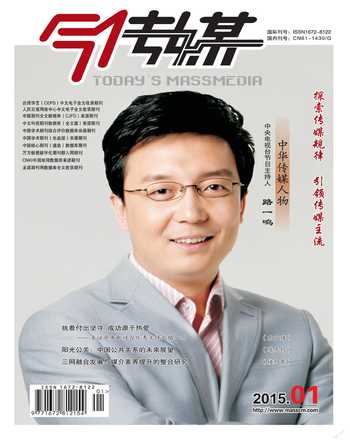大眾傳播視閾下人文精神“式微論”芻議
葉志飛
摘? 要:人文精神的式微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人的異化”,反映在大眾傳播領(lǐng)域就會出現(xiàn)諸如傳播價值觀扭曲、傳播內(nèi)容過度娛樂化、受眾商品化、傳媒從業(yè)者職業(yè)道德淪喪等一些令人堪憂的弊病,這些問題為何會出現(xiàn)?在今后以新媒體為主導(dǎo)的后大眾傳播時代,我們該如何著手解決這些問題并重?fù)P“人文精神”這面大旗正是本文所要芻議的主題。
關(guān)鍵詞:大眾傳播;人文精神;式微論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5)01-0059-03
人文精神古來有之,在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文化中存在著大量人文精神的因子,尤其是在諸子百家的經(jīng)典論著中尤為凸顯,譬如孟子“民為貴”的民本思想,孔子“仁者愛人”的儒家核心思想,莊子提倡“超然物外”的“羽化神游”,皆強(qiáng)調(diào)個人的尊嚴(yán)、道德的完善以及思想的自由等等。由此可見,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中對人的主體性的認(rèn)識達(dá)到了極高的境界,無不展示著高潔的人性光輝。
隨著“五四運(yùn)動100周年”的即將到來,在西方文藝復(fù)興和思想解放運(yùn)動中興起的人文主義思潮也隨之傳入中國一百多年了,西方的人文主義精神旨在通過認(rèn)識人的本性,尊重人的價值,肯定人的存在來驅(qū)散籠罩于西方中世紀(jì)上空的漫長的封建黑暗。人文主義精神主張以人為本,回歸人性本然,任何外界強(qiáng)加的非人道的桎梏和壓迫都不能阻止人對自身全面發(fā)展和對更美好的生活的不懈追求。
一、大眾傳播視閾下的人文精神內(nèi)涵
人文精神的核心內(nèi)涵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第一,人文精神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guān)懷,表現(xiàn)為對人的尊嚴(yán)、價值、命運(yùn)的維護(hù)、追求和關(guān)切;其二,對人類遺留下來的各種精神文化現(xiàn)象的高度珍視;第三,對一種全面發(fā)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1]。而筆者認(rèn)為“關(guān)注人、關(guān)懷人”才是當(dāng)下大眾傳播視閾下人文精神內(nèi)涵的正宗要義。具體來說,從大眾傳播的角度理解的人文精神,更多地表現(xiàn)為大眾傳播過程中對人的關(guān)懷,對人尊嚴(yán)的捍衛(wèi)、價值的追求和命運(yùn)的關(guān)切。社會責(zé)任理論也強(qiáng)調(diào)大眾傳媒的社會責(zé)任,認(rèn)為傳媒享有的新聞自由應(yīng)以承擔(dān)“社會責(zé)任”為前提。人雖然是具有理性的動物,但思想的懶惰會厭倦運(yùn)用理性,陷入無所用心的盲目狀態(tài)。因此,大眾傳播有責(zé)任倡導(dǎo)和捍衛(wèi)社會道德、激勵公民運(yùn)用理性[2]。
二、人文精神式微的本質(zhì)
當(dāng)今中國的人文精神卻呈現(xiàn)出一片式微的光景,從日益昌盛的大眾傳播中就可見一斑。人文精神的式微正如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提到的“人的異化”。馬翁認(rèn)為,人如果把客觀世界及其人本身作為實(shí)現(xiàn)目的的手段,那么人就徹底的異化為非人的機(jī)器。自私、貪婪等人性中非理性的因素膨脹,直至沖昏人的頭腦,阻止人進(jìn)行理性的思考,社會就會出現(xiàn)大面積的道德滑坡。這種現(xiàn)象是可怕的,并正在大眾傳播領(lǐng)域中發(fā)生和蔓延。
三、大眾傳播中人文精神式微的表現(xiàn)及其原因
(一)傳播價值觀的扭曲
現(xiàn)在很多大眾傳媒的傳播價值觀尚未建構(gòu)于普世價值觀之上,具體到中國國內(nèi)的情況來看,也尚未客觀地遵循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忽略了矛盾的客觀性和多樣性,仍舊簡單粗暴地用階級斗爭的思想來統(tǒng)攝對一個客觀歷史事件以及該事件中歷史人物性質(zhì)的判定,在廣大受眾的思想中硬生生地樹立了“非對即錯”的二元對立論。這會給社會帶來一種非理性的主觀思考,導(dǎo)致一些價值偏差和愚昧行為。理性的思考需跳出單一的對立思維,跳出既有的框架,站在人性的普世立場來審視人類的過往,想必這樣才能更接近一個客觀的真實(shí)。
譬如現(xiàn)在大眾傳播的內(nèi)容中充斥著對某些歷史事件的簡單定性和對若干歷史人物的粗暴評價。歷史事件本身是極其復(fù)雜的,歷史人物身處其中也是一個矛盾體。用簡單的只言片語對其進(jìn)行概括,甚至是只講好話不講壞話,或者是只講壞話不講好話,這樣做法的本身就是對歷史的反動。唯有不斷探索,通過我們所及的能力展現(xiàn)出事件的碎片,而不是過去的本身。認(rèn)識過去的目的是為了認(rèn)識人本身何以至此,并非從道德情感上去對所有過往做出道德評價。而作為道德評價的好與壞,無非就是自己想要通過簡單的方式去體認(rèn)自己的過去,這本身就是反人性的。只是單單考慮簡單因素,陳述所謂的事實(shí),而未考慮歷史合力為何會把事件引向那個方向。更有甚者,在下結(jié)論前就預(yù)設(shè)諸多目的,大搞民族主義的伎倆,簡單的兩分法、價值對立的二元論等等。所以,大眾傳播的價值觀勢必要回歸到關(guān)懷人的基點(diǎn)上來,不斷探求人性的本質(zhì),還原人類最真實(shí)最美好的情感價值,探尋未來人類的發(fā)展之道。
(二)傳播內(nèi)容的過度娛樂化
縱觀整個大眾傳播的生態(tài),娛樂化無不充斥著大眾傳播的每一個毛孔。隨著人類社會從近代走向現(xiàn)代,現(xiàn)代走到當(dāng)代,工業(yè)化和城市化不斷升級和擴(kuò)展,打破了原有的以貴族和平民為階級基礎(chǔ)的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的格局,形成了以城市工業(yè)階級為基礎(chǔ)的廣泛的大眾文化。但往往出于對商業(yè)利益的考量,迎合大眾的消遣需求,媒介所擔(dān)任的娛樂功能被無限放大,占據(jù)了教化功能的上風(fēng)。
作為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大眾媒介在傳播內(nèi)容上所反映出來的結(jié)果當(dāng)然就脫不開娛樂過度的快餐式的文化消費(fèi)景觀,正如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提到的那樣:現(xiàn)實(shí)社會的一切公眾話語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xiàn),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yè)都成為娛樂的附庸。而且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jié)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文化被娛樂所裹挾,人們也不再嚴(yán)肅和批判。最終“我們將毀于我們熱愛的東西”。文化將成為一場滑稽戲,等待我們的可能是一個娛樂至死的“美麗新世界”,在那里“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笑以及為什么不再思考”[3]。總之,受眾信息的享樂主義在蔓延,在消費(fèi)社會中,受眾的生活習(xí)慣、思考方式甚至政治洞見、生存技巧都發(fā)生了變化。
娛樂化泛濫的危害直接關(guān)涉到政治傳播學(xué)中很重要的一個命題——公共領(lǐng)域的消失。在大眾媒體出現(xiàn)或尚未蔚然成風(fēng)之前,在歐洲的一些咖啡館和酒吧中,社會各階層在此聚集,討論時政,相互溝通,形成了一個個能影響社會輿論導(dǎo)向的陣地和堡壘,這是一種特別的輿論場,像民間的下議院,討論的過程和結(jié)果能引發(fā)民眾對一切更為理性的思考和判斷,自然也就很好的促進(jìn)社會的民主自由之風(fēng)氣的進(jìn)步,而民主和自由是人文精神延展到近現(xiàn)代的基本保障。然而,這樣的傳播形式在現(xiàn)在是極其稀有甚或絕跡了的,民眾被電視廣播網(wǎng)絡(luò)等大眾傳播的搞笑娛樂所誘惑收買,在這樣繁雜緊迫生活環(huán)境中帶給人輕松娛樂,自然就排斥掉了對殘酷現(xiàn)實(shí)的省思。
從組織傳播學(xué)的層面來看,大眾傳播確實(shí)打破了傳統(tǒng)社會具有教化引導(dǎo)功能的組織(群體)傳播,在中西方的傳統(tǒng)社會,都存在類如教會、宗族這樣的群體性和組織化的傳播場,每一個成員都會或多或少地被侵染上群體的觀點(diǎn)和規(guī)范,而往往這種群體的態(tài)度能很好地引導(dǎo)個人的健康成長和良性發(fā)展,但也是因為大眾媒介傳播打破了以往以“鄉(xiāng)村社群”為組織(群體)的傳播,信息流被解構(gòu)重組,人成為孤立的原子,只有群體傳播才具有的心理認(rèn)同感、社會引導(dǎo)、道德上的肯定等社會調(diào)節(jié)機(jī)制在大眾社會的大眾文化中正在逐步消失,道德秩序失范,人文精神也必然隨之式微。
(三)傳播受眾的商品化
媒介發(fā)展過程中沒有把每一個受眾當(dāng)做充滿血肉和溫情的“人”來看待,而是浮夸的內(nèi)容與低劣的手段來迷惑愚弄受眾、奴化受眾。受眾的商品化就是人的異化和被異化。
《通俗文化理論導(dǎo)論》中說道:“大眾文化理論傾向于把受眾看成是被動的、因循的、無需求的、脆弱的、可操縱的、可利用的和多愁善感的大眾,他們抵抗理智的挑戰(zhàn)和激勵,容易成為他們不得不接受的消費(fèi)主義、廣告、各種夢想和幻想的犧牲品,不自覺地受到壞趣味的折磨,在對大眾文化不斷重復(fù)的程式的虔誠中像機(jī)器人一樣。[4]”加拿大學(xué)者達(dá)拉斯·斯密塞提出的“受眾商品化”概念認(rèn)為閱聽人是一種商品,是傳媒工業(yè)的勞工,為傳媒工業(yè)生產(chǎn)著剩余價值。美國學(xué)者艾琳·米漢將其解釋為:“傳媒真正出售的不是閱聽人,而是收視率和點(diǎn)擊率。[5]”因此,從這種控制論對大眾傳播的闡釋中可以進(jìn)一步看出受眾作為個體及其文化審美需求心理受到了媒介控制的解構(gòu)。
(四)傳媒從業(yè)者職業(yè)操守的淪喪
后大眾傳播時代下,保持良好的職業(yè)操守仍然是每一個傳媒從業(yè)者最基本的職業(yè)道德。這不禁就會讓人聯(lián)想到去年的陳永洲案。陳作為《新快報》的記者,受人指使和在錢財?shù)尿?qū)動下,未經(jīng)核實(shí)地發(fā)表大量有意詆毀中聯(lián)重科的失實(shí)報道,導(dǎo)致其聲譽(yù)和股民嚴(yán)重受損。眾所周知,記者必須堅持新聞?wù)鎸?shí)性原則,堅持不搞有償、虛假和欺詐報道的從業(yè)底線,陳的行為嚴(yán)重違背了新聞記者的職業(yè)道德,嚴(yán)重?fù)p害了新聞媒體的公信力。但整個事件又不是陳一個人能操作完成的,其所屬的報社也難辭其咎。陳也表示,“主要是貪圖錢財和為了出名才這樣做的,自己被利用了。”都是誰在利用他?又是誰向他提供現(xiàn)成文稿,其目的何在?在這條黑色利益鏈條上,陳也許只是個小卒子[6]。幕后黑手到底是誰?這不得不讓人深入追索。
無論從個人還是利益集團(tuán)的角度來審視整個事件,都可以肯定那雙無形的最大黑手就是“金錢”,由此可管窺到資本對大眾傳播的滲透。虛假謠言、侵犯隱私、涉及色情和暴力等違背傳播倫理的不良信息已然成為一些大眾傳媒吸引關(guān)注度的常用手段。資本強(qiáng)勢進(jìn)入并參與新聞生產(chǎn),這反映了公共空間的政治功能和經(jīng)濟(jì)功能發(fā)生改變。大眾傳媒在某種意義上已經(jīng)是霸權(quán)代碼的生產(chǎn)者,隱匿在其背后的商業(yè)關(guān)系、公共關(guān)系和權(quán)力關(guān)系極為復(fù)雜。傳媒的資本化運(yùn)營正在嚴(yán)重影響著傳媒從業(yè)者的道德判斷和價值取向[7]。而大眾傳播中人文精神的涵養(yǎng)和傳承就承載于每一個信息把關(guān)人、媒介從業(yè)者的職業(yè)道德之中,所以人文精神是新聞從業(yè)者的自律精神,也是媒介的自由和公信力的強(qiáng)大支撐和不竭活源。
四、重構(gòu)基于人文精神的大眾傳播
面對大眾傳播人文精神缺失的危機(jī),五個方面可以作為重構(gòu)人文精神的主要對策。
(一)樹立“以人為本”的傳播價值觀
傳播價值觀是大眾傳播的基本立場,是整個傳播活動的出發(fā)點(diǎn)和落腳點(diǎn)。大眾由千千萬萬的個體“人”組成,他們并非一群被媒介或某些力量操作的愚昧分子,他們有血有肉,他們有自己的情感和感受,更有人性最美好的光輝,所以要牢牢把握“尊重人性”這一最基本的出發(fā)點(diǎn),在傳媒的生產(chǎn)鏈條中傳遞人間真情,弘揚(yáng)社會道義,用媒介的傳播力量去溫暖這個冰涼的世道,去關(guān)懷那些弱勢的人群,想他們所想,急他們所急,真切地走進(jìn)他們的生存現(xiàn)狀,真切地領(lǐng)悟媒介傳播的真諦所在。想必只有這樣,傳播的價值才能最大化,媒介的價值傳播和認(rèn)同才能更加牢靠和廣泛。
(二)將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相融合
商業(yè)性和娛樂性是大眾文化的兩個重要表征,但往往由于商業(yè)性的作怪,娛樂性就被無限地放大,甚至膨脹、泛濫,變異為大眾文化所無法克服的平面性、膚淺性、媚俗性等自身局限。其實(shí),大眾文化固有的娛樂性具有很大的進(jìn)步意義,比如,娛樂性強(qiáng)調(diào)人人參與,共同分享,這極大地體現(xiàn)了大眾文化相較于精英文化的廣泛民主性,同時那種刻板的嚴(yán)肅的精英文化在現(xiàn)代人的精神高壓下,完全不能給予普通大眾精神上的徹底愉悅和短暫休憩,所以,大眾文化的娛樂性充實(shí)了人們的閑暇時間,緩解了現(xiàn)代人的精神壓力[8]。但這并不代表我們要徹底拋棄精英文化,反而在大眾文化娛樂化泛濫的當(dāng)下,我們更應(yīng)該發(fā)揮精英文化的高雅性和藝術(shù)性,用更高的道德準(zhǔn)則和藝術(shù)要求來改良過分娛樂化的大眾傳播內(nèi)容,給大眾文化洗洗澡,去去銅臭,使其發(fā)展更能適切社會健康的進(jìn)步和人們良性的精神需求。
(三)以媒介的自律和他律促進(jìn)健康傳播
受眾、媒介、經(jīng)濟(jì)和社會四者在理念上構(gòu)筑了傳播生態(tài)的整體協(xié)調(diào)和有序發(fā)展。傳播者、媒介、受眾、信息四者間的優(yōu)化組合是傳播生態(tài)平衡的重要前提。健康傳播也正基于以上理論前提,倡導(dǎo)公共精神,弘揚(yáng)社會道德,預(yù)防和消除信息污染和傷害,規(guī)避暴力信息的過度傳播以及形勢、技巧的濫用對人身心健康和社會精神文明建設(shè)所造成的傷害。而實(shí)現(xiàn)的路徑就是要大力加強(qiáng)媒介的自律和他律。一方面,堅持媒介自律和新聞專業(yè)主義。重視道德力量,強(qiáng)化自我監(jiān)督和自我調(diào)整。譬如在報道暴力信息時,不渲染不夸大,不過度描述犯罪細(xì)節(jié)來吸引關(guān)注,而是站在本著客觀事實(shí)的基礎(chǔ)上,探討更多深層次的意義,引導(dǎo)受眾進(jìn)行理性思考。同時,還要有良好的傳播品味,以道德責(zé)任和公眾利益作為傳播的準(zhǔn)繩。而新聞專業(yè)主義作為媒介自律的重要保證,在信息傳播尤其是新聞報道中更要注重客觀性,杜絕個人偏見,以冷靜的方式向世人還原或呈現(xiàn)最接近真相的事實(shí)。另一方面,媒介生態(tài)的良性發(fā)展還需要外部力量的監(jiān)督和制衡,比如建立健全相關(guān)的信息傳播的法律法規(guī),接受廣大受眾的監(jiān)督,發(fā)揮市場競爭機(jī)制的優(yōu)化作用等。
(四)強(qiáng)化媒介議程的追責(zé)功能
大眾媒介除了政治、經(jīng)濟(jì)等功能外,其重要的社會功能何在?這是值得每一個傳媒人深思的問題。媒介在科技猛進(jìn)和信息井噴的今天應(yīng)該如何發(fā)揮自身的議程設(shè)置功能就是大眾傳播中重構(gòu)人文主義精神的重要一環(huán)。媒介的偉力就在于它能傳遞最有力的信息,引導(dǎo)最廣泛的輿論;媒介是社會輿論的高地,誰先占領(lǐng)誰就把控了社會的人心動向。媒介從業(yè)者作為信息的“把關(guān)人”篩選貼合各方需求的信息進(jìn)行加工處理,并通過媒介傳遞給大眾,按照符號學(xué)的理論,這就是一種符號化的景觀社會的布景,受眾通過這些已被人為設(shè)置的信息來做出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rèn)知和判斷,這也體現(xiàn)了一種媒介的控制論原理。那么在人文精神的構(gòu)筑中,新聞傳媒是否可以對社會中但凡有關(guān)弘揚(yáng)人道、發(fā)揮人性的社會事件和新聞熱點(diǎn)進(jìn)行凸出報道和大力宣傳呢?比如從重大公共事件、社會詬病、百姓民生以及愛心義舉等方面進(jìn)行深刻的批判性報道和正能量的積極傳遞,從而教育受眾以人文精神并引導(dǎo)受眾深思人文精神的核心內(nèi)涵。
(五)積極發(fā)揮受眾的主觀能動性
霍爾的編碼——譯碼理論解析了公眾對媒介霸權(quán)的解碼能動性。以此理論,受眾作為文化的消費(fèi)者,完全有可能發(fā)揮解碼的主觀能動性,促使文化產(chǎn)品轉(zhuǎn)化為自己所希望接受的形態(tài)[9]。大眾傳播意義的完成在于受眾對信息的接收和解讀,受眾也是意義生產(chǎn)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沒有受眾的參與就沒有傳播意義的存在,所以,一場成功的大眾傳播必須是由受眾和媒介共同構(gòu)成的。可見,受眾不是完全被動的和麻木的,受眾具有一定的選擇性、能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那么,反觀大眾傳播的三個主要角色和環(huán)節(jié),我們是否可以考慮不單單從傳播者和媒介這兩個方面還可以從受眾的角度來尋求解決人文精神在大眾傳播領(lǐng)域缺失的解決之道。比如可以對受眾進(jìn)行人文素養(yǎng)的教育,探求受眾解讀信息的內(nèi)在規(guī)律以及如何讓受眾準(zhǔn)確無誤地理解傳播者傳播信息的意圖,培養(yǎng)其正面的信息消費(fèi)需求。
參考文獻(xiàn):
- 百度百科.人文精神[EB/OL].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0585/5069943.htm?fr=aladdin
- 曾慶香.淺析媒體人文精神的建構(gòu)[J].新聞前哨,2004(9).
- (美)N·波茲曼著.章艷譯.娛樂至死[M].南寧: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
- (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納蒂著.閻嘉譯.通俗文化理論導(dǎo)論[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1.
- 李亞祺.審美的娛樂化---淺析大眾傳播媒介對文學(xué)批評詩性內(nèi)核的消解[J].絲綢之路,2013(2).
- 長沙警方:陳永洲已供認(rèn)受人指使收人錢財[N].新華每日電訊,2013-10-27.
- 劉新榮.大眾傳播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與重構(gòu)[J].當(dāng)代傳播,2007(19).
- 孫葉飛.大眾文化的人文關(guān)懷[J].理論導(dǎo)刊,2005(24).
- (英)約翰·費(fèi)斯克.理解流行文化[M].倫敦:安文·海曼,1989.
[責(zé)任編輯:思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