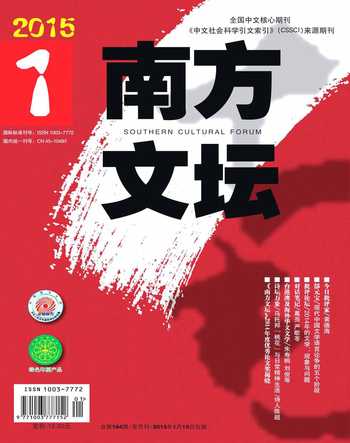異域的位置
近現代以來,中國作家已經積累了不少如何敘述“異域”的文學經驗,從晚清的官員日記開始,實錄精神、反思意識替代了海客談瀛的神話思維,異域的風物制度、人物事件、文化心理等以各種方式進入文本之中,在拓展中國文學表現領域的同時,對作家的審美思維和文本的美學品格等都產生了影響。但我們或是將這類作品簡單歸類為異域風情小說,或是從非文學的角度去探討其異域敘述的意義,很少從創作角度去總結異域敘述的審美意義。在我看來,“探討一個作家如何定位異域、怎樣和為何敘述異域”等問題不但有利于真正發現異域題材小說的價值,也將從深層面上敞開異之于文學創作的意義。
陳謙是旅美華裔作家中的后起之秀,憑借為數不多的幾部小說,她已確立了在當代華文文壇的地位。她的小說,無疑具有地理疆域和文化心理上的游移性,很難鑒定其文本中異域和本土的絕對界限,但其筆下人物的自我意識和空間意識極為清晰,其創作也較為自覺地反思了異域之于自我建構及創作的意義。因此,本文嘗試細讀陳謙的幾部小說,通過梳理其異域敘述的脈絡以探尋作家創作的獨特性,并呈現新一代海外華文創作在表現異域時可能達成的新境界。
異域的抽象指涉:別處的生活
所謂異域,是相對本土或故鄉而言的,在具體層面,它可以指向某個特定地理疆域的風景人事;在抽象層面,則可以賦予各種寓意和象征。在陳謙的作品里,具體層面的異域在其文本中已經朝兩個方向延展,一是美國,一是中國。若從陳謙小說的敘事主體來看,異域首先指向美國。借助那些在中國度過青春歲月再移居美國的華人,文本反復追問美國經驗對這一代旅美華人的意義,追問諸如“他們為什么要離鄉背井,在美國又是否真正擺脫了生存困境?”等問題。對于這一類華人而言,故鄉永遠是中國的某個地方,而美國則意味著截然不同的時空和處境,是異域。從早期《愛在無愛的硅谷》里的蘇菊、《覆水》里的依群、《望斷南飛雁》里南雁、沛寧、王鐳到晚近《蓮露》里的蓮露,都是在美國哪怕飛得再高,中國的故土經驗也無法抹去的人群。而陳謙小說中另一些人物眼里的異域,則又變回中國。2002年發表的《覆水》中,老派的美國人老德和新一代的知識精英艾倫都將從中國來的依群作為遙遠中國的投影和化身。2013年發表的《繁枝》和《蓮露》中,在重回中國創業的旅美華人志達、朱老師眼里,改革開放的中國也成為具有誘惑力和未知數的異域,再次改變了其人生軌跡和生活信念。不過,陳謙小說中,無論關于美國還是中國的具體指涉都非常有限,所涉及的地點、風景和人事雖然也有具體的空間線索可尋,卻不以事無巨細的客觀再現見長。這種具體層面的異域呈現方式,既無法與專注再現的現實主義傳統比美,也無法與近現代集觀看、體驗、反思于一體的風土記、游記文學匹類。
事實上,與其說陳謙是從具體層面展現我們通常所謂的“異域”,不如說她已經從抽象層面對之重新定位與命名。早在《覆水》中,陳謙借助女主人公依群在困境中的兩次突圍,提出了“生活在別處”的命題并對之作了反思。如依群一樣,人們在遭遇困難時,總將希望寄托在遠方,希望通過出走來實現人生的轉變,然而,當別處變成了此處時,我們一樣跌落生活的繁塵之中,一樣遭遇人生的諸多挫折。那么生活的意義到底是在別處還是在此處呢?此處的生活與別處的生活真的大相徑庭嗎?這一連串的問題由陳謙在《覆水》中提出并嘗試回答,但此時陳謙對異域意義的探索還剛開始,立場尚未堅定。一方面,她讓依群喊出“生活在此處”的口號,告誡人們要珍惜自己所擁有的;另一方面,依群又處在無法回頭的宿命之中,只能再次踏上未知的追尋之路。在后來的小說中,陳謙的天平已經傾向于選擇“別處”,“去遠方”變成了她筆下人物的共同抉擇。《望斷南飛雁》中,南雁離開安適的中產階級家庭生活,去更遠的南方完成學業,尋找自我生命的價值;《蓮露》中,蓮露為了擺脫心靈的痛苦和記憶的傷痕,朝海的盡頭奔去。《繁枝》中的錦芯選擇了自我放逐,飄然于熟悉的人群之外。雖然出走是現代人為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衍生的基本生活方式,但陳謙卻將之看成是人的宿命,在別處尋求生命新的可能,成了必然選擇。由此可知,當她將異域定位成“別處的生活”并賦予其體現生命內在價值的意義時,實際是將異域抽象成了具有普遍性內涵的所指——人在現實困境中尋求的希望之境。
這種帶有形而上意味的異域觀,遠遠超越了近現代風土記和游記的異域定位,也超越了1960年代到1990年代留學生文學、新移民文學中的異域觀。近現代以來的風土記和游記中,往往呈現具體而微的異域空間,未能對其進行抽象的思考。而1960年代到1990年代的留學生文學、新移民文學中,異域作為與中國對立的異質空間,常常象征著政治霸權等否定性的固化意象。上述文學創作中,其異域思維模式都建立在中西二元對立的語境之上,從而使得一些有關華人移民的虛構性文本不自覺地陷入了民族寓言的審美模式:“文化沖突成為基本的敘事動力,個人的悲歡離合被放大成民族國家的整體遭遇。”新世紀以來,一些海外華文創作慢慢遠離了這種舊俗的審美模式,做出新的探索,陳謙就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代表。對于陳謙來說,中國經驗和美國經驗都是異常重要的創作資源,其小說敘事幾乎無法避免呈現本土與異域、故鄉和異鄉這樣的空間結構;但通過賦予異域更為寬泛靈活的普遍指涉,陳謙將自己的創作從民族寓言的審美模式中釋放出來。當異域指向的是“別處的生活”時而不是特定國家民族的投影時,敘事的視角也更容易從“文化空間(包括民族屬性、國籍身份等)的變動在個體生活中的投影”轉化為“個體在變動的生活空間里之心路歷程”,宏大的空間敘事就變成入微的心靈敘事,由此,涉及本土和異域雙重空間結構的小說就成為探索個人心靈之旅的場域,不再被國家民族的先驗性敘事框架所局限。
關于陳謙小說“向內看”的特質,旅美學者陳瑞琳有專文論述,她認為陳謙小說是以女性作為載體找到了通向靈魂的藝術通道①。我想對她這一表述加以補充。其實陳謙選擇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女性故事,而是一個個輾轉異國他鄉、尋找自我的女性的故事。如果陳謙意在表現“人”這個命題,必然如陳瑞林所言去“呈現靈魂的痛苦掙扎”②及在痛苦中自我的成長;那么,她讓人物在新的生存空間遭遇新的挑戰,讓生命的韌性和人性的復雜程度在變動的生活空間里得以呈現,也是一種值得稱道的藝術策略,更是一個旅居國外的華裔作家的自然選擇,因為這些女性所能具有的靈魂重量,是在她的經驗范圍之內的。陳謙曾經說過,“在海外遇到的女性,去國離家,走過萬水千山,每個人都走過很難的路,將自己連根拔起,移植到異國他鄉。所以我身邊的女生都很厲害,沒有那種很強的意志力,是走不遠,也無法存活的。”③嚴格地說,陳謙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在她筆下,無論男女,在新的生存空間中都有著同樣的困惑,同樣體現了追尋的勇氣。如《望斷南飛雁》中,無論是沛寧還是南雁,都將美國作為實現自己夢想的空間,在美國數年的奮斗歷程中,他們都面臨著莫大的壓力,表現出極大的勇氣、耐性和干勁。對移民來說,異域都是比故鄉更重要的成長空間,《望斷南飛雁》中,正是在美國,沛寧和南雁才各自成為自己。
如果出走是人的宿命,那么,對以創作來思考生命奧秘的作家而言,將異域作為追尋者自我設定的烏托邦就是合理的敘事策略。正因此,“主人公離開熟悉的此在,奔向未知的異在”成為陳謙小說的基本敘事模式;呈現“在異域中生命的掙扎”也成為陳謙小說探索生命意義的重要審美手段。可以說,由于賦予了“追尋”以本然的意義,“異域”在陳謙小說中呈現出一種形而上的崇高感。當然,作家不是直接使用這一詞語,而是將之重新命名與詮釋,并使之內化在小說敘事之中,它的位置是穩固的。
異域的淡筆描摹:再現的簡化
異域在中國近現代作家的筆下,主要以幾種方式呈現。一是隨意化,作家無意中將自己所熟知的某種異域元素散落在其文本中,還談不上對異域進行自覺再現與概括;二是景觀化,作家將所見所聞或如實記錄或略加選擇,呈現人類學式的日志或浪漫主義的奇觀;三是生活化,作家在文本中主要呈現異域生活的日常層面,風景退居其后,人事變成了主體。陳謙的異域呈現方式接近第三種方式,又有自己的特色。
陳謙小說中異域呈現方式的獨特性在于,她所呈現的生活空間看似具有紀實性,實際是一種再現的簡化,具體而言,是她以選擇性的點染筆法提供一種接近生活常態的空間感覺,但在看似現實主義的風格后隱藏著象征化的現代主義思維。她說:“我并不喜歡魔幻現實主義對現實時空的組合方式,像那種魔幻現實,那種重構的A城、B城那種,不是我的個人的風格能所親近的。每個作家的選擇不同,我就喜歡一種很清晰的,有個人標記的東西,各人的來歷才搞得清楚,我是這樣想的。”④在她筆下,的確沒有出現純粹虛構的地點和扭曲的空間想象,出現的都是舊金山、硅谷、廣西北海、廣州之類的真實地點;活躍其中的人也接近生活常態,缺乏傳奇色彩。這看似與寫實傳統的再現方式一致,其實不然,在陳謙小說中,像巴爾扎克式精雕細刻的場景建構和風俗人物描寫是找不到的。事實上,異域的元素,無論是風景還是人事,在她的小說中都以服從敘事需要的白描筆法來簡約呈現,以一種隨主人公情感流動的方式來安放運轉,淡筆描摹的場景和人事都成了有意味的形式,具有象征性和儀式性,符合的是現代主義的隱喻原則。如《覆水》中,提及依群和母親旅行經過美國西部最大的哥倫比亞河時,并無這河景致的一字描寫,而僅將之作為連接父親投江自盡的節點,以這浩浩湯湯的河引發了母女倆對難以捉摸的生命歸宿的哀嘆之情。就是在描寫美國景致較多的《望斷南飛雁》里,渲染那場冰天動地的尤金城的大雪、那綿綿不絕的舊金山的寒雨,都只為映襯主人公沛寧此時的心境,少見客觀的筆墨。一些海外華文小說里濃墨重彩呈現的異域生活場景和異族情人,在陳謙的筆下也不過寥寥幾筆、色調淡雅。如《覆水》中的美國工程師老德、職業規劃師艾倫、《蓮露》中的風險投資家吉米·辛普森,都是以氣質、精神人格取勝,少見精細的再現式描寫。試看:“那個叫辛普森的老頭齊刷刷的灰白短發,著深黑緊身運動衫,身板筆直地站在一艘神氣的帆船前端,正抬手摘取架在頭頂的太陽鏡,一臉由衷開心的笑容,順著臉上那些因常年戶外運動曬出的深紋四下散開,讓他的臉相顯得立體有力,跟我在沙沙里多水邊撞見的時候幾乎一模一樣。”⑤
必須指出的是,陳謙小說有關異域的元素雖以淡筆描摹,可不乏力度,其審美效果恰如中國畫里的鐵線描,力透紙背。如《望斷南飛雁》里的那場大雪和大雪中駕車獨自行駛在路上的南雁,水乳交融,精彩地呈現了一個在異域環境中獨自跋涉的女子之精神境界。《覆水》里寫中國女孩依群初次見到美國工程師老德時,只有以下兩句:“老德足有一米九的個子,正值壯年,身子骨十分硬朗”⑥,此時只突出他身體的健壯,而不涉及其他特征,顯然是經過選擇的。因為當時犯有心臟病的女主人公依群所向往的只是健康而無其他,故她只看到異族男人壯碩的身體;但后來正是老德的年老力衰造成了兩人婚姻的困境,這一描摹又成為具有諷刺意味的伏筆。在陳謙小說中,這種頗見功力的描摹方式處處可見,使得其異域敘述的細部與小說的整體訴求十分協調,可以承載豐富的內涵。
以“再現的簡化“方式來呈現異域,無疑是陳謙追求簡約的審美風格的體現,在她看來,簡化反而有利于確立一種真實感。她說:“為了使小說看起來更‘真,我必須去掉真實生活里更為復雜的戲劇性元素,因為我清楚地意識到,如果遵循‘忠實于生活的老話,善良的讀者甚至可能拒絕小說的‘真實。”⑦的確,點染式的白描筆法,去掉了那些帶有偶然性的、難以賦予意義的元素,突出了那些能夠凸顯主題的細節,從而可以確立起一種審美的主體性。
但這種異域呈現方式,與陳謙異域經驗的性質不無關系。一般而言,對于剛剛踏入異域的移民而言,他們容易感受到來自差異空間的瑣碎景觀,產生的感情體驗也往往比較極端,異域在其創作中容易被前景化,成為推動敘事、改變人物命運的突出因素。如《芝加哥之死》《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北京人在紐約》《到美國去,到美國去》等作品中,異域都是敘事的焦點,是處在舞臺中心的形象。這種對異域的審美設定,往往催生戲劇化的情節結構、呈現片面膚淺的異域經驗。如《北京人在紐約》中的主題歌如此唱到:“如果你愛一個人,就送他去紐約,因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個人,請送他去紐約,因為那里是地獄。”⑧將紐約安置在天堂和地獄這兩個極端,將之作為主要人物命運極速沉浮的隱喻,體現了被前景化的異域和戲劇化效果之間的內在關聯。但這種過于粗暴的異域呈現方式,逐漸被成熟的移民作家所舍棄,尤其是對那些深入其中,安穩下來的移民作家,他們的異域定位、觀察方式及表達方式都在發生變化。陳謙從事小說創作時,已人近中年。在中國度過了最難忘的青春歲月,對“文革”也存有模糊的記憶;在美國也走過了留學打工的最初階段,進入技術精英薈萃的美國硅谷當上了工程師,過上了中產階級的生活。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她都有了更為全局深入的把握,因此,在她對有關異域的抽象化認定中,兩者都可以是反思回望中的異度空間,但兩者都不可能是黑白分明的戲劇化場景,而是意味深長的生活世界。
陳謙的異域呈現方式,還可從寫作目的的更高層面尋求理解。她的寫作,可視為一種宗教性寫作。每一篇小說,都在呈現靈魂的苦痛、尋找生命可能的救贖之途;恰如面向神父、也面向天父的懺悔禱告,在為迷失的人們招魂。這種懺悔禱告式的意義構造,決定了其文本的外在形式。小說往往采取特定人物的單一視角來展現情節、結構全文,在該人物的回望追憶中,不同時空中的諸多細節被連綴成整體以構建探幽人性迷宮的生活空間。這種近乎意識流的時空組合方式,使得為表征人性復雜性而出現的異域也成了點染式的背景。實際上,因為陳謙小說的聚焦點是呈現“某種人生的困局與生命的困惑”,文本的諸多元素包括故事情節和人物都是淡出的背景,更遑論異域因素。但是,既然小說試圖呈現人性的幽微掙扎,那么作為考驗、表征人性的背景而出現的異域并非可有可無。一方面,如前所述,人的苦難總是在變動的環境中得以呈現,異域作為對人性考驗的實際存在意義非凡;另一方面,宗教性寫作需要依賴特定文化空間才得以存在,就好比懺悔祈禱中的教堂,作為儀式性的背景確保了心靈的聲音暢通無阻。無論是《望斷南飛雁》里沛寧茫然若失的懺悔錄,還是《特蕾莎的流氓犯》里紅梅雜亂無章的心靈囈語,都只有依托基督教文化的異域背景才具有了鋪展的可能性。
當然,在資訊、交通極度便捷的時代,各種空間元素的水乳交融、不同國家族群的人流交匯已成常態,文學中出現異域景觀已是極為自然的現象,根本無須戲劇化、前景化。如此看來,陳謙的異域表達方式也折射了時代的感覺結構。
異域感:一種審美
距離和觀察視角的根源
我們已明白,文學不需也不能作為認知異域的主要方式;如果對異域的再現復制不是目的,那么對它的想象和借用將給文學帶來什么呢?現在,我們從陳謙的創作入手嘗試對以上問題進行總結。
如前所述,一方面,陳謙小說中的異域是以點染筆法勾勒出具有抽象指涉的背景,在這一具體指涉漂浮不定的背景之上,文本重在探索有關人和人性的種種疑惑與思考。另一方面,其小說中本土與異域的空間結構是穩定的,異域雖不是聚焦點,也不是目的,但卻內化在其敘事結構之中,成為不可或缺的成分。如何理解陳謙小說中異域敘述的矛盾性?
在我看來,文學創作的價值,除了依附作家個人的寫作才華之外,也會與思想立場、觀察視角等有關聯。某種程度上,文學的價值就在于能以審美的方式提供與眾不同的觀察方式和思想立場。而海外華文作家的獨特性在于,在本土和異域的空間構造中,他們將自己放在游移不定的中間位置,以自身為聚焦點,不但可以更換本土與異域的位置,更能確立了一種有利于審美觀照的疏離感,這使得他們擁有了與本土作家迥異的觀察視角,很多海外華文創作的審美價值正是從這一中間性位置生發出來的。也就是說,與其說這些作家要再現某個具體的異域空間,不如說他們要借此確立一種異域感,進而形成獨特的觀察視角乃至表達方式。陳謙小說所具有的獨特魅力,也在這一視野之中;理解陳謙小說中異域敘述的矛盾性也要從此開始。
從陳若曦的《尹縣長》開始,海外華文創作就以獨特的觀察視角和思想立場深入了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當下反思之中,顯現了以凸顯人性的復雜幽深為宗旨的趨勢⑨。陳謙的小說《特蕾莎的流氓犯》《下樓》《蓮露》等也被歸屬其中。如宋炳輝認為《特蕾莎的流氓犯》的敘事特色正是“借助異文化場域來反顧本土歷史與文化”⑩。但是,陳謙文本中的異文化場其實在中國和美國之間游動,恰恰是在對兩種生存空間的雙重審視與批判中,其小說從自我存在的角度呈現“人無家可歸”的悲劇性。我想,這正是陳謙小說具備感人至深之藝術魅力的重要原因。
小說《覆水》中,陳謙嘗試以文化差異來構造人生困境,敞開靈魂的苦痛和掙扎過程。華裔女子依群和美國男人老德的婚姻因生理的不和諧而名存實亡,但他們都在苦苦支撐著這一局面。如果說依群是受了知恩必報的中國文化傳統的約束,老德則是為了信守當年與依群姨媽相伴一生的約定,無論是報恩的中國傳統人倫還是西方的婚姻契約,都給兩個人帶來了傷痛和孤獨。依群和另一位美國男子艾倫的邂逅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情感故事,敞開了另一種異域生存困境——文化溝壑造成的情感交流滯礙。職業規劃師艾倫帶著專業主義的興趣,走進硅谷麗人依群的生活,但他們之間存在一種無形的文化阻力,表面意氣相投、實則無法深入交流。當依群明了他們關系的癥結所在時,選擇了退回原位,原本躁動的心也變得更加脆弱焦慮。《特蕾莎的流氓犯》中,陳謙的技法和思考更加成熟,文化空間的印記及其與個人命運的糾葛都透過人物內心的瞬息變化被聚焦。在女主人公紅梅(特蕾莎)的黑暗之心中,中國“文革”時年少的她犯下的誣告罪和在美國接受基督教洗禮后的懺悔意識相互糾纏,使她一直處在罪與罰的陰影之中,不得安寧。她心存僥幸,以為只要向受害者道歉,得到對方諒解就可以獲得新生。但說出來又怎樣?當她向中國來的王旭東訴說了一切時,心中的怪獸仍呼嘯而來,心靈仍在荒漠之中。另一悔過者王旭東費盡周折得來的“文革”紀實,盡管真實動人卻無法撫慰自己、更不用說撫慰他人。無論是中國式的立此存照主義還是基督教的懺悔精神,在陳謙筆下,都未必讓沉重的心靈得以解脫。
在稍后的《繁枝》和《蓮露》中,陳謙對技術理性主義主宰的美國和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進行更為清晰的雙重審視和批判。她筆下的美國硅谷是一個冷冰冰的機器世界,人們在狂熱地投入技術革新、創造財富的世代潮流之時卻喪失了生活的激情。改革開放的中國則是沒有底線的花花世界,將人的靈魂拋入無底深淵。《繁枝》中女主人公錦芯的丈夫志達,在美國硅谷依靠個人奮斗擁有了不菲的財富、完整的家庭,可依然找不到歸宿感;隨著海歸潮到中國創業,抱著重新來過的勁頭,全力投入到一場婚外戀中,美國的精英教育、夫妻的患難經歷、幾個兒女全被拋在腦后,剩下的只有被解放的欲望。《蓮露》中,女主人公蓮露的丈夫朱老師,借助美國文化氛圍擺脫了處女情結,與妻子和諧共處了幾十年,但一回到中國就舊病復發,在傷害妻子的同時,自己也走上墮落之路。而原本可以讓蓮露打開心結的華裔心理醫生,嚴格遵守不與病人產生任何私人聯系的治療準則,在她即將走上康復的半途中將之拋給無常的命運。這一小說,作者或許本意在試圖呈現人無法戰勝自我的困境,但客觀上卻也批判了中國可笑的處女情結、反思了西方的理性原則,某種意義上,正是它們聯手毀掉了一個原本可能璀璨的生命。
如果個體就算游走于中西之間也無法擺脫困境、如果出走或回歸都無法獲得心靈的平靜,那么,我們的靈魂之所究竟在哪里?當陳謙認識到“人無路可走”的結局后,她有關人的探索還能以怎樣的方式繼續呢?她的創作會舍棄本土與異域的空間結構嗎?《下樓》是陳謙醞釀中的長篇小說的序曲,其中依然存在中國和美國的雙重空間結構,中心情節是:一個女人在愛人墜樓死后再也不下樓,困守在靜止的空間里,直到老死。由此看來,陳謙依然在變與不變的辯證法里思考人的生存空間。實際上,變動的生存空間給予人的影響,是陳謙寫作的原動力。她說,“沒有去美國,我不會寫作,沒有這種環境的變換,人的存在不會有如此大的沖擊。在美國的經歷,打開人的眼界,開放人的心靈,甚至改變人的世界觀。震撼和感慨之后的思考,是我寫作的原動力。”11
我認為,異域感的存在,的確是一個移民作家特有的資源,有才華的作家,會充分挖掘這一來自自身經驗的寶庫。但對不同作家而言,異域在其創作的位置會有所偏差,對其處理方式也有所不同。在陳謙的寫作中,異域恰似一個能劇表演者的面具,已成為一種藝術得以成為藝術的框架,內在于其創作思維之中。其內在性在于,它與敘述主體自我建構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借助異域所具有的投射性和他者性,敘述主體才得以不斷自我確認、自我反思。因此,這個異域面具就算鐫刻出真實時空的某些印記,我們也不可將之作為復制再現的范本,而只能作為滲透著敘述主體印記的心理影像。異域一旦成為作家的表征符號,就像表演者的自我不可能脫離面具而存在一樣,兩者相互疊合,催生了新的主體形象。這樣,異域敘述就成為某些海外華文寫作的重要標簽,其表述方式則可以發生微妙的變化。
當然,對于作家而言,帶上這一異域面具之后,自我的位置也變得模糊歧義,他可能需要不斷重構和反思自己的異域經驗來確認自我及其寫作的位置。對于陳謙等海外華文作家而言,只要處在異域和本土的張力空間,這種自我探尋的懺悔禱告式寫作就不會停止,我們期待的只能是另一種異域表述方式的出現。
小結
在陳謙筆下,作為再現的簡化,異域不只是現實主義的布景與現代主義的符號,而是一種類似面具標示的生活成分和身份要素。與其說作家要再現某個異域空間,不如說她要借此確立一種異域感。異域感的存在,確保了作家對其所書寫的雙重文化空間形成具有疏離感的審美距離和獨特的觀察視角;異域感的存在,也使得創作主體的身份處在模糊不清的邊界,需要不斷重構和反思異域經驗以確認自我及寫作的位置。由此,陳謙的小說獲得了一種越界性的美學特質:心靈世界在空間的斗轉星移中出現令人眩暈的復雜性,古典的敘事方式獲得了一種后現代的精神質地。在以追尋自我、反思人性為主旨的宗教性寫作中,陳謙小說遠離了民族寓言的審美模式,開辟了海外華文文學書寫異域的新境界。
【注釋】
①②[美]陳瑞琳:《向“內”看的靈魂———陳謙小說新論》,載《華文文學》2013年第2期。
③11江少川:《從美國硅谷走出來的女作家———陳謙女士訪談錄》,載《世界文學評論》2012年第2期。
④黃偉林、陳謙:《在小說中重構我的故鄉:海外華人作家陳謙訪談錄之一》,載《東方叢刊》2010年第2期。
⑤⑥陳謙:《覆水》,見《望斷南飛雁》,1、137頁,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⑦陳謙:《〈蓮露〉寫作后記》,載《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2013年第6期。
⑧曹桂林:《北京人在紐約》,28頁,朝華出版社2003年版。
⑨⑩宋炳輝:《陳謙小說的敘事特點與想象力量》,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8期。
(顏敏,惠州學院中文系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華文文學的跨語境傳播研究暨史料整理”研究成果,項目號:13CZW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