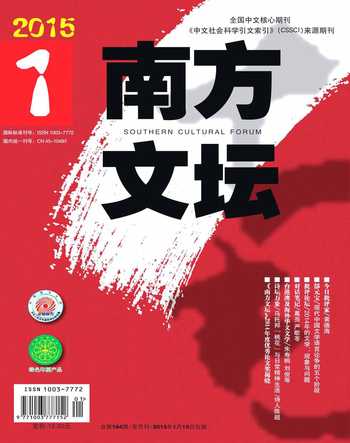近年三種鄉村敘事
劉濤
近年,中國農村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小說對此亦有反應,很多作家關注農村、農民問題,老中青三代作家均有力作推出。通觀這描寫農村的小說,計有三類,各呈現出不同的農村風貌,也表現出作者不同的志向和趣味。
第一類是“三農”問題視野下的農村,這一類強調了農村存在的社會問題,描寫鄉村的凋敝破敗、精神危機、矛盾沖突等,譬如孫惠芬的《生死十日談》、摩羅的《我的村,我的山》和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等。第二類寫農村之美,他們筆下的農村是和諧安靜的,充滿山水田園之趣,農村有隱逸的高人、奇人和古老的智慧,譬如韓少功的《山南水北》、馬笑泉的《巫地傳說》和凸凹的《玉碎》。第三類介乎第一類與第二類之間,他們筆下的農村盡管貧窮艱難,但也有堅韌積極的一面,其筆下的諸多人物充滿著光輝,譬如曹乃謙的《到黑夜想你沒辦法》、李進祥筆下的農村世界及尼瑪潘多的《紫青稞》。
一、“三農”視野下的農村
2000年前后,經過曹錦清、李昌平、溫鐵軍等推動,“三農”問題逐漸引起社會各個階層關注,成為公共話題。1996年,曹錦清兩度赴開封作田野調查,研究農民情況與農村的問題,其中為農民家庭算的一筆收入、支出賬非常令人震驚①。2000年3月,李昌平上書朱镕基總理,反映湖北農村的問題,提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引起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關注②。于建嶸的《岳村政治》寫于2000年前后,談農村的問題和政治等,其《安源實錄》調查始于2001年五一節,關注工人命運變遷。2003年,《中國農民調查》出版,以報告文學的方式揭示了農村問題。2004年《當代》第5期發表了曹征路的小說《那兒》,由此引發“底層文學”的爭論。
近幾年,反映農民問題的文學作品逐漸增多,但描寫農民經濟困境者多,關注農民精神世界者頗少,《生死十日談》(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則是二者兼之。孫惠芬以自殺為突破口,既關注了農村的物質生活,也關注了農村的精神世界。
孫惠芬的《生死十日談》討論農民自殺問題。人,尤其是重要人物,為何自殺一直引人矚目。晚清以來諸多自殺事件,陳天華、梁巨川、王國維、陳布雷、老舍、海子等人的自殺等均曾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引諸多人進行研究、討論。1980年代,加繆哲學流行,關于自殺的研究一度頗為盛行。1980年代末,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研究詩人自殺,剖析深層原因,曾一紙風行。重要人物的自殺背后原因復雜,由其自殺或能見出重要的消息。據說,他們的自殺極具象征意義,事關重大。農民或地位卑微,他們的自殺牽動不了重大歷史事件,也無精彩的政治、學術八卦,故盡管農民自殺事件層出不窮,但關注者甚少。用孫惠芬的話則是“他們就像秋天枝頭凋零的樹葉,飄搖著墮入大地,之后悄悄地歸于寂然”。孫惠芬將這些“墮入大地”的“凋零的樹葉”收攏起來,歸為一束,以文學的方式寫出,或能引起社會關注與關懷。
《生死十日談》扉頁上寫著“在中國,80%以上的自殺死亡發生在農村”,此言觸目驚心。農民自殺比率如此之高,關注度卻如此之低,孫惠芬以文學作品的方式揭起此問題之一角。《生死十日談》通過調查農民自殺問題,展現農村問題,揭示農民精神世界,反映了農村現實。
關于此書寫作緣起,孫惠芬說:“得以接近這些悄然隕落的生命,得感謝我的好友賈樹華。她是濱城醫科大學醫學心理學教授。她拿到的第三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就是做農村自殺行為的家庭影響評估與干預研究。關于農村自殺死亡者及其自殺遺族的研究和預防課堂,樹華已經做了十二年之久。她帶了自殺研究與預防課題組五個研究生,剛入秋就深入到翁古城的村村屯屯。我和丈夫張申一同加入了這個團隊。”由此機緣,孫惠芬直面了農村自殺現象,得以和自殺者的家屬、鄰居等有所交談、交流。賈樹華教授和她的團隊以心理學方式解釋、研究農民自殺問題,孫惠芬則以文學的方式呈現農村自殺現象及背后原因。《生死十日談》乃實錄其事,可謂之報告文學或“非虛構”。記錄就是力量,若沒有孫惠芬這支筆,這些故事將會很快零落成泥碾作塵,無人顧及。
《生死十日談》之名大致可以見出此書主體,“生死”言自殺問題,每一起自殺事件結局相同,但具體人物、具體原因不同;“十日”蓋因孫惠芬與丈夫加入此研究團隊,采訪、整理、分析自殺案例,前后歷時十天;“談”乃對談,孫慧芬在作品中處于采訪者的地位,她摸到線索之后,讓與自殺當事人有關的人直接出場,讓他們陳述、訴說,通過他們展現自殺事件前因后果,由此也帶出了農村的現實和面臨的困境。
《生死十日談》記錄了多起自殺事件,這些事件各個不同,或因婆媳爭端引起自殺,或因丈夫拋棄妻子,導致妻子自殺,或因買樓引起家庭爭端,有奮斗進城的大學生因失戀而自殺,或因家庭內部糾紛引起自殺,或因社會壓力過大自殺等。原因不一而足,大致可歸于經濟問題、情感問題、社會壓力等。孫惠芬以寫實之筆,展示了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與影響等。
《生死十日談》除了講述自殺者的故事之外,還寫及賈樹華教授的團隊,也談及孫惠芬與張申,寫了他們深入采訪前后精神面貌的變化。孫惠芬等人的貫穿、牽引、分析、議論、抒情固然重要,但不若做得更為徹底,干脆讓渡出自我,純任與自殺有關者說話、講述。
摩羅是一位富有爭議的作家,此前他是自由主義者,2010年作《中國站起來》,忽變為民族主義者。其轉型原因引眾人猜測,但促成摩羅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他對民眾的理解。摩羅說:“我按照書文上的說法,一直把我的母親、我母親的母親、我母親的母親的母親的信仰,看做迷信。……我像所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樣,罵他們愚昧無知,罵他們封建迷信。……我罵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種地、舂米將我養大成人的人。”③此后,摩羅一直致力于理解鄉村和他的父母,也重新審視了自己的立場,選擇與民眾站在一起。
在這個意義上,摩羅《我的村,我的山》就可以得到理解了。摩羅從“國民性批判的大合唱中撤離出來”,“為我的父老兄弟一一立傳”。摩羅將自己定位于“萬家村的巫師”,其使命是溝通人鬼,“代村民說話,代死去的和活著的村民,說出他們的甜蜜和憂傷。”這就是《我的村,我的山》用意所在。
《我的村,我的山》看似與1987年摩羅的《深的山》非常相似,二者都寫深山中的農村生活和農民境況,但其實差別已經極大。《深的山》時期的摩羅對中國社會和世界格局尚無整體理解,他所能寫且擅長的只是身邊的生活;但寫《我的村,我的山》時摩羅視野已變,他不是自發地寫身邊的人,而是通過他們寫農村和農民的處境。
《我的村,我的山》關注的重心是“非正常死亡”的村民,摩羅要代他們發出聲音。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民紛紛涌入城市,這些人在城市中浮浮沉沉,少數得道升天,多數凄凄慘慘,生活于城市的邊緣。其中還有一部分因為種種原因死于非命,每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都有著復雜的原因和沉痛的故事,摩羅將這些一一寫出。逝者很快就會煙消云散,摩羅則希望將這些死者的信息收集起來,立此存照。
梁鴻是高校教授,始以文學評論名。可是她逐漸對工作與生活產生了懷疑與評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自己的工作充滿了懷疑,我懷疑這種虛構的生活,與現實、與大地、與心靈沒有任何關系。我甚至充滿了羞恥之心,每天在講臺上高談闊論,夜以繼日地寫著言不及義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沒有意義。在思維的最深處,總有個聲音在不斷地提醒我自己: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種能夠體現人的本質意義的生活,這一生活于我的心靈、與我深愛的故鄉、與最廣闊的現實越來越遠。”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確實與生活隔了兩層,梁鴻要直面生活。2008年前后,梁鴻暑假回家探親,住在梁莊,難免耳聞目睹了農村的現狀,難免憶起人與物的變遷,不免愴然涕下,因此開始調查農村現實,要寫一部關于農村的書。2010年,梁鴻出版了《中國在梁莊》一書,描寫河南穰縣農村現狀,打動了諸多讀者的心,旋即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在《中國在梁莊》中,梁莊是該書主角,全書記述了河南穰縣梁莊近三十年來的變遷,涉及文化大革命時期、改革開放時期,雖亦涉及歷史,但全書以現實為主。梁鴻通過這本書試圖追問:“從什么時候起,鄉村成了民族的累贅,成了改革、發展與現代化追求的負擔?從什么時候起,鄉村成為底層、邊緣、病癥的代名詞?又是從什么時候起,一想起那日漸荒涼、寂寞的鄉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邊緣忙碌、在火車站奮力拼擠的無數農民工,就有悲愴欲哭的感覺?這一切,都是什么時候發生的?又是如何發生的?它包含著多少歷史的矛盾與錯誤?包含著多少生活的痛苦與呼喊?”梁鴻回到梁莊,要探討這些問題,解答這些問題。
《中國在梁莊》呈現了梁莊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農村留守兒童缺乏家長管教,農民養老、教育、醫療缺失,農村自然環境遭到了破壞,農村家庭的裂變,農民的性生活,新農村建設流于形式等。梁鴻“和村里人一起吃飯聊天,對村里的姓氏、宗族關系、家庭成員、房屋狀態、個人去向、婚姻生育作類似于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調查”。梁鴻通過一個一個具體案例,以小見大,描寫了梁莊的現狀。《中國在梁莊》很多情節令人震撼,留守小朋友游泳屢屢被淹死;王家少年強奸了八十二歲老人,并殘忍地將其殺害;兒童就學率低,梁莊小學變成了養豬場;秀菊懷著夢想,幾度試圖掙脫現實,但磕磕絆絆幾次摔倒,于是說“世界上最壞的東西就是理想”;春梅因為久久見不到丈夫,恍恍惚惚,終于喝藥自殺;光河的兒女被車撞死,以賠償的錢蓋了一座大房子……
《中國在梁莊》是非常好的題目,體現了梁鴻的關切處。她討論的是梁莊,卻有著中國的視野,要以梁莊見出中國,通過梁莊理解中國。梁鴻借梁莊討論了中國的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梁莊可謂中國農村的縮影,它被城市擠壓,正在凋敝、萎縮、衰敗。
梁鴻寫完《中國在梁莊》之后,欲罷不能,又接著寫了《出梁莊記》。《中國在梁莊》寫了梁莊的內部生活,寫梁莊的現狀、留守者的情況,寫了梁莊的變遷;《出梁莊記》則是寫了梁莊之外,寫了離開梁莊在中國各個城市打工的梁莊人的情況。兩書合而觀之,方可見出梁莊內與外的全體。
梁鴻寫完《中國在梁莊》之后,自述道:“但是,這并不是完整的梁莊,‘梁莊生命群體的另外重要一部分——分布在中國各個城市的打工者,‘進城農民——還沒有被書寫。他們是梁莊隱形的‘在場者,梁莊的房屋,梁莊的生存,梁莊的喜怒哀樂,都因他們而起。梁莊的大打工者進入了中國哪些城市?做什么樣的工作?他們的工作環境、生存狀況、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況如何?如何吃?如何住?如何愛?如何流轉?他們與城市以什么樣的關系存在?他們怎樣思考梁莊,想不想梁莊,是否想回去?怎樣思考所在的城市,怎樣思考自己的生活?他們的歷史形象,是如何被規定,被約束,并最終被塑造出來的?只有把這群出門在外的‘梁莊人的生活狀態書寫出來,‘梁莊才是完整的‘梁莊。”④梁鴻則以調查實錄的方式,呈現了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狀態,亦令人震撼。
作《出梁莊記》時,梁鴻循著梁莊人的足跡,去西安,訪南陽,赴內蒙古,下鄭州,走青島,進行探訪、調查。《出梁莊記》亦如此結構全書,以空間分篇章,展現了分布于不同城市中梁莊人的情況。梁鴻在序言中列出了她采訪的時間表,也列出了采訪者的姓名、職業、打工地等,以示實錄,亦示對被采訪者的尊重。
在西安,梁鴻對梁莊蹬三輪車群體進行了深度描寫,展現了他們的現狀、工作之艱辛,打架討生活等,也描寫了部分不法城管分子與之爭利的故事。這一群體有固定的“被報道的形象”,他們是城市的不安定因素,影響了市容市貌,影響了城市的交通,梁鴻則以寫實的筆法顛覆了被報道的蹬三輪者形象,展現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喜怒哀樂、被壓抑的無奈等。在南陽,梁鴻走訪了梁賢生一家。通過深入交談,才知道他們在南陽異常艱辛,梁賢生幾起幾落,最終勞累致死。在內蒙古,梁鴻走訪了校油泵者,表現了他們的生存現狀、子女受教育情況,尤其對外地務工人員相親情況的描寫讓人慨嘆。在北京,梁鴻描寫了幾類人,有人雖有體面的工作,但過著艱苦的生活,有人噴漆,吐出來的痰都是綠的,有人發了財,成了腰纏萬貫的大老板,但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個人都有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經歷。在鄭州,梁鴻描寫了富士康工人的內部生活、情感狀態、心理狀態等。富士康員工因為頻頻跳樓,一度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世人對其工廠內部生活、工人狀況充滿了疑慮,梁鴻深入描寫了富士康工廠內外,描寫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情況,讓人知道了富士康工人為何竟至于選擇自殺。在深圳,梁鴻描寫了小鞋廠老板的創業歷程,起起伏伏,也描寫了鞋廠一日,展現了工人的工作情況、心理狀態與日常生活等。在青島,梁鴻寫了在韓國企業就職者的情況,光亮叔和嬸子帶著兒子在此打工,工廠缺少安全保障,空氣混濁,小柱就是因為在此地打工,中毒而死。梁鴻在很多時候讓打工者直接出場說話,把話筒交給他們,讓他們自己講述故事、經歷、遭遇、現狀、對所在城市、工廠的態度,對梁莊的態度等,不通過轉述,如此更能見出打工者的情況與心境。
《出梁莊記》中尚附有大量照片,形成一個潛文本。攝影亦敘事,可以呈現現實,梁鴻將在城市打工的梁莊人的“面相”呈現出來,他們大都風塵仆仆,臉上寫滿皺紋與滄桑,穿著土里土氣,與城市格格不入,一看即知操勞過度,怨氣內積,處境不佳。
二、山水田園的農村
農村遠離城市,生活相對簡單,所以成為很多文人雅士的精神寄托之地,他們將農村比作“桃花源”,那里神秘、富足、純凈,農民不是“閏土”,而是高人、隱士。今日,依然有很多作家在歌詠著農村和農民。
韓少功是思想家型作家,其格局較大,除了寫作之外,還翻譯作品,亦主編過《天涯》雜志,諸多論題曾引發知識界大討論。中國當代作家往往鄙薄學問,以為有生活則足矣,此為他們難以提升的根本原因,而韓少功是例外,他大致做到了“與時俱進”,理解不同時期的主要問題。
韓少功《山南水北》所呈現出來的鄉村世界跟“三農”問題視角之下的鄉村世界迥異,韓少功像一個隱者,像陶淵明,他筆下的鄉村世界田園山水一般,鄉村中隱藏著民間高人,鄉村生活恬淡而自由。韓少功是知青,他曾“上山下鄉”,之后通過升學離開農村,由于寫作成為著名作家。可是,韓少功逐漸厭倦了城市生活,他反而離開城市,回到鄉下,過起了隱居的田園生活。他說:“融入山水的生活,經常流汗勞動的生活,難道不是一種最自由和最清潔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難道不是一種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⑤
青年時期的韓少功離開農村,中年時的韓少功則回到了農村。韓少功人生軌跡與古代諸多讀書人近似,與當代諸多讀書人相反。中國古代是耕讀傳統,讀書人少年耕讀,一旦讀書有成,中舉或中進士,則外出做官,老年退休還鄉;今人則不再如此,學生拼命讀書,一旦通過高考,進入大學,死乞白賴也要留在城市,買房娶妻生子,終老于此,扎根城市。所以,路遙的《人生》才會感動了幾代中國人。告老還鄉對農村尚有反哺,終老城市則對鄉村唯有索取,沒有回報。韓少功反今人之道而行之,此舉在今天有著重要的示范意義。
如果韓少功留在了農村,未能出山,真成了一個農民,不知道今日做何感想?若如是,他眼中的農村會不會如同“三農”視野筆下的農村一樣?然而,韓少功畢竟離開了農村,進城,然后再回農村,心態已然不同:他非但衣食無虞,而且是社會名流。韓少功所見到的農村、農民和農業,其中充滿著奇人異事,充滿著神圣感,草木魚蟲,靡不有情。
書名“山南水北”有兩層意思。一、其中有隱逸之思,山、水有隱者之象,韓少功或因厭倦城市生活,或因厭倦城市中人事糾紛、矛盾重重,故生出隱逸之意。韓少功自道:“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樓所擠壓,不愿被城市的噪聲所燒灼,不愿被城市的電梯和沙發一次次拘押。……于是撲通一聲撲進畫框里來了。”⑥二、其中有探究之意。山乃高者,是上;水乃低者,是下。山水并用,是上下求索,也是“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亦是“鷹擊長空,魚翔淺底”之意。故“山南水北”是探索、研究、理解當下農村之作。
《山南水北》寫法亦如《馬橋詞典》,一個一個人物寫來,一個一個事件展開,仿佛是一部“農村詞典”。譬如,寫鄉間的青蛙,它們富有有靈性,可以辨別捕蛙者;寫如何治蟲;寫村口的瘋樹,仿佛樹有靈,可以使人發瘋;寫月夜美景,萬物俱寂;寫家里的葡萄樹“嬌生慣養”,瓜果使小性子;寫普通草藥治好了怪病;寫雞鴨貓狗;寫年節風俗;寫鄉村行政,鄉長、村長;寫奇人異事,塌鼻子可以治病行醫,可行方術;亦有各色人等,“衛星佬”“意見領袖”“笑花子”“垃圾戶”等。
韓少功的這種風格被湖南青年作家馬笑泉繼承下來,他的《巫地傳說》就是寫了俗世中的奇人。馬笑泉畢業于湖南銀行學校,之后工作于銀行,其《銀行檔案》頗有影響,之后創作《巫地傳說》,寫鄉土中的神奇力量和奇人異事。
在《巫地傳說》中,馬笑泉執拗地說,鄉土社會其實還有著巨大的力量,這片土地是“巫地”,這里有著大量“傳說”,可以證明昔日這片土地的神奇與力量。這種聲音在鄉土社會日益陷落之際,顯得彌足珍貴。小說有兩個關鍵詞:“巫地”與“傳說”,“我”就是這片“巫地”“傳說”的記錄者,“我”要以小說的形式將巫地的傳說保存下來,呈給世人。
《巫地傳說》共分六部,每部寫兩三位奇人,小說以“我”貫穿始終。第一部“異人”,既自述童年,也寫了黑頭與陳瑞生,他們二人以力量和武術著稱,第一部的故事頗似他的小說《憤怒青年》,也是寫“黑社會”。第二部“成仙”,以少年之“我”寫了秀姨與霍鐵生的悲慘遭遇。“成仙”既是對秀姨和霍鐵生的美好祝愿,也是對“文革”的控訴。第三部“放蠱”,寫“我”的大學時代,通過“我”的轉述寫了兩件放蠱之事,并且能夠筆力一轉,寫出“我”和同學的故事,最后稱“世界上還有一類無聲無色的蠱,比有聲有色的蠱蟲更可怕,那就是人心的疑懼和各種扭曲的欲望。”第四部“魯班”,寫工作之后的“我”,小說通過裝修房子之事,寫了二伯。二伯會魯班術,憑借巫術他戰勝了對手,養活了家人,贏得城里人的尊重。這一部融入了一些民間傳說,故事非常好看。第五部“梅山”,寫了銅發爹(放鴨子者)、銅順爹(捕魚者)、銅耀爹(獵人),三人皆會“梅山術”。這部分也非常精彩,或也取自傳說故事。民間傳說已經經過時間淘洗,故能廣在民間流傳,譬如銅順爹大戰魚王等都寫得驚心動魄,精彩紛呈。其實,越是作者的東西少些,作者的“我相”弱一些,作品就會越好些。第六部“師公”,寫當下的情況,法術在現代的沖擊之下已然失效。
《巫地傳說》也頗重視小說的形式,全篇結構松散,還是一如中國傳統小說。“我”是故事中的主角,“我”的各個時期貫穿著不同的奇人,而且小說并未按照自然時間的順序寫出,而是天馬行空,忽東忽西,忽南忽北。
凸凹是北京的作家,卻執著地寫鄉土北京。即使他寫官場小說,其實也是官場小說為表,農村變化為里,以官場小說寫農村情況,譬如他的《大貓》。1990年代以來,小說家喜歡描寫北京的現代性一面。譬如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1994年),將北京與紐約并置;邱華棟的《搖滾北京》《城市戰車》等描寫了北京的“新人類”;電影《北京遇上西雅圖》(2013年)則描寫了中國人有錢了,可以去美國生孩子、消費、戀愛。凸凹自我定位清晰,他說安心做“一個民間的寫家”。此前,“鄉土北京”的提法較多,但因為北京的都市化,此調不彈久矣,故凸凹的努力顯得較為獨特。
《玉碎》寫一個大問題:農村人進城。這個主題一直貫穿于1949年之后的文學。柳青《創業史》中梁生寶堅持留在農村,但改霞卻進城了。柳青對梁生寶持贊賞態度,對改霞則有批評的態度。路遙《人生》主題完全變了,高加林可謂“梁生寶走了改霞的路”,他千方百計要進城,而路遙對高加林的態度則比較曖昧。《玉碎》也寫農村進城者,但凸凹有自己的立場和判斷。小說的名字已經見出整部小說的內涵:玉碎了。
小說在結構上交叉進行,一章寫農村的南曉燕及農村,一章接著寫城市中的南曉燕及城市。如此能夠形成鮮明對比,農村的南曉燕是玉,她勤勞、厚道,各種美德集于一身;城市中的南曉燕卻一步一步走向了墮落,安心成為羅建東的小三,玉碎了。小說結尾處寫道南曉燕“雖然身處城市,卻有些認不清前邊的道路了”,就是卒章見志。《玉碎》與《駱駝祥子》主題頗為類似,祥子進城前是好青年,在城市中卻逐漸走向了墮落。
凸凹有著較強的文人情結,他本人即追求此種風格與情趣,故他筆下的農村被詩意化了,他筆下的農村人物被文人化了,農村好比他的桃花源。農村風景極美,農村民風淳樸,農民溫柔敦厚,是產“玉”蘊“玉”之地。在農村的南曉燕是玉人,質樸純潔、有情有義;南曉燕的爺爺更是被賦予諸種美德,他雖是羊倌,但卻極喜歡民歌,好似民間藝術家。
凸凹筆下的農村更多是個人趣味和情感的投射,他筆下的農民進城亦是其趣味的投射,但與真實的農村狀況或有距離。
三、貧窮但積極的鄉村
第三類寫農村的人、事、風俗、愛情、悲歡,他們筆下的農村雖然凋敝卻又雄奇,貧窮卻又積極,其中依然有著渾厚的能量。這一類作家,譬如有山西的曹乃謙、寧夏的李進祥、西藏的尼瑪潘多等。
曹乃謙,1949年出生,屬于紅衛兵知青一代,經歷頗為坎坷。曹乃謙本名不見經傳,他是山西的警察,不在文學圈內,但由于兩個人的推動,他在文學上的價值被廣泛認可,一是汪曾祺,二是馬悅然。
汪曾祺曾寫一文談《到黑夜想你沒辦法》,開篇即說:“一口氣看完了,脫口說:‘好。”接著說:“作品的形式就是生活的形式。天生渾成,并非反樸。”又夸贊曹乃謙的語言道:“語言很好。好處在用老百姓的話說老百姓的事。”⑦馬悅然是高本漢的學生,是漢學家,懂漢語,了解一些中國文化。因為他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常在中國行走,被作家們前呼后擁。馬悅然翻譯了曹乃謙的《到黑夜我想你沒辦法》,并寫長文推介,一時有人稱曹乃謙將獲諾貝爾文學獎,引發無數人對曹其人及小說好奇。
曹乃謙自述寫這本書的用意:“我在北溫窯呆了一年。這一年給我的感受實在是太深刻了,給我的震動實在是太強烈了。這深刻的感受這強烈的震動,首先是來自他們那使人鏤骨銘心撕肝裂肺的要飯調。十二年后,我突然想起該寫寫他們,寫寫那里,寫寫我的《溫家窯風景》,并決定用二明唱過的“到黑夜想你沒辦法”這句呼奴,作為情感基調,來統攝我的這組系列小說。在這二十九題系列小說中,我大量引用了‘山曲兒、‘麻煩調、‘苦零丁、‘傷心調、‘要飯調、‘挖莜面,只有這些民歌才能表達出人們對食欲性欲得不到應有的滿足時的渴望和尋求。也惟有這些民歌才能表達出我對他們的思情和苦戀,才能表達出我對那片黃土地的熱戀和傾心。”⑧
《到黑夜想你沒辦法》寫山西農村,時間則是“文革”期間。曹乃謙作此書時“文革”已時過境遷,故寫“文革”已完全脫離“傷痕”文學腔調。他另有抱負,這部小說可以歸結為一句話“飲食男女”。此人之大欲也,無論時代如何變遷,飲食、男女不變,故曹乃謙雖寫“文革”時期的山西農村,但他似乎要寫人永恒的方面。
小說以飲食展現山西的貧窮,但主體部分則是以男女展現情義和倫理。窮則窮矣,但是很多人窮得有志氣;雖然性壓抑,但是羞愧之心、倫理、禮儀等依然起著作用。譬如小說寫道:“狗日的他給提出說,說想做那個啥。黑女說:‘嗨哎呀灰鬼。不能了。人一老了就不能了。灰鬼子。她又說:‘要不,你想看就看看。下等兵說:‘不看,看還不如不看。下等兵說完就走了。自那以后,下等兵再沒來過黑女家。”⑨
《到黑夜想你沒辦法》語言非常有特點,大量使用方言。方言因為經過幾千年的沉積,其中能量不可小覷。譬如,2013年金宇澄《繁花》出版,廣受好評,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使用上海方言⑩。另外,《到黑夜想你沒辦法》結構亦有特點,各個章節之間似無關而實有關,共同寫出了“到黑夜想你沒辦法”這個主題。
汪曾祺在評價《到黑夜想你沒辦法》時說,“寫兩年吧,以后得換換別樣的題材,別樣的寫法。”這確實指出曹乃謙的問題,他的格局應該大一些,應該有所轉變,否則就完全定格了。
李進祥是寧夏的作家,他自述道:“我出生在這群人中,出生在清水河畔,在清水河的堿水里泡大了。我的良知的眼睛睜開了,我便有了一種責任;我思索的眼睛也張開了,心生出一種悲憫,為自己、為清水河畔的人,也為多災多難的回民族。我知道自己無法站得更高,采取一種審視的姿態,解剖歷史,可我也無法抑制自己的思索,只能拿起一只禿筆,把能領略到的蒼涼而又雄奇的自然,貧窮而又積極的人生,壓抑而又張揚的個性,敘寫出來。為的是讓更多的人了解這塊地方,了解這群人,了解這個民族。”11這是李進祥見志之言,就小說主題而言,李進祥有兩類小說寫了農村的情況。第一類寫清水河畔的民風、民俗,譬如《挦臉》(《芒種》2012年12期)、《方匠》(《民族文學》2009年第1期)、《剃頭匠》(《回族文學》2009年第1期)、《跤王》(《文學界》2009年第4期)等,這些小說能夠見出清水河畔的風俗、傳統、歷史與現實。第二類寫清水河畔回民受到現代性的沖擊,情況新生,人心已變,譬如《換水》(《回族文學》2006年第3期)、《你想吃豆豆嗎?》(《回族文學》2005年第6期)、《害口》(《回族文學》2007年第3期)、《女人的河》(《回族文學》2004年第3期)、《狗村長》(《回族文學》2007年第7期)、《遍地毒蝎》(《回族文學》2006年第2期)、《宰牛》(《關注》2009年第1期)、《一路風雪》(《朔方》2004年第5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