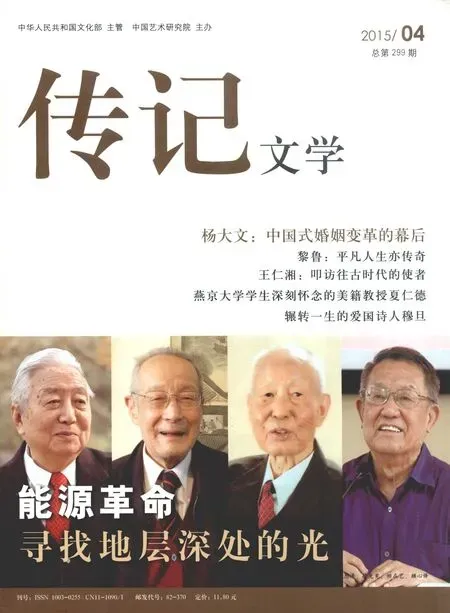閔恩澤:智慧催生艷麗的“科技之花”
文 瀛 瀛
閔恩澤:智慧催生艷麗的“科技之花”
文 瀛 瀛

閔恩澤,著名石油化工催化劑專家,中國煉油催化應用科學的奠基者,石油化工技術自主創新的先行者,綠色化學的開拓者,被譽為“中國催化劑之父”。1924年2月出生于四川成都,1946年畢業于重慶中央大學化學工程系。曾任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主任工程師、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副院長、首席總工程師、學術委員會主任等職;現為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高級顧問,系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國家最高科技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中國石化科技獎、中國催化成就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技術獎、國家技術發明獎一等獎、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日本橋口隆吉基金獎……眾多的榮譽背后是同一個泰斗級的大寫名字。
中國煉油催化應用科學的奠基人、石油化工技術自主創新的先行者和綠色化學的開拓者,這是業內同行對他的一致評價。
2008年1月8日上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站在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領獎臺上,滿頭銀絲的耄耋院士閔恩澤面帶微笑,平靜而泰然:“把自己的一生與國家的建設、人民的需要結合,是我最大的幸福。”
從試驗到失敗,從失敗再到試驗,從一片空白突破催化劑的國際封鎖
1955年10月,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學工程系獲得博士學位并已工作4年的閔恩澤沖破道道封鎖回到了闊別8年的祖國。回國之初,很多單位都不敢接受從美國回來的人,接連吃了幾次閉門羹。閔恩澤說,他很感謝當時石油工業部的部長助理徐今強接受了他,并分配他去當時正在籌建的北京石油煉制研究所。從此,他的人生和祖國煉油催化事業的發展緊密相連。當時,我國煉油所用的催化劑,依靠從蘇聯進口,對于這一領域的研究還是空白。
“那時候各方面條件都很艱苦,實驗室是向當時的北京石油學院借的幾間平房。”閔恩澤回憶說。實驗設備也只有從大連石油研究所搬來的幾件舊設備,試驗裝置要靠自己制備。更棘手的問題是,國內沒有現成可循的技術資料。但是,閔恩澤卻認為,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落后而不爭氣的頹廢習氣。他滿懷信心地組織大家制訂建組規劃,設計實施方案。他親自出去購買材料,添置設備,選拔人才。僅僅幾個月,就建立起一個初具規模的中型試驗裝置。當時,他們只有幾個人,就邊學邊干起來了。沒有技術資料,他組織大家收集國外有關學術論文、專利文獻、產品說明、廣告圖片,從多方面掌握國外技術發展情況,然后結合我國實際,制訂自己的研究計劃,摸索試制國內需要的催化劑。他們為查閱資料,摘錄筆記,不知度過多少個不眠之夜!經過幾年艱苦的努力,閔恩澤和他的助手們在大連石油研究所等兄弟單位的配合下,幾種主要石油煉制催化劑陸續研制成功,投入工業生產。其中磷酸疊合催化劑獲得國家科技成果發明獎。
1959年,蘇聯援建的蘭州煉油廠投產,其中有一套移動床催化裂化裝置是核心,它把重油二次轉化為航空汽油。所用的移動床小球裂化催化劑一直從蘇聯進口。60年代初,中蘇關系緊張后,蘇聯開始以次品供應。
“1960年開始,蘇聯逐步減少以至最后停止了對我國的催化劑供應,當時庫存的催化劑只能維持一年,直接威脅到我國航空汽油的生產,形勢十分嚴峻……”石油工業部的老部長余秋里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把研制催化劑的重擔,交給了從美國回來不久的石油科學研究院閔恩澤同志……”
當時,石油部高瞻遠矚,決定建設一個小球硅鋁裂化催化劑生產廠,并組織會戰,閔恩澤被任命為技術負責人。他臨危受命,全身心投入其中,立即組織專題組開展催化劑的研究和開發;參加工廠設計,確定工藝、設備選型;最后擔任工廠開工副總指揮。閔恩澤整天穿著工服,到車間檢查生產工藝條件,制訂各種試產方案。同時,又和科研組的同志一起研究解決膠球破碎的關鍵問題。這些日子,他吃在現場,住在辦公室,每天8點開始工作,一直忙到夜里1點多,接著開碰頭會,一開就是一兩個小時,所以通常都是凌晨兩三點才休息。閔恩澤決心不辜負黨和政府對自己的信任和期望,用艱苦的勞動去開墾這片廣闊的“處女地”。
早在1948年,閔恩澤在美國第一次看到催化裂化裝置,看到那黑褐色的原油神奇地變成清亮透明的汽油,當時他除了驚奇,只有感慨:中國何時能建成這樣的裝置?
讓他未料到的是,10多年后他卻在研究這套裝置的小球硅鋁裂化催化劑。在試驗過程中經常與危險擦肩而過,第一次試運轉就發生了掉帶事故,閔恩澤親自鉆進高溫烘烤的干燥室,后來他指導設計了自動調帶裝置,才將問題解決。由于技術、經驗等方面的不足,他和同事們在幾間非常簡陋的小平房里冒著危險,反復試驗,失敗、再試驗、再失敗……期間,閔恩澤常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激勵自己也鼓勵大家,“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失敗和挫折教育著我們,使我們變得聰明起來”,邊學習、邊實踐、邊總結,從試驗到失敗,從失敗再到試驗,在探索中摸索前進。
一次,一條60米長的干燥帶運轉起來,由于升溫引起膨脹,發生了掉帶事故,閔恩澤和工人打著手電筒,冒著彌漫的熱蒸汽,鉆進干燥箱內,苦戰3天3夜把干燥帶修好。他累得眼里布滿了血絲,面容憔悴,工人勸他休息,他總是說:“沒事,我身體頂得住。”可事實呢?由于過度的勞累,他的體質在急劇下降,經常感到渾身不適,肺部已經長出一個可怕的怪物——腺癌,在威脅著他的生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堅持不下火線。
經過3個多月的艱苦奮戰,克服了一個個難關之后,終于實現了試生產的成功,生產出了我們自己的高質量的小球硅鋁催化劑。此時,離催化劑庫存告罄僅有兩個月時間。催化劑供應及時得到了保證,中央領導人和石油部領導的心里,就像一塊石頭落了地!
問題解決了,試生產成功了,閔恩澤卻病倒了。回北京之后,在一次針對過敏性鼻炎的體檢中,醫生驚訝地發現,閔恩澤已經患上了肺癌,需要動大手術!就在閔恩澤還不到40歲的時候,無情的病魔奪去了他的兩頁肺和一根肋骨!
大家去醫院看望,他卻說:“我的病沒事,關鍵是小球硅鋁裂化催化劑生產出來了。”大病初愈,爬幾層樓梯都會氣喘吁吁,閔恩澤探索的腳步卻并未停止。在之后的幾年里,他又接連攻克了重重難關,研制出了我國煉油工業急需的磷酸疊合催化劑和鉑重整催化劑等。就在這些成就的帶動下,一批催化劑工廠、煉油廠拔地而起,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國煉油催化劑發展的基礎。
人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正當他帶領助手們努力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時候,1966年那場政治浩劫席卷全國,閔恩澤也被卷了進來,甚至牽連到了他的家人。和那個年代所有被誤解的人們一樣,他先是被當作“特嫌”和“一小撮階級敵人”關進“牛棚”。
在牛棚里,除勞動改造外,他還要寫交待材料。他利用這段時間來思考、總結和學習。如今回憶起那段日子,閔恩澤依然十分感慨地說,他把以前催化劑研究過程中的得失成敗都記錄下來;通過讀《毛澤東選集》、學習《實踐論》和《矛盾論》,來加以總結分析,這為他后來的催化劑研究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為他走上科學巔峰準備了哲學思考方法。
1969年,他從“牛棚”出來后,雖然沒有給他分配工作,但他仍然時刻關心著催化劑研究的進展情況,主動幫助課題組的同志擬定科研方案,替有關同志查閱和摘錄文獻資料;誰有什么問題不明白,他總是熱情地給予解答,直到弄明白為止。
1970年,石油部派他去撫順石油三廠參加加氫新技術攻關。當時,他愛人去干校了,身邊帶著9歲的獨生女兒,他連夜把孩子送到親戚家,托他們送到愛人那里去,自己第二天就出發了。在撫順,不管政治風云如何變幻,各種派別怎樣對戰,他總是專心致志地在工廠現場做試驗工作。
1975年,石油部又派他去長嶺煉油廠協助整頓生產秩序。他一到那里,就深入車間調查研究,親自動手打掃車間,整理廠容,并和工人一起,改革工藝,消除粉塵,改善勞動條件,工人安心工作了,生產秩序很快走上正軌。后來,他又在廠黨委的支持下,組織科研單位、高等院校部分有關同志一起,經過兩年多的努力,研究成功一種新型加氫精制催化劑,使長嶺煉油廠生產的柴油行銷香港,獲得國家產品質量金質獎。
直到打倒“四人幫”之后,閔恩澤才回到北京。1978年,科學的春天到來了。這一年,閔恩澤獲得了“在我國科學技術工作中作出重大貢獻的先進工作者”稱號,他熱血沸騰,激情澎湃地引用他十分喜愛的詩句來表達心聲:“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1980年起,閔恩澤開始擔任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他參加中國催化化學代表團出國考察,看到我國煉油催化劑產品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又拉大了,心里非常難過。回來后,在一次討論科研任務的黨委擴大會上,他為此著急得哭了。他表示決心加倍努力工作,要在短時間內,使我國煉油催化劑產品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他提出對今后煉油催化劑科研任務要按“一趕二超三創新”來部署,不僅要學習一些外國先進技術,更重要的是根據我國的需要、資源的特點,去發展自己的新型催化劑。在科學的春天里,閔恩澤又帶領科研人員邁開了堅實的步伐。
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這10多年中,由閔恩澤帶領研制的半合成分子篩裂化催化劑,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由閔恩澤指導研制成功的一氧化碳助燃劑,既提高了催化裂化再生效率,又降低了能耗,直接經濟效益達每年1億多元,并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在“大慶常壓渣油催化裂化”國家計委攻關項目中,閔恩澤成功地指導開發了我國第一代CRC渣油裂化催化劑,獲1987年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另外,閔恩澤指導研究的加氫精制催化劑的制備規律、開發成功高脫氮活性的RN-1催化劑,1989年獲中國專利局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聯合頒發的專利金獎,1991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多年的努力拼搏和刻苦鉆研,終于結下了累累碩果。閔恩澤高興地看到,我國煉油催化劑品種不斷豐富和齊全,并形成系列,不但大大滿足了國內煉油生產的需要,而且屢次在國際舞臺上嶄露頭角,我國也逐漸成為世界少有的裂化催化劑供應商之一。
石化催化領域的每一重大進展都無法繞過他的名字,自主創新是他畢生科研的關鍵詞
1925年,美國科學家Murray Raney發明的金屬骨架鎳合金催化劑被命名為雷尼鎳(Raney鎳合金),廣泛用于醫藥、農藥、化纖、石油化工等多種行業有機合成的加氫反應中,世界年消耗量巨大,我國年消耗量達1萬噸。經過不斷改進,這種催化劑的活性已趨穩定,制備方法已趨成熟,作為粉狀催化劑一直在釜式攪拌反應器中使用。閔恩澤等開發的“非晶態合金催化劑和磁穩定床反應工藝”,恰恰通過自主創新,改進了這一“經典”試劑的使用效率和使用方式。
那是1980年的一天,閔恩澤邀請美國專家來北京講學。他了解到國外大公司在分子篩領域成功的經驗是:搞新的催化材料,而不是搞催化劑。這就好像做衣服要先找到新的布料一樣。閔恩澤大受啟發:從找新催化材料入手實現自主創新。
如何去選擇具有發展前景的新催化材料?閔恩澤不斷從鉆研文章、專利、書籍中得到靈感,從實驗中得到啟示,受其他領域概念的開導,從學術討論中打開思路……
1985年,當讀到一篇有關非晶態合金催化材料性質的研究報告時,他眼前一亮,眼光敏銳地意識到把晶態合金催化劑轉移到非晶態合金上,將開辟一個新催化材料領域!他聯想到:“一個新催化材料,還要配以新型反應器來充分發揮其優越性。新催化材料、新型反應器和新反應是創新的‘新式武器’,它們的原始創新往往帶來集成創新。因此,必須在新催化材料、新反應工程和新反應的科技前沿開展導向性基礎研究和開拓性探索,尋找和積累‘新式武器’。”
如何尋找新型反應器?此前,閔恩澤曾讀過埃克森公司關于磁穩定流化床的報告,他當時就認識到這是一種新型反應器。后來又讀到埃克森基礎研究實驗室主任在美國西北大學所作的一份報告,把金屬原子簇、液膜分離、磁穩定床作為長遠研究的領域,他進一步認識到磁穩定床的重要意義。于是他決定用全新的非晶態合金材料代替晶態Raney鎳合金,用磁穩定床反應器代替釜式反應器。
說干就干,這一干,就是20年。經過無數次挫折、失敗,無數次試驗、分析,前后3代科學工作者、10余名博士和博士后、數千名技術人員和有關高等院校學生、研究機構人員堅持不懈,攻堅克難。20年后,他主持開發完成的這項“非晶態合金催化劑和磁穩定床反應工藝的創新與集成”榮獲2005年度唯一一項國家技術發明獎一等獎。此前,該獎曾連續6年空缺。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化學部1986年科學基金評審會議與會人員合影(前排:左四為閔恩澤、左十一為吳征鎧、左十三為徐光憲、左十四為林克)
作為這項技術發明的總設計師,閔恩澤指出,實現原始性創新的途徑之一是把現有技術的科學知識基礎轉移到全新的科學知識基礎上。對“非晶態合金催化劑和磁穩定床反應工藝”來說,這項成果把原有的晶態Raney鎳合金和釜式反應器的科學知識基礎,轉移到全新的非晶態和磁穩定床反應器的科學知識基礎上,終于實現原始創新;同時為實現這一科學知識基礎轉移的工業化,實現新催化材料與新反應工程的集成,自然又會形成一些集成創新。這項創新帶給閔恩澤很多啟示:“最重要的是,我對自己增強了信心。經過我們這些年的努力。它證明,中國科技人員有能力自主創新。”
談及原始性創新,閔恩澤說,從蒸汽機車到電氣機車,從用膠卷的傳統相機到數碼相機,都是原始性創新。要實現原始性創新,必須改變原有技術的科學知識基礎,不能走老路,要走新路。怎樣才能實現原始性創新?可以借鑒一位老畫家對于繪畫的看法。他說,要臨摹古今中外的名畫,要到名山大川寫生,臨得多了,寫生多了,創作的靈感就會產生。對于科技創新,我們就要廣泛學習古今中外的有關技術、專利,要深入企業生產一線,學得多了,見得多了,科技創新的靈感就會產生。問及創新的感受,他毫不猶豫地說:“思考催化劑的問題是快樂的;當想出一個好的解決方法時,也是快樂的;當課題最終取得成功時,那更是快樂的。”
1991年,閔恩澤從《催化科學與技術》上首次看到一篇文章引用福斯特的“技術進步S型曲線規律”,即技術進步通常經歷一個“慢—快—慢”的發展周期;而當某一技術達到或接近其發展極限時,技術進步將通過“非連續式”——即轉移到一個全新的和完全不同的知識基礎上來實現。閔恩澤發現,1930年至1980年間化學工業的重大新技術開發就遵循了這種S型曲線規律;并且,當“非連續式”技術進步發生時,70%的情況下技術領先地位易主,現有技術的擁有者不再是領先者;“非連續式”技術的發明創造人,要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認識現有技術的極限,設想出繞過它們另行開拓的可能途徑,并把這一構想變成現實。“噴氣燃料加氫脫硫醇(RHSS)技術的開發和工業應用”,正是這一理念的成功范例。
噴氣燃料是民航和軍用飛機燃料,其中的硫醇不僅使油品發出臭味,而且對飛機材質有腐蝕作用并影響燃料的熱安定性。以往國外普遍采用液體堿作為催化劑,通過催化氧化反應加以脫除,但同時產生廢堿排放,污染環境。20世紀80年代后期,國外嘗試開發固體堿催化劑,以求緩解污染。
閔恩澤率領他的博士生團隊,一開始沿用固體堿催化氧化的思路,卻屢屢走進死胡同。1996年年底的一天,閔恩澤下班回家路上跟人聊天時,靈感突現:噴氣燃料中的硫醇最易于加氫脫除,可否利用這一原理另辟捷徑,在比常規加氫工藝更緩和的條件下加氫脫硫醇?思路大開,流程一下子打通,短時間內開發成功RHSS新工藝,廢渣排放降低99.8%,并顯著降低操作費用,能從多種原料油生產合格的噴氣燃料。目前已建成7套每年15—100萬噸規模的工業裝置,總加工能力每年420萬噸。RHSS技術占國內新建或改建裝置80%的份額。
從石油催化劑的研發,到催化材料的發明、綠色化學的應用,再到現在的生物質能源開發,即“生物柴油”的研發,閔恩澤的研究成果不斷地創新。而談到這些創新,閔恩澤認為堅持是最重要的因素。他笑呵呵地說:“就像 《西游記》一樣,取經要經過九九八十一難,唐僧就很執著,再多困難也沒有動搖他取經的決心,最后終于到了西天,取得真經。”
他說,科技人員要實現自主創新,就要有奉獻精神,要勤奮,要實事求是。“科技發展到了今天,進入工業化時代,技術自主創新常常需要形成團隊才能完成。要形成一個很好的團隊,一要誠信,二要寬容。反對的意見不可避免,不要計較。”說到這里,他又提到了電視連續劇《西游記》的主題歌:“‘你挑著擔,我牽著馬……’,這就是各盡所能、團結協作嘛!孫悟空本事再大,也有許多困難解決不了,需要找來土地神來了解當地情況,還要向如來佛、觀世音求救。我自己也是這樣,碰到自己不懂的東西,給同事、朋友打個電話請教;遇到困難,還要向中國石化總部求救。”
“做事情還要講規矩,要守法誠信。唐僧的緊箍咒就是約束孫悟空的規矩。做學問尤其如此,不講規矩,不成方圓;不講誠信,難以成大器。譬如學術上的弄虛作假、剽竊之風等,萬萬不可取。”閔恩澤幽默地說:“我自己有時當唐僧,要帶團隊;有時當孫悟空,要搞技術攻關;有時又當沙和尚,提供后援。”在他看來,一個人做的事,能夠和國家強盛、民族命運聯系在一起,這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
亦師亦友的泰斗開啟中國的綠色化工時代,為石化研究儲備人才庫
20世紀90年代初,發展綠色化學、減少環境污染越來越成為普遍的心聲。這時的閔恩澤雖然已經年近七旬,但依然走在科技發展最前沿,站在歷史的高度,他深感對子孫后代的責任重大,開始致力于把催化科技應用于綠色化學中去,把自己的催化劑研究從石油煉制領域擴展到石油化工的有機化工原料以及化纖單體領域。
1995年,閔恩澤擔任中國科學院化學部《綠色化學與技術——推動化工生產可持續發展的途徑》咨詢課題組長,組織調研活動,主編出版調研文集《綠色化工技術》,并提出發展我國綠色化學的建議。
同年,他又擔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與中國石化集團公司聯合資助的“九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環境友好石油化工催化化學和反應工程》的項目主持人。閔恩澤高瞻遠矚的學術把握、精心的指導和兢兢業業的敬業精神使這一重大項目取得了圓滿的成功。
為解決國內對己內酰胺這一重要化纖原料的迫切需求,中國石化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相繼耗資25億元、35億元,引進以苯和甲苯為原料生產己內酰胺的裝置各1套,在巴陵分公司和石家莊化纖公司生產。到了2000年,由于多種原因,兩套裝置年虧損近4億元,急需扭虧為盈。
閔恩澤參加中國石化技術服務小分隊,去巴陵分公司技術咨詢后,又主持石家莊化纖公司己內酰胺現場診斷,提出建議;以企業為創新基地,產學研相結合,動員全國優勢單位和人才,聯合攻關,僅用了7億元進行工藝改造,把兩套裝置的生產能力由原來的每年5萬噸分別提高到每年14萬噸、每年16萬噸,提高了產品質量,實現扭虧為盈,而且徹底消除了引進技術帶來的嚴重環境污染,從而開啟了中國的綠色化工時代。面對多方贊譽,閔恩澤真誠地說:“能把自己的一生與人民的需求結合起來,為國家的建設作貢獻,是我最大的幸福。”
閔恩澤的付出得到了廣泛的贊譽與社會的認可。1989年和1995年,閔恩澤兩次被評為“全國先進工作者”,1989年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授予“杰出校友獎”,1990年被評為“國家千名有卓越貢獻的專家”,1995年獲首屆“何梁何利基金科學技術獎”,1997年獲科協“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稱號,1998年獲日本橋口隆吉基金獎。
新世紀以來,閔恩澤依然精神飽滿,進入綠色化學中的生物物質資源利用新領域,利用油料作物發展生物柴油。這一產業的發展不但可以降低對進口石油的依賴,減少汽車尾氣對空氣的污染,還可以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保護環境,并可以支援“三農”問題。
作為戰略科學家,閔恩澤非常關注和熟悉國際科技前沿,并始終站在世界石油化工科技的前沿。20世紀90年代初,他就提出發展我國綠色化學的建議,并指導開發成功多項從源頭根治環境污染的綠色新工藝。21世紀以來,他進入綠色化學中的生物質資源利用新領域,指導學生開展利用油料作物發展生物柴油的生產工藝研究。目前,已開發成功高壓醇解生物柴油生產新工藝,建成每年2000噸的中試裝置。
巴蜀之子耄耋之年鄉情難了
閔恩澤是個地地道道的成都人。“我回國50多年來,好多事情都變了,就是四川口音沒變。”
閔恩澤出生在四川成都。美麗的岷江滋養了肥沃的川西平原,也孕育了燦爛的巴蜀文明,富庶的天府之國積累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閔恩澤還能依稀記起當年,閔府家中那副對聯:“忠孝傳家遠,詩書繼世長。”
紅照壁、銀絲街、北門趙王廟……成都熟悉的街名、變幻的街景,閔恩澤在晚年每年都會回四川一次,去成都找找看看這些街道,每一個地方都還在,只是變化很大。
當年的四川正是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等軍閥割據混戰的時期,軍閥之間燒殺搶掠,戰事不斷,人心惶恐。在那樣一個動蕩不安的年代,閔恩澤遵循家訓,走上了求學之路。
上小學時,閔恩澤就開始學習“國學”,每天要讀一篇《古文觀止》,臨摹王羲之、趙孟頫等人的書法。在童年的記憶里,孔孟之道、詩書畫印等傳統中國文化的精髓已經伴隨著桐油紙和松油墨的香味,一起滲入了閔恩澤的骨子里,根深蒂固。
早在初中時代,閔恩澤在私立南薰中學時,就表現出了全班佼佼者的過人成績,后來便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四川省立成都中學(前成都二中,現為北京師范大學成都實驗中學)。在這個學校讀了還不到一學期,侵華日軍的轟炸機就開始在成都上空嘶叫著盤旋了。閔恩澤至今仍然記得當時的情形,日軍的飛機第一次在成都上空投下罪惡的炸彈,閔恩澤隨著人流逃出成都,跑到荒郊野嶺的亂墳崗、田埂邊躲避炸彈。
后來學校搬遷到成都郊外的三岳廟。在那里,用竹子和稻草臨時搭建了幾間屋子,在墻上抹一點白灰,就當作是教室和宿舍。記憶較深的是,那時候一下雨,屋子就漏,雨水漏下來,就得拿盆子接著,于是滿屋子都是雨水劈劈啪啪打在盆子里的聲音,有時一整夜都無法入睡。那時候閔恩澤從學校回家,需要步行5個多小時,從中午12點一直走到下午5點多鐘!
盡管條件如此艱苦,閔恩澤仍然非常努力地學習,每天堅持點油燈夜讀。教書的老師也十分賣力。說起那時候的數學老師,閔恩澤贊不絕口。由于那個老師代數教得好,大家便叫他“饒代數”,還有“鄭生物”(四川喜歡用事物的特點來命名,比如鐘水餃、賴湯圓)。那段艱苦而充實的時光給閔恩澤留下了美好的回憶,最高興的要數去門前的河溝里抓鱔魚,粘滑的鱔魚平時躲在水下的洞穴里,到了夏天的晚上,它們會鉆出洞穴,到田泥表層乘涼,這時,只要用光照,它們便不會再動,乖乖束手就擒。當時,愛打排球的閔恩澤還是年級排球隊的二傳手。
雖然少小離家,對于成都和母校的記憶卻讓閔恩澤永生難忘。2004年元月,心系母校的閔恩澤個人出資10萬元,捐獻給北京師范大學成都實驗中學,用于建立“恩澤獎學金”,并表示將盡自己的努力吸納各方資金補充該項基金。至今,獲得過“恩澤獎學金”獎勵的優秀學生、優秀畢業生和優秀貧困生一共有120多人。閔恩澤表示,會盡自己的努力吸納各方資金補充該項基金。
恩愛的院士伉儷科學報國,用自己的智慧催生著艷麗的“科技之花”
傍晚時分,北京西北一隅的中國石化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內,經常可以看到兩位老人攜手散步,林蔭路上留下他們斜長的身影。這兩位看起來很平凡的老人就是兩院院士閔恩澤和他的夫人陸婉珍院士。在我國科學家陣容中,夫妻院士并不多見,而閔恩澤與陸婉珍就是一對獲得過我國工程科技界最高榮譽的恩愛伉儷。
1942年,中學會考成績優異,閔恩澤被直接保送進了當時的重慶國立中央大學,他最先選擇的是土木系。當時,身為銀行家、實業家的舅父對閔恩澤發生了很大影響。當時農業大省的四川急需生產化肥,舅父想在四川建一個化肥廠,卻苦于缺乏專業人才,閔恩澤改志要在家鄉搞實業,建化肥廠,于是在大學二年級時毅然轉學化工。就是這個決定,為他以后走上煉油催化科學之路埋下了伏筆。
大學畢業,閔恩澤回到成都一家自來水廠做分析化驗工,一個星期只需要做兩次化驗,生活簡單而苦悶。于是他又回到重慶,在一家肥皂廠實習。實習過程中得到消息,當時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要招收一批印染技術人員,需要經過培訓,還有可能出國。通過考試,閔恩澤考了第一名。于是在1946年10月,閔恩澤到了當時中國最大的印染廠即上海第一印染廠,學習印染專業,培訓結束后當了一名漂染車間的技術員。這個工作也很辛苦,每天要值班12小時,而且在這里只能整天埋頭苦干。
1946年暑期,國民黨政府組織了一個自費留學考試,通過考試者,可以提供官價的外匯,還可以得到一張船票和半年的生活費。閔恩澤通過了考試,向舅父借了一筆錢,再加上在中紡工作時積蓄的工資,于1948年3月去了美國,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學工程系攻讀研究生。
在美國,閔恩澤學習十分刻苦,僅用9個月就拿到了碩士學位。由于成績優秀還獲得全額獎學金(全校僅有11人拿到了這筆獎學金)。用這筆獎學金,閔恩澤繼續攻讀博士,并順利地戴上了博士桂冠。
1950年,閔恩澤與當時已經是博士后的妻子陸婉珍走上了紅地毯,跨進了婚姻的殿堂。閔恩澤與陸婉珍是中央大學學習時的同班同學。陸婉珍祖籍上海,生于天津,長在濟南,7歲回到母親的老家常州。陸婉珍讀書時代成績很好,小學到大學三年級一直當班長,中央大學讀大四時才“讓賢”給閔恩澤。陸婉珍喜歡數理化,數學一直全班第一,也喜歡體育,跳高、球類運動是長項。陸婉珍和閔恩澤的緣分從就讀中央大學化學系時就開始了,她的理想是當“中國的居里夫人”,個人問題并不重視,所幸緣分一直跟隨著他們。后來,兩人一前一后赴美國留學。
1951年7月讀完博士以后,閔恩澤和妻子都參加了工作,他由副化學工程師提升到了高級化學工程師。在當時,兩個博士的收入是相當可觀的。對于這時的閔恩澤來說,生活已經相當優越了。在他心里,“出去是為了學有所成,沒有想留在那里,就一個目的,學成了就回來”。這時,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了,國際局勢日漸緊張,美國政府限制理、工、農、醫等專業的人才離開美國國境,回國之路變得異常艱難。甚至有美國人諷刺說,回國,就等于拿腦袋往石頭上撞。盡管如此,閔恩澤和夫人一方面在工作中努力鉆研先進科學技術,收集各種技術資料,為參加新中國建設作準備;一方面為取得回國簽證進行不懈的斗爭,一直沒有停止歸國的腳步。終于,他托朋友在香港找了一份工作,到了查濟民先生在香港創辦的中國染廠當研究室主任,條件是9個月以后輾轉回大陸。1955年10月,閔恩澤終于攜妻子一起跨過羅湖橋,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接受采訪時,閔恩澤回憶起接受胡錦濤總書記頒獎時的情景充滿了幸福感。他欣喜地說,我很幸運,這是黨和國家給予科技人員的最高榮譽,反映了黨和國家對科技事業的高度重視,對科技人員的親切關懷。“我只是個上臺領獎的代表,這個獎項是全國幾代石化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很幸運,50多年來祖國石油工業的興旺發展,為我提供了發展專業、施展才華的大好機會。事實證明,我50多年前回國是正確的選擇。”
高血壓、膽結石、胰腺炎……折磨著年邁的閔恩澤。多年前,夫人陸婉珍曾患腎癌,一側腎被摘除。但他們倆對于疾病一向泰然處之。身邊人都知道,工作起來的閔恩澤不像是一個體弱多病的人,對催化劑研究的“鐘情”,似乎催化著他的無限活力,在他的工作日程安排上,從沒有8小時的時間限制。
1991年,閔恩澤患了膽結石,痛起來大汗淋淋。后來在南京急性發作,不得不住進南京軍區總醫院手術,取出的結石直徑有25毫米。醫生說,他的膽囊磨得比紙都薄了,再不手術是很危險的!在南京住院期間,他還讓他指導的博士生把有關的信函、論文送去,在病房里審閱。
這些年來,閔恩澤一直保持多年養成的習慣:查閱國外資料。石科院圖書館訂的煉油、催化、化工方面的國外原版雜志,寄來以后圖書管理員先送到他辦公室,他一本一本地瀏覽,一篇一篇地看,了解相關研究領域的最新動態與國際前沿。雖然身體也大不如以前,閔恩澤還在勤奮地學習、工作:睡到凌晨兩三點鐘醒后他要按時吃藥,如有所思或靈感突現,他就趕緊記下來。

閔恩澤與夫人陸婉珍過生日
由中石化集團和侯祥麟、師昌緒、張存浩、李靜海4名院士聯署的《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推薦報告》,在概括閔恩澤科技成就和貢獻時用了這樣的言語:“他被公認為我國煉油催化應用科學的奠基人,石油化工技術自主創新的先行者和綠色化學的開拓者。”這3項中的任意一項,可能都足以把他推上最高領獎臺。
然而,陸婉珍在他獲獎之后如此感言:“以前看王選、袁隆平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總有神秘之感;而閔恩澤對我來講很平常。我要說的是,有平常人的能力,加上系統訓練和勤奮,人人都能獲得成功。”陸婉珍這樣評價,他能取得一些成績,并不是他比別人聰明,只不過是他一輩子都在不停地鉆研這件事。女兒閔知琴這樣說:“他的腦子比較單純,一天到晚就在想他那個催化劑的事。他做事非常執著,名與利他都不會去管,就是為了做成而做成。”
據陸婉珍透露,閔恩澤參加國家最高科技獎領獎前夜曾反復練習講話稿:“他是一個很認真的人。在上大學時,我就發現他是個很負責任的人,從他的筆記就能看出來,寫得特別工整。”兩位院士唯一的女兒目前在美國工作,彼此照顧已經成為兩老的生活習慣。閔恩澤一直保持著很年輕的心態,雖然已是高齡,但他對電腦、手機等新生事物也很感興趣,甚至對一些玩具都非常喜歡,平時他仍會用計算機等輔助工具。
閔恩澤現在正籌劃兩件大事:一是把50多年的自主創新案例寫下來,以便于后來者學習培養創新型人才;二是探索利用生物質資源生產車用燃料和有機化工產品,迎戰油價飆升和大量進口石油的考驗。他的研究成果無疑將恩澤后世。
催化劑是一種它能夠加速反應速率而自身不改變的物質。它能夠誘導化學反應發生改變,而使化學反應變快或者在較低的溫度環境下進行化學反應。作為石油化工領域著名的催化劑專家,閔恩澤用自己的科學創新思維催化著石油化工的突飛猛進,用自己的智慧催生著艷麗的“科技之花”!
責任編輯/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