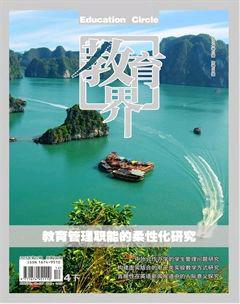《赫索格》:父權制與女性主義的碰撞
申曉旭
【摘 要】《赫索格》問世之后,索爾·貝婁被譽為“福克納、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文學繼承人”。本文從弗里丹女性主義出發,分析了作者隱藏在《赫索格》中的父權制意識形態與女性主義的相遇、美國基督教文化與猶太文化的沖突。
【關鍵詞】《赫索格》 女發性主義 父權制 美國文化 猶太文化
一、父權制下的厭女情節的體現
父權制,指被男性所控制的社會體制。在家庭生活中表現為父親承擔了整個家庭的福利,同時在家庭中具有話語霸權。父權制認為男性都擁有主宰和決定一切的權力。處于父權制下的婦女處于從屬地位,不僅被剝奪了選舉權、受教育權等,還被排除在各種社會權力機構之外,被迫處于受壓迫的地位,從而淪為附庸。
父權制文化下的傳統文學中,女性形象被歸類為兩個極端:一個是高貴的淑女、家庭中的天使,她們無法做自己,她們只是妻子、母親和女兒,她們溫柔、可愛、順從、貞潔;另一個則是與“天使”形象完全相反的“妖婦”形象,她們刁鉆古怪、野心勃勃、不懂順從、處處與男性作對,她們是紅顏禍水,把男人們引入了痛苦的深淵,她們自然地成為父權制文化下厭女情節所嘲諷和貶低的對象。然而歸根到底,這種“天使”和“妖婦”的二元對立是父權制文化下厭女情節的具體表現——即父權制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歧視和偏見。
小說的故事開始于赫索格第二次離婚。通過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講述了他的經歷和遭遇。他的第二任妻子瑪德琳的不忠和忘恩負義使他倍受打擊,使他的精神支柱倒塌。赫索格將種種不幸與痛苦的根源都歸咎于瑪德琳的背叛。赫索格將自己看作妻子與好朋友通奸的受害者。他一直強調自己將她從宗教中拯救出來,而其不但沒有對他感恩,反而狠心地將他攆出家門。索爾·貝婁把這個“壞女人”塑造成赫索格迷惘與困惑的罪魁禍首。
然而對于赫索格來說,這樣的“壞女人”又豈止一個。他的前妻黛西對于自己的想法十分堅持,是一個有著極強管理能力的女人,但這些僅僅可以給赫索格帶來生活上的規律,她的理智和規律使他的婚姻生活枯燥沉悶,這些只會限制他的創作靈感。他并不把這些優點看作她的美德。雷蒙娜漂亮、性感,在招待男朋友方面十分有經驗。雖然她對赫索格照顧得無微不至,在赫索格看來,她最終的目的卻是成為“赫索格太太”。
赫索格將感情、生活、學術上的不幸完全歸結于他身邊的“壞女人”,原因不過是他本身所受的父權制文化的影響。同時,貝婁在“妖婦”形象的塑造上完全通過赫索格這一男性的話語,剝奪了女性為自己辯護的話語權,這種女性話語權的喪失也正是貝婁男權文化的重要表現。
二、女性主義的解讀
1.弗里丹女性主義的解讀
貝蒂·弗里丹是20世紀60—70年代美國婦女解放運動的領袖。她與貝婁同為在美國長大的第二代猶太移民。在《女性的奧秘》中,她認為,主流社會宣揚的“幸福的家庭婦女”形象作為典型的美國婦女形象,成為女性們競相追求的樣板。數以百萬的婦女都活在“幸福的家庭婦女”的神話中,在各方面都過度依賴她們的丈夫,缺乏自身價值。弗里丹號召陷于人生彷徨的千萬女性要走出“女性的奧秘”的禁錮,戰勝父權制對于女性的啟示和偏見,去從事創造性的工作,使自己獲得重生。
貝婁在《赫索格》中刻畫了六位活在“幸福的家庭婦女”禁錮之下的傳統女性,園子、黛西、雷蒙娜、莎拉·赫索格、丹妮·龐特里特、菲比·格斯貝奇。她們沒有明確的目標,缺乏主動性和自信心,在兩性關系上把自身放在被動的位置上。
園子認為女人天生就應該以男人為中心,只能付出,不求回報,甚至在被赫索格拋棄之后仍然沒有任何怨念,還提醒他小心瑪德琳。黛西是一個獨立且有主見的女性,然而多年受猶太傳統文化的教育,在家庭生活中,她處處以丈夫為中心,即使遭到背叛仍舊無奈接受,隱忍度日。雷蒙娜,經濟獨立,漂亮性感,卻仍然認定只有成為赫索格太太才能實現其最終欲望。丹妮在離婚后依然履行著作為妻子的義務,給老頭子填報稅單,替他保管全部檔案材料,甚至給他洗襪子。菲比面對丈夫的背叛,保持多年的沉默,只為了保全作為一個妻子和母親的身份。赫索格的母親莎拉在加拿大做苦工掙錢補貼家用,幫助丈夫渡過難關,將丈夫和兒女作為自己生活的全部意義。貝婁通過赫索格之口講述了六位傳統女性的悲苦命運,對生活在父權制社會中的女性寄予了深刻的同情。
2.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創作于20世紀末的小說《赫索格》已經受到了蓬勃發展的激進女權主義運動的影響,帶有明顯的對于“新女性”形象的建造。貝婁在《赫索格》中構建了一位獨立自主、我行我素的“新女性”形象——瑪德琳。當赫索格憤憤地譴責瑪德琳忘恩負義的同時,也有許多不同的聲音在肯定她。瑪德琳的姨媽澤爾達認為她是一個“莊重” “正經”的女人;曾選修過赫索格的課的杰拉婷·波特內在心中也對瑪德琳大加贊賞,認為她有能力把握命運;赫索格的律師朋友桑多和他的妻子也同樣認為瑪德琳是一個好人;就連心理醫生埃德維也替她辯護。這許多人對瑪德琳批評并不像赫索格所說的那樣的不堪,可以反映出貝婁借他人之口間接肯定了像瑪德琳一樣的“新女性”,從而反映了作品中體現出的進步的女性觀。
赫索格對瑪德琳的態度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瑪德琳的美貌、能力吸引了他,他瘋狂地追求她,希望從此過上浪漫激情的生活;瑪德琳對他的背叛讓他充滿憎恨,認為這個“壞女人”想要奪取他的一切并且要搞垮他;然而當他在充滿殺意的時候看到瓦倫丁為小女兒瓊斯洗澡的溫情一幕時,他被感動了;當他發現瑪德琳并沒有讓女兒與自己家人疏離時,他開始反省自己,開始意識到女性及女性特質的可貴可敬之處。他開始放下過去的一切仇恨,以一種全新的態度來迎接未來的生活。
三、猶太文化與美國文化的沖突與融合
索爾·貝婁是一名美籍猶太作家,身受猶太傳統文化——典型的父權制文化的影響。在猶太文化中,男性將女性看作欲望的客體,將其視為“第二性”,作為男性的附庸品而存在。男性作家將自己的審美理想和愿望強加在女性身上,塑造的女人不是“溫柔、美麗、順從”的“天使”,就是“淫蕩、自私、丑陋”的“妖婦”形象,而這種所謂的“天使”或“妖婦”只不過是父權制下根深蒂固的厭女情節。貝婁以赫索格的口吻通過對瑪德琳“壞女人”形象的描寫來論述赫索格的悲慘生活。《赫索格》中所凸顯的厭女情節也是可以找到它的淵源的——猶太文化在索爾·貝婁身上的傳承。
貝婁是在美國長大的第二代猶太移民,盡管身上存在著濃厚的民族文化痕跡,卻不能與美國主流文化分割。首次,隨著歐美女權運動的發展,生活在“新女性”第一次登上歷史舞臺的時代,貝婁深受第二次女性主義思潮的影響。《赫索格》中瑪德琳不同于父權制社會的傳統女性形象,突破了“天使”與“妖婦”二元論,顯示了貝婁女性主義的寫作傾向。再次,20世紀中期,美國社會由工業社會步入了后工業社會,社會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傳統家庭結構解體,享樂主義盛行。社會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促使同時代的貝婁對女性的態度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貝婁通過小說中其他角色之口間接對瑪德琳的肯定也是對當時社會趨勢的一種跟隨,體現了小說《赫索格》中所具有的進步女性觀。
無法在猶太文化和美國文化之間做出選擇,而又將兩者對立起來,貝婁表現出一種同時代美籍猶太作家所共有的糾結與掙扎——一種獨特的“美國性”。
【參考文獻】
[1]李滟波.從《圣經》看西方厭女癥的源頭[J]. 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3).
[2]劉鋒.《圣經》的文學性詮釋與希伯來精神的探求[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3]吳曉東. 20世紀外國文學專題十三講: 插圖本[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