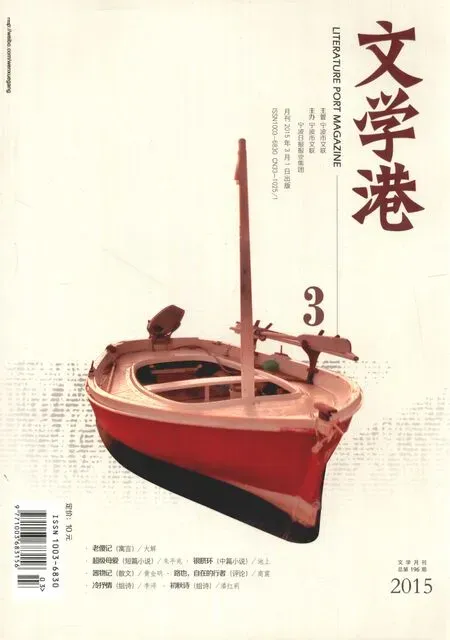器物記
黃金明

1、木器與木匠
在鄉村,木器隨處可見,數量繁多,大至木屋木船 (含龍舟),小至木勺耳挖,甚至所謂鐵器也總離不開木頭。譬如刀斧必安裝著一截木柄,如木犁、耙等則跟鐵器混合組成,但畢竟還是木器。南方罕見小木屋,木頭乃常見的、必需的建筑材料及裝修原料,譬如橫梁、檀柱、格子、門窗、門檻、門框、門扇、門閂諸如此類,都由木頭唱主角。
木器可粗略分為三類,一類是木頭工具,如木棰,木砧等;一類是木頭用器,如戽擔桶、酒桶、擔水桶、洗腳盆、“耙趟”、風箱、風柜、木籠、神龕、木槌 (供敲銅鑼用)、木秤、木尺、刨 (除刀片部分亦全為木器)、墨斗、瓦缸蓋子等等,僧人用的木魚及戲班子用的木刀尚不算在內。最后一類即為家具,如床、柜、箱、椅、桌、凳等。木器的普及比竹器有過之而無不及,且更牢固耐用,對制作者的技藝要求也更高。鄉間幾乎每個男子都會編織一兩件簡單竹器如畚箕之類,要做木工則須有專人傳授。光以木桶而論,就有水桶、糞桶、潲水桶、戽擔桶、酒桶、米桶等之分,其實都是木桶,大同小異,只因功能或用途不同,有的吃香喝辣,有的以屎尿為伍。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們挑井水都用木桶。那些木桶多以杉木板拼嵌而成,桶板之間純以木頭楔子拼接,再圍繞桶身箍兩三道鐵線,牢固異常,亦不會漏水,用三五年沒問題。據說箍桶的環節很關鍵,故在木匠之外衍生出箍桶匠這一職業來。很少木桶會突然散架,由于桶耳的木板常跟鐵制的擔水鉤相摩擦,木不敵鐵,卻磨損嚴重乃至朽爛了。一次,我挑一擔水走在村巷上,突然感到肩頭壓力驟然一松,耳畔聽得一聲炸響,一只桶在石巷摔得四分五裂;另一水桶亦砸在地上,還好沒有受力,尚能保持完整。
戽擔桶是常用的戽水工具,從溪河戽水上田或捉魚,跟戽斗一起使用,大顯身手。戽擔桶的主體是一個小木桶,跟洗腳盆相仿,桶邊按二等分處嵌有兩根木楔,木楔兩端各系著一根長繩子,須兩人雙手各執兩根繩子以配合使用。手一起一落之間,讓木桶裝水,潑灑,再切入水中,再潑出去,如此周而復始,直至大功告成。操作者如控制傀儡一般,有著奇特的韻律,操作者借助上揚及下蕩之力,頗得用力之巧勁,不太勞累,有時一干就是三五小時。
鄉間常見的搬運水工具乃是水車,但水車也越來越罕見了。在中火嶂腳下的溪畔急流處,尚有巨大如摩天輪的圓形水車,像車轱轆般亂轉,是利用水力來拉動磨米和磨面的機械。我在水碓邊的鄰村見過龍骨水車,形如龍舟,水從一端灌入,被輸送到另一端上去,倒是毫不費勁,稱得上木制機械中技術含量較大的木器。戽斗是用竹器編織的器具,呈“U”狀,裝上竹竿長柄,由人持著使用。
鄉間的家具基本全是木頭打制的,布藝、金屬、塑料家具乃是九十年代后的事。鄉間的家具亦相當粗陋,連木頭沙發也不多見,坐具以條凳、板凳、椅子為主。餐桌多是那種方形的八仙桌,卻用足材料和功夫,貨真價實,經久耐用。比較考究的是新婚用的大床及柜子 (除了放衣服,還將細軟、契約、證件之類放入暗格或小抽屜)。年輕男子結婚,再窮也要設法請木匠打一套像樣的家具,主要是床、衣柜、碗柜、梳妝臺之類。床是那老式的,床母上雕龍畫鳳 (改為:刻鳳),或雕些花草鳥獸,整張床十分結實,床腳由厚重木頭做成,床柱子及架子亦毫不含糊。不用木板做床板,而以竹篾織成的床寮 (鄉間頗為簡陋的竹器,先削好寬大如拇指的竹片,再以細軟小篾條縱橫交織而成),睡上去既韌實又有彈性,比彈簧床墊及硬板床都舒適。還設有床屏和木頭做的床架子,以供罩蚊帳之用。
蚊子猖獗,無論有多少驅蚊法如燒蚊香、滅蚊器及電蚊拍之類,最有效最環保的仍是掛蚊帳。雙紗蚊帳能更好地將蚊子拒之床外。老一輩用的多是自家紡紗縫制的麻布蚊帳,染得漆黑,倒是不易辨認蚊子 (因蚊子本身亦灰黑如帳)。一襲雪白干凈的蚊帳乃小媳婦引以為豪的事,臟了就洗,拿去山坡的灌木叢上撐開曬干。那種老式木床,我在城市已無可尋覓了。全是歐式木床,多輔之以床墊使用,要掛方形蚊帳更無計可施。直至近年市面出現了一種鐵架子,可利用床腳固定以掛蚊帳,才算解決了問題。
鄉間人家對床及衣柜十分重視,很可能這輩子就打這么一套了,故馬虎不得。床也結實,睡幾十年沒問題。衣柜高大,間隔多而深,就像一個百寶柜,棉被、衣服及細軟等分門別類塞入其中。柜門雕鏤著各式吉祥花卉及珍禽異獸,如我家的柜子,就有“花開富貴”“龍鳳呈祥”“壽比南山”之類,雕工不俗,刀法靈動。富貴是村莊最后一個會雕刻工藝的木匠,他過世之后,村里已無人能在床、柜上雕一朵小花了。
大堂哥十七歲時去海南做木匠學徒,等我上小學時,他已是手藝不錯的木匠了。他除了掌握多種尋常木器的做法,在家具廠,還是做新款西式木床、餐桌及沙發的主力。
那年夏日,他砍伐了家里的幾棵大樹 (以苦楝樹及杉樹為主,算不上名貴,卻是村莊常用的木料),要親手打造一套結婚用的家具。床是西式的,也不打傳統的條凳,而是含兩個小茶幾五件套的西式沙發。這在村莊都算新鮮事。夠不上移風易俗,卻也別開生面。大伯父滿腹牢騷,嘮叨說:“我從未見過這樣的床和椅凳。也不知道吉不吉利。上下兩村可有這樣的古怪家具?”大堂哥只管推動著手上的刨子,卻不管他。一塊木板在他刨動下,變得光滑閃光,一塊塊單薄而柔軟的刨花從刨子上吐出來,像大堆泡沫在庭院里膨脹,空氣中彌漫著新鮮木料的清香。這些刨花將被堂妹塞入爐膛中去。沒有比這更奢侈的柴禾了,它們在爐膛中發出火焰,幾乎沒有灰燼。
我吃飽就蹲在一旁看大堂哥作木工,他用鋸子將木頭鋸開 (鋸成木板或木方),用刨子將木頭刨得光滑,用墨斗上的黑線使木頭筆直。他的耳朵上架著半截鉛筆,偶爾被取下來使用,大多數時候架在耳根上,堂哥動作幅度甚大卻不會掉落。旁邊的工具箱雜七雜八地放著鑿子、刨子、錘子、刀片等各類工具。那些或長或方的木板,或粗或細的木方,還有一些有著流暢線條的彎曲木件,在大堂哥魔術師般的手上組合成了床、沙發、椅子、衣柜和櫥柜,那些嶄新的木器在院子里直立著,仿佛具有了生命,至于上漆及打磨,那是輕松的工作了。
我央求大堂哥從一截圓木鋸下一小截橫斷面,并鑿了一個孔眼,稍加修整,就成了一個小車輪。我又從邊角料撿了幾塊小木板,再利用錘子和釘子,圍繞車輪為核心,制成了一輛小輪車。我在上面運送做游戲用的稻草、苦楝子及土塊諸物,還拉著妹妹在村口轉來轉去。妹妹坐在小車上,快活得咯咯大笑。那個夏天,我成了村莊最神氣活現的孩子。
木頭轆轤可能是村莊最簡易的打水機械。只要輕輕搖動木頭上的鐵制搖柄,木頭就會將連接著的繩子一圈圈地收緊,將繩子末端上系著的一桶水緩緩升至井口。轆轤使繁重的打水勞作變得輕巧,并具有了幾分悠閑。
木頭風箱是一個長方匣子狀的鼓風器,構造復雜。有四個“掩”(閥門)及雞毛做成的活塞諸物,我一直想將其拆解以洞悉其秘密,沒有如愿。仿佛里頭有一個小獸張大嘴呼氣,只要輕輕一拉風箱桿,一股風就會將爐膛的灰燼變紅,并使柴禾尤其是木柴燒得噼啪作響。村子使用風箱的人不多,大多是用竹筒制成的吹火筒,用嘴沖著爐膛吹風,也起到一定作用,只是常被煙火熏燎得灰頭土臉,乃至涕淚交流。在打鐵鋪里,風箱倒是必不可少的用具,風箱口發出的強風使鐵器在炭火中變紅、發軟。
2、陶器
陶器 (鄉間瓦器亦多,除碗碟諸物外,瓷器倒不多見)易碎,絕大多數是用具,跟鐵器及木器相比,做不了工具,偶或做玩具 (如泥雞、陶俑及瓷狗),至于景泰藍之類的工藝品,在村莊從未露面。它作為器具,有時跟木器重疊 (如碗、盆),有時跟鐵器重疊 (如煲、壺)。陶器由泥土焚燒而成,大多數僅充當容器之用。陶壁里的空洞、空無或虛無,乃是燒陶工的用意之所在。正如人們建房子,要用的乃是房子里的空間,但沒有四壁,那個空間也不會存在。多年之后我寫詩,覺得詩大于一切材料的總和,卻不是材料的簡單相加或集合。詞語及句子僅是磚石及其他建筑材料,僅是那堵有形而堅實的墻壁。詩在其中呈現卻無法捕捉乃至描述。
當我們說寫詩,其實詩是無法被寫出來的。我們只能通過語言的囚籠去暗示那烏有的籠中鳥。運氣好的話,詩也許是那些語句之間的縫隙及空白。大多數的時候,詩仍在某些神秘的事物中沉睡而不被打擾。你可以感覺到,但無從言說。
村莊里的陶器首先用來裝水或液體之物 (如油、酒、醋及煤油),陶器的堅硬及密實使其愉快勝任。廚房里有寬口大水缸、酒缸、尿缸、油罐、水罐、咸菜瓦埕及淡豆豉壇子諸如此類。陶器同樣是盛裝五谷及雜糧的容器,放上蓋子,可防鼠防蟲,如裝谷米、薯類、豆類、米粉等。按其容積及用途,陶器庶幾可分為缸、壇子 (埕)、罐、盆、碗、碟、“瓦竇”(陶瓦燒制的空心管道,用于鋪設下水道或連接起來做煙囪,乃鄉間有特色的陶器)之類。那些大大小小的壇子,還是制作各式各樣咸菜的醬缸及貯藏之所。鄉間最常見的咸菜有以蘿卜做的蘿卜干及“菜苗”,用白菜及芥菜做的酸菜,用芋頭葉梗做的芋殼,用黃瓜做的黃瓜干,用蒲瓜做的瓜咸等等,制成或晾干之后,將其存入壇子密封,需要食用就去掏挖。
陶器終究會破碎,有的大缸先是裂開一條肉眼難以看見的縫罅,之后逐漸擴大裂痕并最終在地上四分五裂。有的壇子在塞咸菜時撐得太滿了,被生生撐爆。有的壇子于寂靜無聲的某個角落忽然“噗”地炸裂,那記聲音足夠讓屋子的每一個人都聽得真切,仿佛它的破裂是為了引起注意。爛得最快的是瓦煲,飽受水與火的煎熬,很快就會裂開而不堪再用。碗有時在孩子的手上突然滑落,在地上摔成碎片。多好的碗啊,嶄新,光潔,如果不是摔破的話,用上七八年仍簇新如故。孩子摔爛碗讓父母痛惜不已,又惴惴不安,據說此乃兇兆,必須有娘家煮糯米飯買洋傘送來,方可破解。如此一來,那個碗的損失似轉嫁到了娘家。有的娘家不太樂意,卻不得不辦。這就是風俗的力量。至少,鄉間很少有人像電視里爭吵的小夫妻故意摔爛碗碟。
洗腳盆、尿缸等經常使用的陶器也會爛得快些。大缸似亦不及小壇子耐用。那年初春,有人在紫薇坡的花生地上挖出了幾個舊壇子,據說里面有蛤蟆、清水諸物,沒有發現目標中的白銀或銀元。紫薇坡數百年前曾是一外姓村落。后不知何故湮滅于塵土中,又見那些壇子,古舊不似近物,怕有些年頭了。
在過去,摔破了的陶器可以修補,此稱之為“補缸瓦”。鄰村就有“補缸瓦”的人。據說,他不僅可以將一個破缸補得滴水不漏,還能將破碗用鉚釘及某種特殊樹脂自制的膠水補好,難看雖是難免,卻不妨礙使用。在過去的數十年間,常有“補缸瓦”的人挑著工具箱穿村過寨。我沒見過該“補缸瓦”佬入村,也沒見過有人拿碗盆給人補。倒是有棉花匠、磨刀人、鄉村貨郎、閹雞佬、屠夫及劁豬匠等穿梭來往,層出不窮。

一次,我在鄰村見到了那個老人,他拄著一根拐杖在村巷里走動,很快就融入了墻角的陰影。我跟他的小孫子爬到閣樓上看他的工具,一只小風爐及幾把奇形怪狀的刀鉗之類,我無法揣測其古怪的用途。畢竟,碗碎了就算,已無人去修補。
3、掃把與畚箕,竹子與竹器
在鳳凰村,掃把是最常見的清潔用具。平時無人打掃村巷及山路,除了過年大掃除,方有人將屋邊四周打掃,反正是石板路或泥路,常有人行走,反倒干凈整潔,南方雨水充沛,亦有洗刷之功。在陰雨連綿的“漚水天”,土路泥濘,稀爛一片,讓人畜泥足深陷,反倒無法行走。掃把須臾不可或缺。最常見的掃把就是將“掃把枝”(山上生長的一種小灌木,枝干密集,葉子細碎如米點,花朵細小,呈淡黃色,除了供柴禾之用,其最大用途就是制作掃把了)砍回家,曬干并將葉子拍打清除,只剩下丫丫杈杈,用竹篾或麻繩 (后來尼龍繩、玻璃繩亦應用廣泛)牢牢捆縛,劈得大小適中的青篾條比繩子更好用,平時清潔庭院、掃地板,稱手好用。市面亦有出售。“掃把枝”堅韌耐用,并可掃除泥沙碎石,比其他材料 (如竹枝、塑料、豬鬃毛等)制作的掃把更好用。大掃除時,在掃把上插一長竹竿作柄,就能打掃屋頂及四壁的蛛網及塵埃,或掃凈床底下的垃圾。
此種掃把除了搞衛生,還是曬谷子時收集稻谷的重要用具,常跟“耙趟”(由木棍嵌入一塊木板組成的農具,可用于平整農田、收攏東西如泥土、谷子等)連用,可謂焦不離孟。先用“耙趟”將谷子往曬坪中央集攏,再用掃把將薄薄一層谷子掃去,一粒不剩。掃把平時就放在墻角或曬坪上,隨時可用。一個家庭,常備有六七把之多。掃把用久了,必遭磨損,掃把枝磨得鋒銳光滑,如锃亮利刃,被磨損至只余光禿掃把頭,方才丟棄或塞入爐膛化為柴薪。
針對不同的清潔場所,常備有不同的掃把,如掃谷、掃地及掃豬圈的掃把,各有分工,不可混用,否則就失去了搞衛生之意。“天地間有一把大掃帚在揮舞”(歌德語),說明了其清掃的用途,而最終也將自己掃除。畚箕是一種用竹篾編織的容器,一端是圓弧,箕口平直,狀如字母“D”,上面用竹篾安裝擰麻花似的四條提臂。可盛裝東西,如裝土糞、沙石、薯類等,在裝柴禾時那些提臂被撐大至圓形,用途之廣,難以盡述,裝垃圾不過是其偶爾使用罷了。畚箕跟掃把關系很密切,猶如菜刀與砧板,鐵鍋與鍋鏟,瓷碗與筷子,湯盆與勺子……類似的拍檔在鄉間舉之無盡。掃把將垃圾或廢棄物收集,并裝入畚箕倒到竹林、池塘邊或河灣上去,那些地方儼然成了垃圾池。開頭尚未見弊端,待垃圾成山之際,村莊已略顯頹敗,有些本事的人,都進城打工或定居去了。村中人越來越少,垃圾堆倒是越來越大。
上述介紹的掃把,乃是最常見及最重要的一種。除了掃地、收谷,尚有無數處所需用到掃把,譬如餐桌上掃除骨頭菜梗,在使用抹布時先得用一種小掃把 (用麥秸、椰子皮或脫粒后的高粱穗制作,此類掃把亦叫“掃”),如手臂般粗細,比通常掃把小得多,洗鐵鍋、洗銻煲、刷水桶及掃灶頭。這種“掃”材料較柔軟,說是掃,不如說是“拂”及“抹”,用于清潔灶頭、餐桌等方便靈巧。好在制作掃把的材料取之無盡,方法亦簡單,即使是八九歲的孩子,亦能掌握。
鳳凰村竹木山林甚多,幾乎每一戶人家的屋邊,都有一叢竹林,在鬼落山、園山、屋背山諸坡,更是竹海浩瀚,無邊無際。竹子種類亦多,有大斑竹、火格竹、單竹、篁竹諸種,適合不同的用途。大斑竹粗碩堅硬,甚難劈成篾條,但堅固厚實,乃做扁擔之材,亦可代木頭搭棚架及做梁柱之用。單竹竹壁單薄,竹管內空大,易于削砍,但皮脆肉酥,易于操作,卻不耐用,除了編織那些南菜北運用的一次性籮筐外,頂多用來扎籬笆,沒有多大用場。而火格竹就較于這兩者之間,是編織竹器的最佳材料。篁竹細小結實 ,多用于薯類上籬樁及扎籬笆之用,亦可削制竹笛。
竹器竹類繁多,充當了農具 (如籮筐、畚箕等。竹頭又是連枷的主體,稍加削整光滑,保留其棒槌狀頭部及弧度,中間鉆眼,裝入小木槌以作連接,另一端接上一截木頭為槌,就成了脫粒時最常用的連枷,即“禾把子”。使用時,高高揚起,重重砸下,下一著借勢將棒槌揚起,如此反復輪回。使用的依然是簡單的杠桿原理,卻比光拿棒子敲打稻穗更省力高效)、漁具 (如魚籠、魚簍)、生活用品 (如筷子、牙簽、紙扇)等,沒有一個農家能離開竹器。眾所周知,各類竹筍可食,是不錯的蔬菜。村莊的人也偶爾拗幾只嫩筍放入泡制芋殼 (香芋的葉梗,可做咸菜)的醬缸中腌制,味酸爽口,滋味不俗。但嫩筍及筍干的吃法,在村莊極少人嘗試,亦不知何故。
竹子或竹篾的用途十分廣泛,如編織籃子、雞籠、牛笠 (套在牛嘴上的罩狀竹器,防止牛吃莊稼用,而又有孔眼供其透氣),亦可應用到其他器物上去,或成為其部件,或作捆綁之用。豬肉佬亦用細篾條扎豬肉。篾白是類似于火炬的東西,點燃了火光熊熊。籬樁、扎籬笆、建房子、“莢茅”(用竹篾將稻草捆扎起來,乃茅屋頂的主體,可遮風擋雨)、斗笠 (先用篾條編織成頭盔狀再填充以巴掌大的竹葉)、葵篷等雨具,主體亦是竹篾,數之無盡。竹子乃牙簽之母。在漫長年代里,村人上茅廁刮屁股的東西不是手紙,而是篾白。而“竹攪”(乃篾白別稱)火向來是對付雨天“沙蟲”咬腳的唯一方法。竹 (竹竿、竹枝、竹葉以及竹筍殼等)所有部分,曬干了都是不錯的燃料。淡竹葉可入藥,單竹芯亦有清熱解毒之功效,父親常去拔來數根,放入中藥煲涼茶。
上述只是竹子的實用功能,至于其制作玩具、工藝品、美學意義以及君子之風的道德寄寓,農民既不了解也不關心。竹林中十分靜謐,輕風吹拂竹枝的簌簌聲及竹子被搖撼發出的空虛之聲,幽遠、清亮而悅耳,仿佛風鉆入了竹管內部而在演奏。竹子是笛子等多種樂器的前身。每株竹子都是一支及數支潛在的笛子,猶如雕像隱身于石頭之中,只要將多余及淤塞之物鑿掉、剜除或打通,就改變了其面目及腔調。
我常在竹林中踱步,只為了享受那份闃靜及吹過竹枝間的風聲。林中也常有這樣的一只雞,幾只鳥。它們比我更悠閑,又準確地啄食泥土和草葉上的蟲豸。我偶爾順手撿幾片竹筍殼及竹枝做柴禾。有時也在地上尋覓竹蟲的幼蟲。我像勘探礦藏的人細心察看,并常有收獲。竹林是一個小世界,里面棲息著麻雀、翠鳥、紅嘴鴉等鳥類、“青竹標”等蛇類及無法計數的蟻類、蝶類、“割蟲”等昆蟲。竹林中的雜花野樹繁茂異常,在金銀花、白花茶的濃郁香氣和雪白花瓣之上,常有大黃蜂及色彩斑斕的蛺蝶在飛舞。它們輕盈、單薄的翅膀宛若飛翔的花瓣。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最后一年,有人發現竹子像稻子一樣揚花并結穗,就像是放大的、巨型的稻花,色澤和香氣都有相似處。這不是一叢竹子,那幾乎是整個村莊的竹子,鄰村如荷木垌、胡家莊及大孫村也傳來了竹子開花的消息。這是不祥之兆。
據說,竹子開花六十年一次,一個甲子就是一次輪回,毫厘不爽。仿佛有神秘之人在暗處準確地計算,并提醒了每一株竹子。但問題是,這個六十年的最初一次是如何確定的呢?是誰確定并憑什么確定呢?為什么不能早一年或晚一年?這個六十年似跟竹子的生長期無關,而是說,當輪回之年,竹子們就必須死去 (枯萎、發黃而最終變白)。到了秋日,竹籽逐漸飽滿而成熟,竹子大片大片地死去,不分大小、粗細、種類及老嫩。枯干的竹子連竹葉都呈現出灰白之色,宛若森森白骨,之前的青翠已褪色,在秋陽的照耀下讓人心生悲愴而驚懼。竹米的形狀、粗細,都很像稻米而呈褐黑。上一次竹子開花結籽時,正值饑荒之年,有人煮食竹米而不能消化,比觀音土更讓人致命。在農民看來,竹米乃無用之物,其繁衍不需要竹籽,大多不能食用,顯得邪氣,隨之而來的是竹子大片死亡。事實上,竹子開花的周期太長而讓人無法適應。《山海經》云:“竹六十年一易根,而根必生花,生花必結實,結實必枯死,實落又復生。”《晉書》亦有記載:“晉惠帝元康二年,草、竹皆結子如麥,又二年春巴西群竹生花。”目睹過兩次以上的,不會是年輕人。
一直到翌年初春,才有新生的竹筍從地下鉆出,并將成長為新一代的竹子。看來,竹子的死亡盡管徹底,但還不算是毀滅性的,因為沒有觸及其根基。
竹制品在鄉間占據著重要地位,大至可以搭棚架屋,編筐織籮,小至筷子牙簽,無不與竹有關。竹還是造紙的重要原料,在廣東恩平一帶,至今還有人用土法造紙,暢銷不滯。
竹屬“歲寒三友”,又名列“四君子”,詠竹畫竹者眾,又有“食可以無肉,居不可無竹”之說。這也是文人騷客吟風弄月附庸風雅。我從未見過文人的詩或畫出現過竹蟲,仿佛竹蟲乃是烏有之物。這也難怪,這種長相奇特丑怪的昆蟲,實在大煞風景,不比蝴蝶斑斕,可入莊子之夢,不比蜻蜓點水,可烘托尖尖小荷。據此亦可見文人的價值之取舍。所畫之竹,不是真實之竹,實乃抽象之竹;所詠之竹,不是自然之竹,實乃理想之物。說到底,都是借竹而另有寄寓,或一吐塊壘,或癡人說夢。但竹蟲便無一可取之處。
但問題是有竹的地方便有竹蟲。文人掩目捕雀,孩子卻求之不得。在每一處竹林中,都有半截竹筍斷裂,掉在地上。這便是竹蟲的杰作或罪惡。筍尖斷落的竹筍,還會繼續生長,并剝落竹殼,抽出竹枝,長大成竹。但已經是不存在竹梢的無尾之竹。這樣的竹子往往不夠堅韌,材質不佳,不堪大用。
竹蟲分成蟲和幼蟲,幼蟲蛹白白胖胖,在密封而黑暗的巢里吃喝并生長,它不需要光明,漆黑恰巧可以掩飾其勾當。而成蟲是一種外貌丑怪的甲蟲,身體狹長,背部長著兩片硬殼,硬殼下面是柔軟的羽翼,腹部有四對鋒利的爪子,嘴部有一根尖長的吸管。就此而言,跟蟬類有些相似。蟬蛹在地下生活,而竹蟲蛹在鉆入地下之前,首先要過一段漫長而舒適的“竹居”生涯。
竹蟲飛行敏捷,屢在竹林中穿梭,看見竹筍破土而出,就咬破筍尖,在竹筍里播種。竹筍就是竹蟲蛹的小巢,實際上乃是竹筍的蛀蟲,很快便將竹管蛀空,只剩下一層薄薄的管壁,而筍尖也日漸枯死。至于嬌嫩而多汁的筍肉,早已成了它的腹中之物。它開頭只是米粒般大小,但很快便急劇膨脹,肥胖臃腫,大的幼蟲,可以長到成人拇指般粗細。當竹蟲在竹筍的尾梢發育壯大后,必連同竹筒從筍梢外斷裂而掉落。那截跟五號電池般大小的竹管里,散發出嫩竹纖維被蟲子咬食的腐敗氣息,里面居住著一只白胖的蟲子。它比最魁梧的蜂蛹還要雄壯,它將鉆入泥土生活一段時間,并像蟬那樣脫殼而長出翅膀。成年的竹蟲是一種黃褐色的甲蟲,肉質硬如木石,但幼蟲卻乃美味。在粵地不少竹海風景處,便以食竹蟲為噱頭而招徠游客。
我幼時去茅坪祭祖時路過一個村莊,我們上茅坪山祭完祖后,在返程中都會經過一個村莊。村莊就在水邊,它的名字叫“水”。這是一個夢幻般的村莊,每次想起它,我都有一種怦然心動的感覺。據說村莊有六七百年的歷史,還保存著不少古建筑。村口的牌坊和村巷兩側那些油漆剝落、勾心斗角的屋檐,對于一個孩子來說顯得新奇。村莊的人穿著灰褐色的葛衣,頭戴尖頂斗笠,腳踏木屐,面容恬靜平和,頗有古風。我仿佛回到了古代,我所遭遇的乃是一個從古代走來的村莊。
河邊長著茂密的竹林,那些竹子又高又大,把竹筒鋸下來稍作打磨,就是很好的米升,我家里就有一個,但我不知道它來自這樣的竹子。這種竹子的奇特之處還在于它的葉子,大如手掌,長逾一尺,在清風中輕輕吹動。以前我曾在斗笠的夾縫和煮熟的粽子上見過這種寬大竹葉,現在得以目睹它的真容。這樣的竹子,猶如唐朝的美人,臉如滿月,身材豐腴,一舉一動都有說不出的雍容華貴。
4、燈盞
村莊的夜晚仿佛是從大地內部的隱秘角落(如密林、房舍之間)滋長的。當太陽西沉,夕陽仍通紅如火球,天空上的云霞燦爛如燒紅的金屬,村莊逐漸陷入了灰暗之中。暮色越來越濃,天上的霞光已無力照入一座村莊層疊密實的屋舍間。夕陽像一個光芒四射但越來越暗的線軸,它往山坡下滾去,并一圈圈地收走了天地間的光線,村莊中此起彼伏的炊煙跟暮色融為一體。村莊終于步入了夜晚。天上明亮的星光,陸續亮起的燈盞,強調著這種濃郁得花不開的黑暗。在白天存在的事物,在夜晚都隱匿、消失了。譬如遠山、河流和田疇,連暗影也看不清。這一切就像變魔術,讓人感到新奇和不安。看不見不等于它們不再存在,夜空中傳來蝙蝠的吱叫聲,貓頭鷹的梟叫,還有躁動而興奮的狗吠,昭示了它們以及某些神秘之物的存在,但你無法目睹。
我坐在院子里,光憑那熟悉的腳步聲,就知道父親已回到村口,但要等好幾分鐘,才能在燈盞的微光看清他疲倦的面容。黑暗使那些無法發光的事物被遮蔽了,但同時使某些發光的東西彰顯。只有夜晚才提醒我,太陽遮蔽的東西也許更多,譬如月亮、星星、燈盞和螢火蟲。這些或近或遠或大或小的發光體,它們像閃光的釘子,使黑布袋般的夜晚出現了漏洞。如果不是夜晚,我將無法看清一只螢火蟲黯淡的藍光。所有的燈盞都在模仿太陽。
月亮從山岡上升起,并將其柔和、沁涼的光亮照耀在夏日的庭院上。月亮以鐮刀或圓甕的不同形象釋放著程度不同的光華。對于在夜晚略感恐懼的鄉村孩子來說,月亮永遠是最美的燈盞。它優美地高懸,月光像奶水一樣乳白、滑溜,夾雜著晚風中吹來的花香水氣。在古老的傳說中,我仿佛看到了月亮中的庭院,院中樹影婆娑的桂樹,以及被斧頭刃光反射的伐木者悲傷的額頭。對于兔子,我總是無從猜想。我沒有見過兔子(哪怕是兔子的畫像或影像,也在入學后才見到)。月亮如一只白色的氣球,飄過果林和低矮的圍墻,釋放著越來越深的寂靜。月亮在發光,它不知道它的光來自何方。我驚詫于月光沒有溫度,但對其亮度略感不滿。在最亮的時刻,我也能就著月光在板凳上做算術題,它的光仿佛是霧狀的白紗,恰好可以做夜夫人的面紗,卻無法將黑暗驅散。
星光更不必說了。夏日繁星滿天。有幾顆星又大又亮,像閃光的寶石,尖銳,堅硬,它們像一把閃光的圖釘撒向了廣闊而起伏的夜空。它們像野獸的瞳孔在閃爍。的確有不少白色或淡黃的星,像誰的眼睛在眨動,而我看不到那張臉 (或是誰的臉)。
那個夜晚,父親帶我去農場看電影歸來。我伏在父親的背上,目光不可避免地被漫天閃耀的星光吸引過去。我仿佛聽到了一片嘈雜的聲響,浩蕩,吵鬧,仿佛是一條大河在天上流淌,并濺出了銀色的浪花。仿佛群星在吵鬧,在辯論、叫嚷乃至咆哮。我注視著漆黑夜空中無數閃光的圓點,我幾乎被匯入了那洶涌的星光聲浪之中。父親踩在泥路及草根上的簌簌聲,幾乎被我忽略了。
暮色降臨,村莊反倒變得喧囂起來。農夫們紛紛從山野返回,牛趕回來,放牧的家禽,被從村巷及山坡上捉回來,狗興奮地搖尾,吠叫。這種喧鬧聲將夜晚完全覆蓋,好久才沉靜下來。爐膛里火光明亮,映照出廚房里的東西、墻角上的小天井和水缸、灶頭上的幾只銻煲及鐵鍋,分別裝著烹飪中的飯菜及熱水。妹妹不斷地往灶膛添加柴禾。忙個不停的母親,像一個陀螺在團團亂轉。她在廚房和院子之間穿梭,準備著豬食、雞食,還忙中偷閑,洗好了鐵鍋及青菜。一些飛蛾及昆蟲因為火光的吸引,從四處撲來。有的蛾子和綠蟬,像一架小飛機莽撞地沖入廚房,撞到墻上。
在黑暗之中,那些發光的事物照亮了我的視野,盡管光亮如此微弱,我還是忽視了它們所照亮的是更大的黑暗這個事實。在鄉村之夜,有什么比一盞燈給我帶來更大的安寧?月亮太過高遠。燈光給我的不僅是光亮,還有爐火般的溫暖。一盞燈仿佛在黑暗中挖掘出了一個光亮的洞窟,它以微弱的光線頑強地守衛著脆弱而動蕩的邊界。我坐在那團光亮之中,感到黑暗看上去如鐵板一樣厚實。但也不是想像中的那么恐怖,只要點亮了那根細小的燈芯,就可以像變戲法一樣將黑暗驅趕。
在鄉間,最常用的照明工具是煤油燈。燈座由玻璃瓶子做成,如葫蘆狀,黃銅燈盞裝著棉繩編成的燈芯,上面蓋著薄脆的玻璃燈罩。
煤油燈的主要配件均可散買,我將母親買回的燈盞及燈芯安裝到空墨水瓶上去,我驚詫于其嚴絲合縫。村人稱煤油為火水,故煤油燈又名火水燈。這兩樣相悖之物被扭合一處,并不顯突兀,乃因水火相濟。在我們看來,火苗乃由“水”所滋生。燈座是透明的,可以看到煤油不斷耗損的過程及其余量。那些煤油看上去的確像水,它散發出一種難聞的味道,而火光就寄生于這些“水”之上,那條彎曲而垂落于煤油的小棉繩,源源不斷地輸送著煤油并保持火焰的持續。由于棉繩纖細,燈光并不明亮 (也許是為了節省煤油的緣故)。這樣纖巧的火苗迫使你安靜下來,哪怕是稍重的呼吸都可能將其吹熄。“熄滅”是如此容易,庭院于瞬間沉入了完全的黑暗。而一根火柴就可以將其點燃。當火柴上的火焰嫁接到燈盞上去,我才松了一口氣。
燈盞的熄滅,大多是由我們完成的。當我們完成了夜晚的事情,譬如吃飯、洗腳,父親偶爾的勞作如編織竹器,母親縫補舊衣……夜漸深,我們需要安寢了。燈光變得不再需要乃至多余。也是為了將煤油節省下來,留給下一個夜晚,我們湊近燈盞,鼓起腮幫子,用力吹氣,那動作和神情都是粗暴的,有幾分惡狠狠,務求一擊必中。“熄滅”帶來的黑暗類似于絕望。燈光是微弱的,我注意到它跟爐火有不同之處。爐火的強弱完全取決于我們每次傳遞的柴薪多寡,且帶著濃煙,當然,風箱或火筒的作用亦不容忽視。我們催動著爐火并保持著其連續性。而燈盞則是獨自燃燒,仿佛在黑暗中壓抑著啜泣的婦人。爐火中響起噼啪聲,仿佛木柴也被自己涌出的火焰所燒痛,并留下較大量的木炭及余燼。燈盞是寧靜的,孤獨的,它面對浩淼如時間本身的黑夜,因其纖弱光亮而倍加羞怯。我注意到燈繩也會耗損,并不可避免地化成灰燼。當燈光在變暗并跳動,眼看就要熄滅,母親麻利地剪掉了燈芯的焦灰,火苗騰地躥起來,恢復了光明。
一盞燈對孩子來說,猶如夢幻般的裝置或玩具,或一個神話國度中的器具,而這個國度純粹由這一片橘黃燈光所構筑。我在燈盞面前學會了遐想或沉思。我借助燈光看清了燈盞的內部結構及其如花朵的焰苗。這在它熄滅時看不到。燈光像某種奇異之物或類似于溫暖、幸福的情緒充盈了房間,并溢出窗戶而被黑夜所吸收,猶如墨汁在宣紙上緩慢滲透并凝固。正是因為燈盞,使我腦海中出現了白晝復活般的恍惚感,燈光改變了黑夜的顏色。我閉上眼睛,想象著另外的燈盞,在別的房間或院子里被點燃,那些燈盞和燈光都有某些相似乃至共同的東西,而在燈光周圍的人們卻干著不同的活計,或者發呆。在沖涼房 (洗澡間)中,燈影、水汽彌漫中的婦人胴體仿佛也在發光。小學生在燈下做著練習。而在鄉村,燈光作為一種照明工具,很少用來照耀報刊書籍之類的印刷品。沾滿油跡及塵土的鈔票是一個例外,農夫點數鈔票的時刻美妙而稀少。
父親經常等我們 (主要是母親)熟睡之后,偷偷起來點燃燈盞去翻看那些雜七雜八的書籍,內容主要是中醫、術數、堪輿之類,偶爾也會看一看舊小說。每次都是燈光將其暴露了,母親的斥罵聲將我們吵醒了。煤油是要用錢換取的,看書大可以借助日光而不必花錢,在夜晚點燈看,在母親看來太奢侈而浪費。
油燈可能是最簡易的燈盞。在重大節日如春節、年例之類必點油燈 (有信仰虔誠者初一、十五亦點),一只小碟子,一攤花生油或菜籽油,一根燈芯草,擺放在神龕或案頭上,燈草上的火焰細小而閃爍。這個習俗可能受到佛教的影響,庵堂廟宇就燈火長明。按佛教的說法,燈可破暗為明,在佛堂、佛塔、佛像、經卷前點燈,乃功德無量之事,于諸經記載甚多。村人在香火屋(即祠堂或大眾屋廳)或家中點油燈,意在祭祀及緬懷先人,寓意先人處身其間的幽暗長夜有大光明。油燈發出的光太弱,不足以照亮別的事物。在這里,點油燈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與其說為了照明,毋寧說是一種儀式。在此,“香燈”乃后代之代稱,譬如香燈有繼,固有薪火相傳之意,亦謂后繼有人。
由稻草編織成的“稈傳火”,在黑暗中散發出稻草的味道和濃煙,讓蚊子不敢靠近。它暗紅的火頭在明滅,偶爾一陣風吹,也會發出火光并于瞬間消失。因此,它帶來的光亮大可忽略不計。煤油燈還有一個用途,就是將蚊帳內外的蚊子燒死,使人們得以安眠。
偶爾也點蠟燭,但鄉間人買蠟燭照明成本太貴,不多見。孩子們將藥丸子外的黃蠟盒用鐵皮罐子煮熔了,夾著燈芯、倒入小竹管制作成的小蠟燭。這與其說是照明的東西,毋寧說是玩具。這樣的蠟燭來之不易,我們不會隨便點燃,要留在節日方才動用,點燃了也不是為了照明,而是欣賞蠟燭的火苗,以及燭淚在消融和堆積。到了一九八五年,村莊終于拉上了電燈,煤油燈才逐漸退出家庭 (因為經常停電或電壓不夠,電燈也不是每晚都能照亮)。電燈使黑夜亮如白晝,使黑夜的事物影影綽綽地露出了面目。電燈帶來的實用性毋庸置疑,卻削弱了燈盞給我帶來的夢幻及遐想。
火的光亮、熱度和它的顏色,使其仿佛是白晝的縮影或模型,是黑夜開出的花朵。火是夜晚在那黑色大氅上燒出的孔洞。我曾經試圖用兩塊堅硬的石頭制造出火星,在暮色之中,孩子用石頭猛力碰撞,火星只閃了一下就消失了,無法照亮任何事物,短暫到讓人的目光難以捕捉。但我們仍然興奮得歡叫起來。
鄉村的火種主要是火柴。一面帶著磷片的火柴盒,里面裝著數十根小木棍綴著棒槌狀磷球的東西。將火柴在盒上用力一擦,火苗騰地產生了,但瞬間就燒到了捏著火柴梗的手指,必須盡快將火柴投入爐膛或點燃燈芯。在發霉的天氣,火柴因受潮而難以點燃,母親將火柴及火柴盒放在嘴邊哈氣,以將潮氣驅趕,然后再擦。有時擦一根就著了,有時一口氣擦光一盒火柴,仍未能擦出火來,母親的臉色也跟著晦暗下來。
那種鐵皮打火機是鄉村的奢侈品,其頂端裝著小砂輪和打火石,用手扳動發出的火星,將煤油筒上的燈芯點燃。它就是一盞小煤油燈。擁有一個锃亮的打火機,是我的夢想,但打火機相當昂貴,也容易損壞。父親寧愿使用廉價的火柴而不愿購買那種看起來更像是某類鐵皮玩具的東西。
在寒冷凜冽的冬天,我們也會自制火爐取暖。如果能覓得城里人裝餅干或月餅的鐵罐子,只要在罐底鉆幾個孔眼,在上端穿一根鐵線以作提手,就是一個很理想的火爐。往里面投放切碎的木頭或竹片,火苗在飚出,而底部的炭塊艷紅如寶石。我提著火爐,踩著田野上枯干的草根,或走在寂靜的村巷上,胸口暖洋洋的,一股巨大的幸福或陶醉籠罩著全身,像國王一樣滿足。是的,我就是這個火爐的小領地的君主。在火爐四周,圍聚著一群臉蛋兒凍得通紅而快活的孩子,他們將手湊近火爐,讓火的溫暖驅趕在空氣中不斷堆積的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