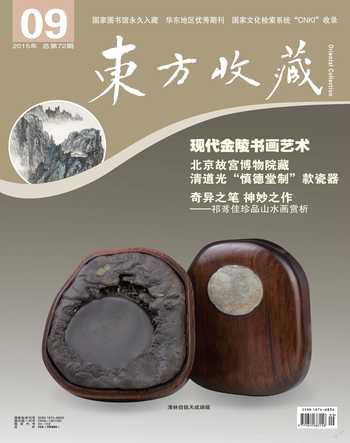大器晚成習石鼓 道登天門臻化境
趙紹龍
回憶起蕭嫻90壽辰的書法展,依稀記得展覽的場面轟轟烈烈。現場“道登天門”四個大字,以奪人的氣勢涵蓋了整個展廳。85件力作光彩照人。蕭嫻被熱情的人群包圍著,我竟不能走近她一點,只好遠遠地站著,從老人慈祥的微笑中分享她內心的幸福。
記得那天揭幕儀式結束后,我和美術館副館長老馬去隔壁漢府飯店看她。輕輕敲開308號房門,她女兒江鳳子躡手躡腳迎出來,說老人睡了。“她太激動了,沒想到一生清貧,粗茶淡飯,竟能活到90歲,更沒想到有今天這樣的盛況。我怕她累了,勸她安安靜靜躺一會。”
我們不敢打擾,另找一處小坐。談起蕭老的身世經歷,都十分感慨。
有人說蕭嫻是大器晚成,其實,她從少年時代就脫穎而出了。父親蕭鐵珊善寫字,篆、隸、行、楷都會,蕭嫻自小幫他磨墨牽紙,耳濡目染。有一天他寫了字就出門了,蕭嫻照著寫了一張。父親回來,發現多了一張,問女兒有誰來過了。蕭嫻說沒人來,是她寫的。父親不信,蕭嫻又寫一張,果真不錯。從此就正式教她寫字。13歲,為廣州大新百貨公司落成寫丈二匹對聯,字大如斗,社會震驚。15歲,應邀參加宋慶齡舉辦的名家書畫義賣,受到孫中山贊賞。20歲時,蕭嫻寫給朋友的一幅西周金文 “散氏盤”,被當時的碑學大師康有為看到,大為欣賞,并且很有興趣地補了一段題跋:“笄女蕭嫻寫散盤,雄深蒼渾此才難,應驚長老咸避舍,衛管重來主坫壇。”衛夫人、管夫人都是我國古代著名的女書法家,衛夫人(衛鑠)還是王羲之的蒙師,曾著有“筆陣圖”,影響深遠。康有為作此比喻,可見他對蕭嫻的器重。
說蕭嫻大器晚成,或許含有另一層意思。蕭老曾經向我談起,她的生活道路很坎坷的。其夫江達青年時期在法國和德國勤工儉學,30多歲回國結婚,懷著一腔熱血,想通過煉鋼救國圖強,卻得不到當權者的支持,處處碰壁。蕭嫻通過父親求人,才找到個 “抄寫”的差事。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后,一家人顛沛流離。為圖生計,她在成都與畫家王東培聯名搞了個書畫展,賣了幾百元。后來還是朋友幫忙,到西北路局當過收發,又去造紙廠做些寫寫算算的雜事。在那種社會狀況下,書法藝術有誰重視呢?可以說,蕭嫻在相當長的歲月里,是被社會遺忘了。
我認識蕭嫻,是在 “四人幫”被粉碎不久,正是撥亂反正、百廢待興時期。她的書名已經很大了,生活上卻依然清貧。印象最深的,是她的住所。那是在玄武湖畔,一個菜農市民雜居的近乎鄉村的地方。竹籬笆院墻上,爬滿絲瓜一類藤蔓,院子不小,種著幾畦菜蔬。破舊的平房里光線似乎很暗,連櫥柜等老式家具也蒙上暗黑的調子。蕭老心情卻很好,跟我談了許多書法上的事。她說寫字要下苦功,甜水中不容易學到東西。寫字又是一種修養,所謂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不可把名利金錢看得太重。這些話,我一直牢牢記著。
80歲以后,蕭老的境遇有了很大的改善。她從江蘇省文史館調入江蘇省美術館,成為專業書法家,并被評聘為一級美術師。她的平房,由于女省長的親自關心,遷入鎖金村寬敞明亮的新居。她的體魄也比以往更健壯了。蕭嫻的書法藝術,進入一個新的時期。用她自己的話說,寫字的時候,性格、環境、乃至社會,都一起反映到筆底下來,那面貌還能不變嗎?1981年,蕭老先后在南京、貴陽、濟南等地舉辦個人書法展,作品被各地博物館、紀念館、名勝地收藏或刻石、制匾,享譽國內外。
這么說,蕭嫻也真是大器晚成了。
蕭嫻書法最大特點是有一股豪氣。這當然與她的性格有關。蕭老說:“我的脾氣急,性子野,喜歡寫大字,不喜歡寫小字。”小時候先寫顏真卿麻姑仙壇記,她嫌其板,改學鄧石如隸書,那“疏可走馬,密不透風”的結體一寫竟成了黑墨團。于是又改學“石門頌”、“ 石門銘”、“ 石鼓文”,一拍即合。石鼓文是戰國時石刻大篆,樸茂渾古,不煩整裁,自有奇采。石門頌是漢代摩崖石刻,結字極為放縱舒展,奇逸奔放,氣勢磅礴。石門銘系北魏漢中石刻,自然超脫,飄逸奇宕。蕭嫻從“三石”中汲取、借鑒,遍覽浩如煙海的歷代碑帖,滋養了自己的藝術個性。又經康有為親授,特擅擘窠大字。那種渾厚、蒼勁和灑脫之氣,不要說在女子中獨一無二,就是在整個中國書壇也是十分難得的。近幾年,蕭嫻以其八旬高齡,游歷祖國名山大川,山川奇氣、日月精華,更添胸中豪情,運思揮毫,意氣常在畫中。當年,她為瑯琊山書寫“天門登道”,弟子桑作楷、莊希祖靈機一動,將其調換組合,成為“道登天門”,隱喻恩師藝術造詣之深,已臻化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