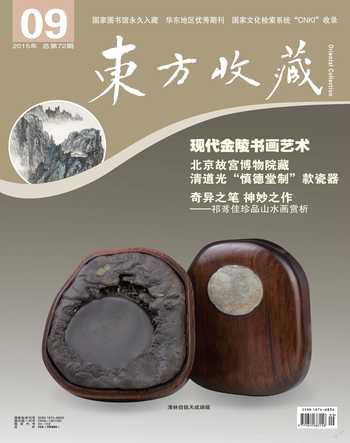賞“玉戚”話“親戚”
許滿貴
“玉戚”,先秦文獻記載為夏商周儀仗、樂舞禮器。成語“朱干玉戚”,典自《禮記·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孔穎達疏:“干,盾也;戚,斧也。赤盾而玉飾斧也。”即朱紅的盾牌、玉飾的斧頭,為古時作儀仗(樂舞道具)禮器。《公羊傳·昭公廿五年》:“昭公曰:‘吾何僣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詩經·大雅·公劉》:“干戈戚揚。”《禮記·祭統》:“大樂正學舞干戚。”《禮記·樂記》:“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注:“干戚并稱,皆言舞器也。”《韓非子·五蠹》:“執干戚舞。”《漢書·董仲舒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于庭,而頌聲興。”北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唐蠟百神樂章·舒和·凱安·送文舞迎武舞》有:“瑤弦自樂乾坤泰,玉戚長歡區宇寧”、“執龠持羽初終曲,硃干玉鏚始分行”、“玉鏚初蹈厲,金匏既靜好”、“既執羽旄先拂吹,還持玉鏚更揮空”的詩句。然而,“玉戚”源于石斧,原為兵器。“戚”是同一個氏族系列的斧鉞統稱,并與氏族血緣組織“親戚”有牽連。(圖1、甲骨文、金文、篆文等“戚”字書體演變)考證如下:
“戚”字在安陽殷墟甲骨文卜辭中有10個象形字(圖1)像雙刃上多利齒的鉞,一種戰斧。造字本義:雙刃帶利齒的戰斧鉞。《戚姬簋》金文(上圖示“戚”象形字)=干(武器,代戰爭)+八(“兮”的省略,表示嘆息)+戈(武器,代戰爭),表示因深受戰亂之苦而嘆息。《俶戚敦》金文(上圖示“戚”象形字)=虍(虎頭,代猛獸)+犬(代狩獵),表示對虎豹猛獸的擔憂與恐懼。秦·詛楚文(上圖示“戚”象形字)(河川受堵,洪災)+戈(武器,代戰爭),表示苦于戰亂和自然災害。有的篆文將金文的“干”、與“八”合寫成“尗”(讀音叔)。撿選《屯南甲骨文》、《甲骨文合集》“戚”象形字、《殷周金文集成釋文》,有16件西周早期青銅器刻鑄族氏金文“戚”象形字。觀之(圖2—1、2—2)一目了然。
殷墟甲骨文和族氏金文的“玉戚”的象形字,當可論定。(圖3)仰韶文化晚期扁平玉斧,南陽獨山玉標本,鄧州市八里崗遺址92F11出土:長8.9厘米,寬7.6厘米,厚1.3厘米。黑綠色,潤澤細膩。體扁薄,呈梯形。單面刃,背有管鉆而形成的大凹窩,器中部一側有對鉆穿孔。刃部有密集細長的擦劃痕跡,應屬勞動工具。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晚期玉斧(圖4):長13.1厘米,寬6.1厘米,厚1厘米。窄長斧形,圓弧刃,通體透紅,器面鉆三孔,大小不一,均鉆極其工整,器兩面加琢花紋帶。舉斧例可證,“玉戚”源自仰韶文化時期的勞動工具。玉戚、玉鉞在此前仰韶文化中沒有發現過,一般認為它是一種脫胎于石斧的專門性武器,它的出現,暗示戰爭或沖空與日俱增,這與考古專家在河南靈寶仰韶時代西坡遺址看到的防御設施和河南陜縣新石器時代廟底溝遺址的亂葬灰坑是可以相互印證的。
《說文解字》:“戚,戉也。從戉(讀音越)尗(讀音叔)聲。戉,斧也。”“鏚,戉也,斧之長柄者。經文皆從戚,俗作鏚。”“尗”本指一個豆莢內的豆子,字本義:兄弟序列,排行老三(伯、仲、叔、季,表示兄弟之間的關系)。“戉”與“尗”聯合起來表示“一個系列的小斧子”。段玉裁《說文》注:“戚小于戉。”王紹蘭段注訂補:“戚刃蹙縮,異于戉刃開張,故戉大而戚小。”“當有小義”,對照實物證明論點是正確的。“戚(鏚)”屬體形比較窄小的鉞;其體窄長,鉞刃略成弧形,后有方形的枘;鏚比鉞體略窄,在鉞體與鉞內之間有微凸的闌(橫擋),因其刃較長而常用于作斬首的刑具,亦作儀仗禮器。實物對照證明論點是正確的。《左傳·昭公十二年》:“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敢請命。”注:“鏚,斧;柲,柄也。”意思是說:“君王命令破開圭玉裝飾斧柄,請問裝飾成什么樣子。”(圖5—1、圖5—2)新石器時代神面紋玉戚:高20.6厘米,寬13.1厘米,厚0.4厘米。線刻,一側為神人半側面頭像,頭戴冠飾,披拂長發,眼眉清晰可辨;一側為一方形臺座上置神人冠飾的形象,象征軍事統帥權力。(圖6)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夏代四期寬扁體玉戚:長21.1厘米、高23厘米。粗白玉料制成,體寬身近方形,中間有一大穿孔,兩側各有六條突起扉牙,雙面刃,刃部仿璧戚類,等邊分切成四等份圓弧刃。夏代玉戚形制似鉞,長方或近似網形,器面有一大小不等的圓孔,兩側各琢出扉棱裝飾。
“玉戚”,在夏、商早期屢見不鮮。清人吳大澂《古玉圖考》對商代玉戚定義:“玉戚,舞器也。”而青銅器專家馬承源則認為:“吳大澂所下的定義根據并不充分。‘玉鉞一詞文獻少見,但有‘玉戚一詞。戚(鏚)即鉞,也是斧柯之物,文字家謂戚是鉞屬而小,古代舞用‘朱干玉戚。文中所載的玉鉞都不甚大,柲(柄)飾又甚豪華,作舞蹈(專指巫舞)的道具也未嘗不可。用途未必局限于軍事權力,如表示先人在部落或氏族中的地位,如權杖一類的性質。”
考證“玉戚”真實用途有五:(1)非實戰儀禮武器。《尚書·顧命》:“一人執冕,立于東堂;一人執鉞,立于西堂。”在沒有金屬之前或金屬器未大量使用之前,起著主導作用或顯得更高一等,顯示玉德和鎮威而非實戰用的儀禮武器。(2)武舞用器。古人在獵獲大量食物,包括捕殺兇猛動物,獲得戰爭勝利及其他重要典儀時,都要行樂(跳舞)“文舞”、“武舞”。玉戚用作武舞之器,意在增加“威武”的重要儀式。(3)權力或財物的象征。(4)納貢或饋贈品。西周宣王時虢季子白盤銘文“贈用鉞”;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1件玉戈,上書六字銘文“盧方皙人戈五”,意即方國上貢給殷王朝的禮物。(5)祭祀和陪葬品。四川廣漢三星堆一號祭祀壇中出土的數件玉戚,其用途是最直接例證。(圖7)每每發現古墓中的玉戚皆放在逝者身旁,無疑是其下屬、親人奉獻給死者的珍貴陪葬品。
“玉戚”形制大致可分為長條弧刃式、寬扁體、梯形、斧鉞形、環璧形。戚鉞之別,在于刃部。戚刃內收成舌狀,鉞刃兩側外移。(圖8)夏代長條弧刃式玉戚:牙黃泛灰色,一面器表似乎曾用硃砂繪有某種圖案,局部還有編織物的沁痕。戚身修長,兩側邊琢對稱各六個戚齒,有二圓穿,上一圓穿應是月穿較大,是玉鉞向玉戚過渡的標本器。“戚(鏚)”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玉戚”的兩邊裝飾有“扉棱”,扉棱的“齒”代表“系列”,即一個“齒”代表一個兄弟氏族。“扉棱”是玉戚的重點特征,也是分期斷代的依據之一。觀察圖3神人側面紋玉戚,可以發現“扉棱”與神人側面紋有一定的延續關系,“扉棱”的出現與神人側面紋的關系可能相當密切。“扉棱”由齒頂、齒谷、分隔槽組成。早期的扉棱為平頂、平谷、平槽、直壁,橫豎間以直角;其中齒谷逐漸演化為橫C字形,再演化到斜C字形,分隔槽則由ㄩ字形演化到U字形,再到V字形;V字形則由深逐漸趨淺。(圖9)夏代二里頭環璧形(璧斧合一)玉戚:為青玉,器身扁平,中有大圓孔,兩側有扉牙,刃部較平直,刃寬9.6厘米。“環璧形玉戚”一般弧背、中孔較大,似乎都是由環形及凸領環形玉器改制而成。戚刃有平刃、圓刃、弧刃、多尖內收刃,刃部一般為雙面磨制而成。可見新石器晚期、商早期古人對禮器的設計已運用了復合體觀念,二里頭文化流行玉戚的合體,突出體現了玉禮器將形式美與象征意義巧妙結合的特點,復合體的運用在商晚期“婦好”墓中出現2件 “璧斧合一”玉戚(圖10—1、10—2);“斧鉞合一”玉戚8件(圖10—3、4、5、6、7)。
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兵器·鏚》:“鉞、鏚是同一類兵器,然而有大小的區別。”青銅鑄造的“鏚”,在二里頭文化期及商早期出土有:長條弧刃式、長條厚本式、曲邊大孔弧刃式銎;商晚期出土有:直邊弧刃式、不等邊弧刃式、短銎式;西周早期出土有:曲邊多曲刃式、刺內有闌式,可作為旁證。
親族制度,是國家制度連鎖中國文明的路向。“親戚”是連用結構緊密的詞語,孔穎達《禮記·曲禮上》疏:“親指族內,戚言族外。”親指父、戚指母。《呂氏春秋·論人》:“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高誘注:“戚,親也。”“戚”由大小系列的斧子引申義:掌握軍權的同胞兄弟。再引申義:戰時并肩作戰的兄弟氏族、胞族。段玉裁《說文》注:“戚,又引申訓憂,度古只有戚,后乃別制‘慽、‘慼字。”(圖11)河南偃師縣二里頭出土夏代梯形玉戚:高11.2厘米,刃寬6.7厘米,孔徑0.7厘米。青玉,有黃褐色沁。器呈長方梯形,上端正中鉆一圓孔。戚兩側上部有對稱齒棱,兩側下部內凹成弧形。弧形刃,雙面磨制。器型規整,無使用痕跡。
親族制度與國家制度連鎖形成“家國同構”的城邦,又稱“酋邦”,是人類社會由部落向酋邦發展為國家的重要階段。古代部落或氏族既是血緣組織,也是軍事組織。一對夫妻生育的多個兒子長大后,各自分家形成了自己的氏族。各個兄弟建立的氏族稱為兄弟氏族,氏族首長又兼任軍事首長,其軍權以斧鉞體現。大氏族的首領用大號斧鉞,中等規模氏族的首領用中號斧鉞,小氏族的首領用小號斧鉞。各個兄弟氏族的斧鉞其質地、樣式、規格基本相同,而同一個氏族系列的斧鉞統稱為“戚”,按照尺寸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依次排列的戰斧系列。“這也許就是玉戚與玉鉞名詞不同的緣由!”
夏商、周早期精工制作的“玉戚”,已失去了原有的實用功能,作為禮儀器在西周時期用于舞,以頌揚周武王伐紂之功德。(圖12)商代長方體玉戚:長(中軸)13厘米,寬8.5厘米,厚0.6厘米。全器黃色玉質,局部帶有綠色及褐色斑,質地溫潤。器身作略不對稱梯形,近背端鉆有一孔,平背,平刃,兩側各刻飾五個牙飾。商代“玉戚”沿襲了夏代的形制,或長方或弧圓,器體兩側均飾有齒狀扉棱,有的器面還出現了獸面紋裝飾。西周玉戚形制與商代后期的同類器物別無二致,(圖13)西周虢國虢季墓M2001出土環璧形(璧斧合一)玉戚:長14.4厘米,寬13.3厘米,厚0.8厘米。青玉質。體呈扁圓狀。前端略窄,刃端闊而呈弧形,兩側邊有脊牙各六個裝飾,中部有一圓穿孔,背面上留有一道切割痕跡。
“玉戚”是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的產物,始創期在陜西神木石峁遺址出土(28件)和墓葬確系的龍山晚期文化(圖14),盛行期在夏或早商,所有者絕大部分是奴隸主貴族或部落首領。它消失期在殷商,而石制品或邊遠地區的玉戚的使用似延續至西周乃至戰國。(圖15)陜西省西安張家坡出土西周斧鉞形玉戚:高9.9厘米,刃寬9厘米,厚0.4厘米。呈白褐色,上有朱砂痕,不透明。通體磨光,大致呈長梯形,上窄下寬,近頂端正中有一小圓孔,左側有一較大圓孔,系單面鉆,上嵌綠松石,兩側琢出齒牙狀扉稜,對稱分布,弧形刃,兩頭翹成尖狀,系由兩面磨成,刃部較為鋒利。嵌綠松石工藝最早見于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獸面形玉冠飾,眼用綠松石嵌成;夏代青玉半月形器圓孔內鑲有圓形綠松石、二里頭出土的獸面紋銅牌飾嵌有綠松石;商代婦好墓出土青玉援銅內戈也鑲有綠松石;此器佐證周代玉雕繼承了松石鑲嵌工藝。玉戚的傳播路線,從先后不同年代物和地點情況看,是從黃河中上游始創后,由陜甘向四川、云南再往越南傳播;另一路線從陜甘向黃河下游的山東、江浙、福建傳播;最后又于廣東一帶,從時間先后看黃河流域最早,后期傳播延續向南發展時間相對較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