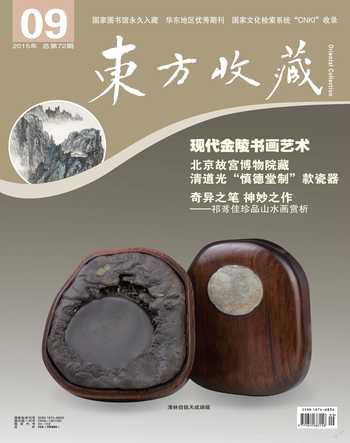湖州近代古錢大藏家潘瀾江考
劉健平
現已百歲的全國著名泉學家陳達農老先生再三提到抗日戰爭勝利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居于湖州地區,集幣好的藏家主要有潘瀾江、鄭德涵、陳達農三人。時稱潘以多勝,鄭以精勝,陳以奇勝,可成三足鼎立之勢。陳達農先生,性格外向,為人豪爽,對收藏方面毫不保守,且平易近人。喜和眾藏友交流心得,樂于向志同道合的同好展示藏品。收藏面前不分老小皆融洽。并且時常指點提攜后學。在實踐之余又著書立說,所以終成一代泉學宗師,被稱為泉界的常青樹、活化石,名聲享譽國內外!而鄭德涵先生,是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的晚生。學問極深,書畫琴棋無所不精,尤精金文、甲骨文。曾應邀參加《辭海》編纂工作。和諸多近代大師有師友之誼,而且是20世紀40年代中國錢幣學社社員,泉學方面蔣伯塤是其恩師。故上海師大、中國美院(浙江美院)等極賞識,多次邀請前往教授古文詩詞。然由于湖州安吉當地教育局再三誠懇地挽留和他一貫淡泊的心志,故沒有成行。隱于安吉三中平凡崗位任教一生,桃李滿園。夫人錢重引亦工繪畫音律,伴鄭一生,琴瑟之合也。由于鄭一生勤于教學,收藏為業余之玩,加之淡泊名利,謙虛謹慎的作風,所以從不輕易示人藏品,知之藏者甚少也。連同邑居之陳達農老先生也沒有寓目到其秘藏。潘瀾江先生,更是忙于醫學,用傳承祖傳之中醫濟世救人,外界只知是湖州名醫也。收藏是其自娛自樂的業余愛好,更由于性格內向關系,從不輕易展示給人看,更不喜和人多交流。故潘氏生前只有他的忘年之友陳達農先生有幸目睹他收藏之大半也,而所知潘氏藏事者甚少。而潘、鄭兩位現為藏界知曉大名,也是陳達農先生多年宣揚湖州近代泉藏家“潘、鄭、陳”三足鼎立藏績的結果。
世代名醫潘氏家族
江南太湖流域,由于濕熱偏盛,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歷來民眾又喜食肥甘,故疔瘡、瘍癥患者極多。正如《內經》所說:“膏粱之體、足生大丁”。而潘氏中醫外科正是治療這方面的佼佼者。
潘氏中醫的傳承,由于史料散失。從潘斌璋先生稿,據上海市衛生局、浙江省衛生廳調查,只能推到十代。而且據研究潘氏家族乾隆時有做過御醫,潘家所以可稱為世代中醫之家族。而浙江湖州市德清縣鐘管鎮曲溪灣村,更是現在史料可查的潘氏家族清中期后“曲溪灣潘氏中醫外科學術流派”的發源地。曲溪灣村現在還留存有潘氏家族清末中式建筑的幾間老屋和一幢民國時期的西式洋樓。而潘氏后人保存的資料中,只能推算到清乾隆年間居湖州德清縣鐘管鎮曲溪彎村的潘鼎。而潘鼎以上祖輩的情況就成為了一個研究課題。由于時間久遠,潘鼎生卒年月也無從考證。但他應用炒、灸、煅、焙、制、煨、提、風、飛、爛、霜等多種手法,祖上家傳的醫學和長期的實踐而自成一家的精到醫術卻揚名江南。在道光年間,潘鼎之子潘旭,字東陽,得真傳,是為此流派第二代傳人之代表。其以薄貼和散劑見長,又鉆研內科,達到內外兼治的妙手,尤擅治熱病。其子吉甫、申甫,是為第三代傳人之代表。吉甫號“稻香書屋主人”,以研究外科理論為主,尤重教育,有門生上百人。編撰有醫學許多啟蒙之讀物,用實踐加理論奠定了潘氏流派的理論基礎。申甫勤攻讀,中秀才,后隨父潘旭學醫。曾和兄吉甫,門生張彥英、王彤軒、吳譜農等一起成立了“曲溪國醫學研究會”,分析疑難雜癥,編寫醫學書籍。一代國學大師俞樾經申甫診治痊愈后贈予“術精祝括”的金子大匾。民國時期,申甫還治愈了駐滬法國總領事的頑癥,法國總領事為了感謝,出資并親自為其設計,在曲溪灣建造了一座西式洋樓,至今屹立。其弟子達上百人!其后又家傳至潘青時、潘青泉、潘蓮舫等,是為第四代傳人。皆有名聲、醫案等傳世江南。
醫術高超的低調大藏家潘瀾江
潘瀾江(1896—1963),湖州人,祖父是潘吉甫,父潘蓮舫,于清朝光緒年間從祖居德清曲溪灣遷居湖州紅門館前姜家房屋開診所。子女中潘瀾江排行老三,潘春林排行老四。潘春林后隨父學醫一年后,父逝世,則由兄潘瀾江帶著繼續行醫。學成后,兩兄弟分而開設門診,后均為湖州名醫!其中潘瀾江,從事醫藥研究工作五十年,醫名甚著。抗戰前門診每日百余人次,并開設多期學習班,廣為傳播“潘氏中醫外科”,其學徒上百人。其精通外科,對疔疽、腸癰、流注等有獨特治療效果。曾有六尺余金箔匾八個懸于醫療大廳。這些是患者對其醫術高明的深度認可和贊揚。在祖傳外科用藥成方的基礎上,增添了二百多個藥方,均有詳細論述。曾有部分驗方介紹于《老中醫臨床經驗匯編》、《浙江中醫臨床經驗選輯·外科專輯》、《浙江中醫藥》等書。
潘瀾江先生,在江南地區留下的是赫赫有名杏林高手的盛名。妙手回春、救死扶傷的故事至今還能有所耳聞,但鮮有人知他的收藏,因為潘瀾江一生致力于救死扶傷,收藏只是他業余工作后的愛好。況且不張揚,內斂謙虛謹慎的性格,造就了他不公開、不炫耀、不示人的收藏作風。而且收藏品德收藏風格很好,心胸又極開闊,不和人爭比。盡在蒙頭游自樂中!所以,一代大藏家至逝世時,世間大都只知其醫道,而不知其藏道。所以現在記載潘氏的文史資料中,大多只能看到一個中醫外科名醫的風采。
幸而潘瀾江先生,認識了忘年之交陳達農老先生(今年一百歲還健在)。陳老在著作中多有提起,并加以稱贊。提起潘瀾江,陳老也是肅然起敬。雖然他們倆相差二十年,但他們之間的友誼很深,交往也是亦師亦友之態。所以陳老是有幸見過潘瀾江精藏大部分不多的人之一。而且現在是世上唯一健在見證潘氏大量精藏的證人,進而使得世人知道了潘氏之精藏的史實。
潘氏精藏在抗日戰爭時散失過一次,又在文革中散失過一次。后潘氏家人致信中央、地方各部門,請求歸還,并多次追討。后向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同志反映,由中央指示,成立專門調查組對此事調查,后落實政策,追回小部分。“潘氏藏品文革查抄散失事件”引起轟動,并由當時《湖州晚報》記者曹國民先生寫入內參。讓人從另一面知道了潘氏精藏之豐,水平之高。
另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余榴梁、徐淵、顧錦芳、張振才編著的《中國花錢》一書中收錄了潘瀾江先生舊藏的花錢大量精美拓片。這是其子潘斌璋從落實政策歸還的殘藏中拓片提供的。這已使藏界震驚不已。上世紀80年代初其子潘斌璋和陳達農共同在湖州市舉行了一次錢幣展。以普及錢幣知識為目的。
潘瀾江之子,潘斌璋(1929—2012),傳承了父親的醫學。是浙江著名的老中醫,名醫專家,其專心于醫學,以救死扶傷為己任,老老實實當好一個好醫生。對于家藏,由于文革當中受到查抄散失打擊,所以謹于示人。在醫學上他有建樹并著文不少,但收藏上著文不多,在陳達農先生幫助下只有《瀾江泉目》、《潘氏藏泉精選》等拓、錄完成。湖州錢幣學會曾想給潘瀾江出一本遺留舊藏的書,原則是用國際慣用之小組鑒定法,錢幣學會眼力好的錢藏家組成小組大家探討,對于不開門的予以放棄。但潘斌璋對此法不認同。另錢幣學會要拓片出書,由學會指定拓片高手幾十錢一組拿回拓好,再交換第二批再拓。而潘斌璋卻要在他家中拓片,不許實物離手。后因種種原因沒有達成意向,終而沒有出書。而陳達農先生心胸開闊,采用了錢幣學會提出的合理條件,出書得到了滿意的結果。潘斌璋先生由于家人后代不喜收藏,自己又受過散失打擊,所以雖喜歡古玩但矛盾心理中一直默默轉讓著藏品。但對同邑湖州人好像羞于交流,一般到他家很難見到藏品實物,只能看到拓片本。而有湖州藏家真誠提出高價求他轉讓,也很難如愿。(湖州只有他的一個泉藏好友凌某買到一些)。他雖然一面不喜交流,不輕易示藏品,不輕易出讓,也不參加湖州市錢幣學會的活動,但一生幾十年中卻慢慢將眾多潘瀾江舊藏散向了外地。古泉、玉器、雜件無所不包!外地藏家稱之為是一個“金礦”。然而潘斌璋不擅與人交流的性格在信息社會面前變得對于藏品價格行情成了“與世隔絕”的人。而潘氏生性直爽,輕視經濟利益,講朋友交情、講義氣的作風在當今復雜的古玩圈古玩售讓中是明顯占下風的。而且據說他售讓時總考慮到別人利益,不想讓買者吃虧。而且一旦確定買賣時,友情第一,性格爽快。而且他總盯著常來他家的幾個外地朋友售賣。其實是形成了藏價沒有對比性、競爭性,對賣者是不公正的。所以潘氏售出的藏價極其低廉,有的甚至被層層轉手后,又被湖州藏家買回了湖州。潘斌璋在2012年逝世前后(1929—2012),外地市場上曾出現了許多孤品、珍品古泉和高檔古玉等,這是潘氏最后一批讓出藏泉、藏玉等古玩。當這些信息從四面八方反饋到湖州時,舊物已蕩然無存。留下的是藏界的震驚!更由于后輩的不懂!是收藏盲。在潘斌璋紀日,家人將潘瀾江、潘斌璋父子留存的珍貴拓片、信件、書籍等燒化不少。湖州高勇勇君有幸得到“陸心源藏泉由吳昌碩拓片”珍貴拓紙若干張,整理成了一冊書《歸安陸心源氏藏泉》,已是幸運之極!其實像潘瀾江這種級別的大藏家遺藏,完全可以在知名大拍賣行舉行的專場拍賣會公開拍賣!這也是收藏家們引以為戒的!
大藏家潘瀾江的藏品
湖州陳達農老先生,一代泉學家,稱潘瀾江“收藏之富,甲冠湖州”。“潘瀾江,本城第一泉藏家。”“上乘品數不勝數”。“先生藏泉貪而不妒、富而不嬌,對農則誨而不倦,誠而不詐。藏泉甲菰城而僅與知己者共享,未著錄。以不出遠門,忙于治病,而擁有豐貨,養晦僻地未得顯聞,惜哉!”而從陳達農、潘斌璋等回憶看,潘瀾江精于醫道,而所得資金大部分用于收藏。且酷嗜古玉、古泉,另帶青銅、雜件、書畫等的收藏。收集活動貫其一生不止,有半世之久。古泉儲有正規品種五千以上(不含細版別)。另復品細目則以袋貯、斤稱,有十數擔之多。光康熙套子錢完整一套者,就多達數十副之巨。古錢中珍稀品更是層出不窮。而儲玉竟達二缸之巨。你想古泉以擔算,玉以缸儲是何種收藏氣派!惜日軍侵華,湖州淪陷,避難于楂樹塢,被土匪搶劫一空,損失慘重。后來繼續收集古泉、玉器及其他藏品,重振旗鼓。而于1963年10月3日逝世時,傳下精美鼻煙瓶七十只,古玉一壇,古泉正品近五千種(不含細版別),清代錢樹一株(后分割),書畫、銅器、雜件等,而且有一套湖州清代收藏家陸心源舊藏之甲骨文(共四盒),甚為國寶,全國流傳有續者只有二套。……。不幸“文革”浩劫,全部藏品抄家散失!后落實政策,劫后只追回部分古泉等藏品。據潘氏后人記錄,按當時物價,損失就在幾千萬元。
我們現在從潘瀾江先生辭世二年后,其子潘斌璋和陳達農先生共同整理并拓圖的《潘氏藏泉精選》、《瀾江泉目》中可以看到其精藏之管豹。古泉藏有咸豐寶福一十(漢文)鎏金扶比八千,穆青銅寶大錢,銀質太平元寶篆書折二右旋讀背星月。小平大樣建炎元寶篆書寶字短冠,洪武通寶篆書折三背上月下星,天啟闊緣背上京左右十一兩大錢等等。
潘瀾江嗜泉一生,孤品、珍品極多。然譽滿泉界的藏品是大足通寶折十大錢。民國時,潘瀾江先生曾赴鄉間為其先人勘察墓地,值杭長路正興工建設,在湖州西門外楊家埠附近地段見到筑路工人正好在群集圍觀剛掘到的一枚大型古泉。潘先生忙上前說服,終以當時現錢給予一番而易得。此即名震泉林之“大足通寶”孤品也。時潘先生造詣未深,不解其珍貴也。而戴葆湘嗅覺靈敏,眼力犀利,又善于和人交流,足跡遍布全國,眼線放滿諸城,熟識天下泉藏界。雖極嗜錢,但為了生活,主要是為富有的藏家供貨、牽線,經營錢幣,是其兄戴葆庭泉幣事業上的好幫手,且跑到極品泉幣大都讓兄戴葆庭先審閱定奪。潘、戴由于皆嗜泉,故在湖州古玩眼線的引見下慢慢熟識。戴葆湘這時且巧又來湖,潘氏即拿剛得之“大足通寶折十大錢”示以戴氏。戴葆湘見之,極為震撼,手拓片后馬上回去報于其兄戴葆庭。戴葆湘、戴葆庭商議后決定用款盡力購之。戴葆湘開誠放言:“這枚幣我和家兄都很喜歡,潘先生你要多少銀元只管說!”潘瀾江笑對:“我看醫治病,得以銀鈔足以生活。而且我又不貪愛錢財,得銀元多有何用?!獨喜集古泉樂也!不賣!”戴葆湘無計可施,又回報其兄戴葆庭。戴葆庭和戴葆湘二兄弟經商量決定,既然潘先生巨金不賣,那其喜歡古泉,就以古泉易之吧!這樣戴葆湘往返數趟。潘瀾江為戴氏兄弟的真誠所打動,又為易泉之豐厚條件所感動。后同意戴氏請求,以一百枚珍稀古錢易換大足通寶錢。這一百枚錢中以靖康元寶篆隸折二對錢打底。其大足通寶折十大錢后歸大藏家戴葆庭收藏。而戴葆庭更取自己的齋號為“足齋”,可見此錢在戴氏心中的地位。此品可以和張叔馴的“齊齋”大齊通寶相抗衡。大足為武則天稱帝建立大周時的年號之一,極其珍貴。一般泉界看到的偽居多,罕有真品,此為孤品,至今沒有發現第二枚。而今大齊通寶卻已現世多枚矣!后戴葆庭贈予潘瀾江《足齋泉拓》三卷,以示感謝!集戴氏一生得泉之精品大珍,然《足齋泉拓》中雖名“足齋”卻未將所得“大足通寶”泉拓收錄。所以留下一個古泉史上的謎!而據潘瀾江兒子潘斌璋生前說,其父生前也問過戴葆湘關于“大足”。是戴葆湘親口說的“大足”下落。其兄戴葆庭得大足通寶折十大錢后,極為高興,命名為“足齋”。這引起泉界有力者的羨慕。不久,有富有泉藏者許以天價重金求讓,并加上朋友感情牌請求得之!戴氏后終為所動。但購買的藏家提出以下條件:1.對于“大足通寶”的買家要保密。2.“大足通寶”拓片不能留世傳于天下為條件,請求戴氏兄弟不能留下任何關于“大足通寶”的拓片及資料。戴葆庭、戴葆湘兄弟不但眼力好,而且是泉界信譽極高的人,終守諾言沒留下“大足通寶”錢拓資料于后世。而湖州潘瀾江先生收藏大足通寶后沒有更深去想,平常更不熱衷于拓片,而且“大足通寶”得到不久迅即易之!所以手中竟然也沒有拓片留存。關于此,戴葆湘來湖時順便問過潘瀾江,有否存有大足通寶拓片,潘氏說“沒有”時,戴氏笑而長嘆:“那世間目前就看不到大足通寶的拓圖了!”而據說,購此泉的藏家于民國末期飛離中國,去海外了。珍泉現在不知所蹤。“大足通寶”泉界期待終一天能夠亮劍人間!
潘瀾江集藏一生,尤喜古泉、古玉。然忙于醫學,古玩終無所著述。由于集泉極豐,難免有偽錢購進。然其慢慢研究就會發現其偽,可見功力也非同一般。由于概率的關系,買的古泉如山,偽錢也慢慢積成堆。而且有時故意買進偽錢以研究,并自己幽默打趣是“偽錢大王”。生前曾想請陳達農先生幫助整理,著一本《偽鑄泉譜》以警示后學者。然陳氏后受波政治運動,潘氏又中途病逝。文革中藏品又大量散失,終沒有成書。實為憾事!陳達農先生后補有《“偽鑄泉譜”序》《偽鑄古錢過目錄》兩篇文章。然陳達農和潘斌璋在潘瀾江逝世二年后,整理刊出《瀾江泉目》、《潘氏藏泉精選》留世,也讓我們有幸目睹一代大藏家藏泉片麟之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