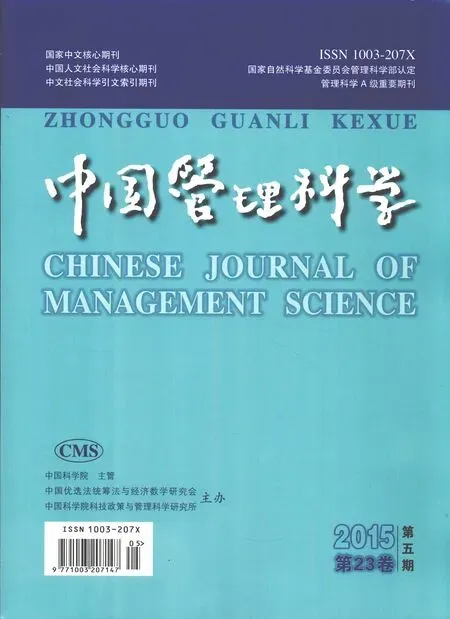組內競爭與組間競爭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差異
——基于移動壁壘分隔作用的研究
段 霄,金占明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84)
?
組內競爭與組間競爭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差異
——基于移動壁壘分隔作用的研究
段 霄,金占明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84)
本文基于戰略群組理論,通過實證研究探索了組內競爭、組間競爭對移動壁壘內外部企業具有的不同影響。以中國制藥業上市公司為樣本,采用階層聚類分析中的Ward法進行戰略群組劃分,識別行業中的移動壁壘并將其保護功能作為調節變量,然后分別使用POLS和RE回歸模型對兩類競爭的效果進行了分析檢驗。研究發現,組內競爭對于移動壁壘外部企業績效的不利影響顯著大于其對壁壘內部企業的影響;相反,組間競爭對移動壁壘內部企業績效的不利影響顯著大于其對壁壘外部企業的影響。上述發現表明,行業中不同類型競爭的效果存在顯著差異,而企業相對于移動壁壘的位置是造成上述差異的重要原因。對競爭效果的準確分析需把握以下兩方面因素:行業中有哪些移動壁壘,以及競爭發生在組內還是組間。
戰略群組;移動壁壘;組內競爭;組間競爭;企業績效
1 引言
企業間競爭幾乎在所有行業中普遍存在,也是管理學研究的重要主題。以往研究已經揭示,較高的競爭強度不利于企業績效。在競爭激烈的完全競爭市場中,企業長期來看將獲得零經濟利潤。而能夠削弱競爭程度的壟斷力量則可能使企業獲取超額利潤。例如,集中度較高的行業一般整體盈利水平也較高[1]。Porter[2]的行業五種力量模型也表明,激烈的行業內部競爭對行業整體利潤率不利。這是因為激烈競爭使各企業的產品價格受到沖擊,且需要付出更多精力與成本應對企業間的對抗。而差異化戰略能一定程度上降低產品的相似性從而減弱競爭,有利于提高盈利[2]。Cool和Dierickx[3]也發現行業的整體盈利水平與該行業的競爭激烈程度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盡管行業內競爭對企業績效的負面影響已獲得共識,但以往研究始終未能揭示的一個問題是,企業之間的競爭在效果上是同質還是異質性的?如果競爭是同質的,企業只需關注總的競爭程度即可,與誰競爭并不重要。反之,如果不同類型的競爭效果有差異,企業就必須關注如何與不同類型對手展開競爭的策略問題。這也是本文所關注的問題。
少量研究文獻與上述問題有一定關聯性。例如,Peteraf[4]發現不同群組的企業應對競爭的方式有差異。Chen和Hambrick[5]發現企業規模對其競爭行動及響應的程度、速度等方面具有影響。Caves和Porter[6]認為競爭者之間對互相依賴的認知會影響競爭激烈程度進而影響企業績效。但這些文獻未對不同類型競爭的效果差異開展系統性研究。
研究上述問題的困難在于如何系統地對不同類型的競爭進行區分。如果把行業內的企業看作幾乎同質的個體,就無法把握不同性質競爭的區別。然而,把行業中每個企業都看作獨特的個體又過于繁瑣,也不符合管理者在實踐中把同類競爭者進行分類的思考習慣[7]。戰略群組(Strategic Group)理論恰好有助于解決這個問題。戰略群組是行業中由一些實施著相似競爭戰略的企業組成的企業群[2]。同一群組內的企業在經營范圍與資源運用等方面非常相似[8],對環境變化的反應模式也相似[9];而不同群組之間則差異明顯。戰略群組之間在績效上也存在顯著差異。Mascarenhas和Aaker[10],Fiegenbaum和Thomas[11],Nair和Kotha[12],孫先定等[13],倪文斌等[14],楊鑫和金占明[15]都在不同行業中都發現了這種績效差異。劃分戰略群組可以把行業中的眾多企業按照關鍵差異進行分類,企業間的競爭也就可以系統地分為戰略群組內部的競爭以及處于不同群組的企業之間的競爭。本文將深入探索這兩類競爭對企業績效的不同影響。
在此基礎上,本文將創新性地采用移動壁壘的獨特視角對行業內競爭進行分析。移動壁壘(Mobility Barrier)是阻礙企業改變戰略模式而從一個群組轉移至另一個群組的力量[2,6]。企業跨越移動壁壘移動需要付出特定的成本[16]。由于移動壁壘的存在,戰略群組不是自由進出的偶然組合,而是具有穩定性的企業群體[17]。行業內通常存在多種移動壁壘。例如,產品或服務的范圍是一種移動壁壘[16],縱向一體化程度[6]和企業掌握的技術[12]在一些行業中也是重要的移動壁壘。
移動壁壘有助于識別不同企業的競爭地位[18]。在行業中,移動壁壘的高度具有相對意義。例如,美國制藥業中最有優勢的群組相對其它群組的壁壘“高度差”不同[19]。移動壁壘相對高度最低的群組在行業中處于缺乏保護的地位。在其它戰略群組看來,這個群組不具備移動壁壘的保護。由于進入的阻礙最小,這個群組一般具有最多的企業數量。除了少數的并購情形之外,行業外的進入者都會進入最缺乏保護的那個群組[6]。郭朝陽[18]也指出,行業外部企業進入本行業最缺乏保護的那個群組并不難。可見,行業中往往存在著處于某種移動壁壘保護下的各具優勢的企業和缺少任何壁壘保護的大量普通企業。故此,本文將基于移動壁壘的分隔作用,研究行業中的組內與組間競爭差異。研究結論將對戰略群組理論的完善做出貢獻,并揭示移動壁壘所具有的尚未得到關注的功能,對競爭環境的分析和競爭對手的選擇等企業管理實踐活動也將帶來重要啟示。
2 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2.1 移動壁壘的分隔作用
移動壁壘分隔下的行業內競爭如圖1所示。為便于理解,圖中只考慮一種移動壁壘,豎直的虛線表示移動壁壘,其兩側各有一個戰略群組,空心點代表一個企業。同一群組內企業之間的競爭是組內競爭;不同群組成員的競爭稱為組間競爭,競爭雙方跨越移動壁壘,處于不同的地位。

圖1 移動壁壘分隔下的行業內競爭
移動壁壘的隔離作用具有不對稱性。移動壁壘通常是單向地阻礙一側的企業移動至另一側,如規模較小的企業難以進入大規模企業組成的群組,但反方向的移動則容易得多。當然,一般不會有企業愿意進行這種不利的反向移動。不對稱隔離作用使移動壁壘兩側的企業處于不對等的競爭地位。移動壁壘對于劣勢一側的群組(外側)中的企業具有阻礙作用;而對優勢一側的群組(內側)中的企業則具有保護作用。行業中缺少移動壁壘保護的戰略群組最容易受到模仿和損害[9]。
移動壁壘保護下的企業容易獲取高績效的原因包括:(1)移動壁壘能保護企業較少受到行業中其它群組的競爭影響[9],降低了競爭強度。(2)由于僅有很少企業可成功實現群組轉移,處于移動壁壘保護下的企業通常在數量上少于移動壁壘外的普通企業,在群組內面對著較少的競爭者。(3)行業外的企業在進入某行業時一般會選擇難度較低的戰略群組作為目標[6],移動壁壘保護下的群組因較難進入而很大程度上免受行業外進入者的影響。(4)移動壁壘內部的企業通常在物質資源、技術與經驗上處于優勢,普通企業難以模仿壁壘內部企業的戰略[10],因而移動壁壘保護下的企業更容易爭奪到該行業中高盈利或具有潛力的細分市場。
2.2 組內競爭的效果差異
在參與組內競爭時,移動壁壘內、外部的企業面臨著不同的情況。移動壁壘外部的企業通常是行業中最普通的、缺乏優勢的競爭者,且數量眾多,因而難以互相溝通和協調[6]。較低的制造工藝和技術水平使它們傾向于采用價格戰等簡單競爭方式。由于缺乏壁壘的保護,行業外的進入者容易瞄準這個群組[6,9]。這些企業在參與當前激烈競爭的同時還面臨潛在進入者的威脅。資源上的弱勢使它們主要在盈利較低的細分市場中競爭。所以,激烈的組內競爭對移動壁壘外部的企業績效具有強大的負面影響。
對于移動壁壘內部的企業,不僅本群組內的企業數量較少,而且較少受到行業外潛在進入者的威脅,群組內的競爭者比較穩定,容易產生長期的互相了解。處于移動壁壘內部的戰略群組通常在某個或某些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如技術、規模、企業所有者的身份等,基于這些獨特優勢且高度相似的戰略群組成員之間容易感覺到彼此的互相依賴關系[6],易于互相理解從而進行有利于雙方的溝通與協作[4],降低競爭強度。可見,移動壁壘內部的企業參與組內競爭時,受到的不利影響應比移動壁壘外部的企業受到的影響小。根據以上分析提出假設1:
假設1:組內競爭對移動壁壘外部企業的不利影響顯著大于其對移動壁壘內部企業的不利影響。
2.3 組間競爭的效果差異
位于移動壁壘內部的企業參與組間競爭時,它們和競爭者分屬不同的戰略群組,實施的戰略有很大差異,難以互相溝通和協調。移動壁壘內部的企業可能需要參與自己不熟悉的價格戰等競爭方式,對抗程度比組內競爭更高。而且,移動壁壘外部的競爭者數量眾多且容易互相模仿,也不利于企業與之協調而降低對抗。此外,壁壘外的競爭對手通常在知識、技術等方面處于較低水平,移動壁壘內部的企業在與這類企業競爭時可獲取的有價值的經驗較少。可見,移動壁壘內部的企業參與組間競爭時受到的不利影響較大。
移動壁壘外的企業在參與組間競爭時也面臨著難以溝通和協調的問題,但移動壁壘外的企業更習慣簡單而激烈的競爭方式,這與它們面對的組內競爭模式比較相似。它們一般在產品與技術上不具優勢,面對組間競爭時仍使用低成本的競爭策略,不需要進行專門調整。同時,移動壁壘外的企業參與組間競爭時面對的是在產品、技術、管理等方面具有高水平的競爭者,可在競爭過程中獲取組內競爭難以接觸到的知識與經驗。企業還可能通過與有名望的實力強的對手競爭來增強自己的聲譽。所以,移動壁壘外部的企業參與組間競爭時受到的不利影響相對較小。根據上述分析提出假設2:
假設2:組間競爭對移動壁壘內部企業的不利影響顯著大于其對移動壁壘外部企業的不利影響。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與群組劃分
本文以2010與2011年中國制藥業上市公司為目標樣本,除去被標注ST或*ST的公司8個以及數據嚴重不全的公司21個,適合本研究采用的共計91家上市公司,共獲得182個樣本觀測值。財務方面的數據主要來自CSMAR和RESSET等國內數據庫,經營方面的數據由作者從公司年報中收集。專利數據查于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藥品化學分類和治療領域查于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網站及《中國藥典》。由于國內尚無制藥行業的戰略群組研究可供參考,劃分群組的戰略變量及其衡量方法主要參考了國外制藥業的戰略群組研究文獻[8][20]。各戰略變量的含義和衡量方法如表1所示。
企業規模用其銷售收入的自然對數計算[8,9,21-22]。將各公司銷售額最大的3種藥品作為該公司的主導藥品進行戰略變量的計算。本文樣本下各戰略變量之間相關性普遍較弱,基本在0.3以下,可直接聚類分析。聚類方法采用階層聚類法中的離差平方和(Ward)法,此方法在戰略群組研究中應用最廣[3,11-12,21,23]。各戰略變量都事先進行了標準化以保證變量間的可比性[8]。

表1 劃分戰略群組的戰略變量
由于時間跨度不大,聚類時各變量取企業在兩年內的均值。借助SAS的cluster過程進行聚類分析,綜合考慮R2,ΔR2,Pseudo-t2等指標,得到4個戰略群組。通過對每年的數據聚類進行對比,可發現這4個群組的主要成員未發生變化,群組結構穩定。國外制藥業中的群組數量通常在3至6個[21],與本文劃分結果一致。
3.2 移動壁壘的確定
通過各群組的戰略變量均值可對移動壁壘進行識別。戰略群組1的研發投入強度是各群組中最高的,其典型成員企業是高度注重研發、生物生化藥品居多的公司。研發能力可能是進入該群組的移動壁壘。戰略群組2的產品集中度最高,典型成員企業是產品集中、國外銷售比例很大的中型化學藥公司。高度集中的競爭戰略使此群組的企業具有較高的專業性,最高的國外銷售比例可能表明其產品質量較高,這些應是該群組的進入壁壘。戰略群組3的成員企業規模、產品線寬度均最高,其典型成員是產品范圍廣的大型公司。企業規模和產品線寬度可能是進入該群組的移動壁壘。戰略群組4的銷售費用和OTC藥物數量最高,傾向于提供科技含量相對較低的OTC藥物,且不得不增大銷售投入。其成員企業數量眾多,沒有突出優勢。行業的新進入者很可能瞄準這一缺少保護的戰略群組。
可見,前三個戰略群組各有優勢,均得到某種移動壁壘的保護。而戰略群組4的進入門檻最低。從凈資產收益率看,前三個群組的平均值是14.67%,群組4是12.26%,且Mann-Whitney檢驗在P<0.01水平拒絕了兩者相等的原假設。根據以上分析,本文認為戰略群組4缺乏壁壘保護,而前三個群組處在各自的移動壁壘保護之內。
3.3 變量設計
(1)因變量
企業績效。選擇銷售凈利率(ROS)、凈資產收益率(ROE)和總資產凈利率(ROA)作為企業績效指標。ROS在戰略群組領域的研究中得到了不少應用[3,8],而ROE和ROA則更為廣泛地用于企業研究中。三個指標分別進行回歸檢驗,若能取得一致的結果,可說明研究結論更穩健。
(2)自變量
① 組內競爭(RIVW)。
② 組間競爭(RIVB)。
制藥業的特點非常符合本研究的需要。藥品是一種比較特殊的產品,它包含較多的專門知識,消費需求的個性化程度低。多數消費者不具備專業的藥品屬性知識,醫生或藥師在很大程度上代理了消費決策。根據規定,處方藥不可在大眾媒體上做廣告。在促銷方面,由于需要定量服用,企業無法建議消費者增加消費量,或者進行買一送一等促銷。藥品的外觀、花色、包裝、商品名稱都不具有重大作用,關鍵屬性是治療疾病的類別和效果。以上特點共同決定了制藥企業之間產生競爭關系的前提是它們的藥品具有相同的治療類別,治療類別不同的藥品之間沒有任何替代性。國外制藥業的戰略群組文獻也是基于藥品治療類別來衡量競爭[3,8,20-21]。
以企業之間具有同樣治療領域的藥品數量來衡量競爭。設置二分類變量Dij,當企業i與企業j(i≠j)屬于同一戰略群組時,Dij=1,屬于不同群組時Dij=0。若行業內共有n個企業,企業i與企業j間的競爭為RIVij,則企業i面對的總的組內競爭為:
企業i面對的總的組間競爭為:
以上衡量方法符合企業間競爭的不對稱性。即企業間競爭RIVij對于競爭雙方的企業雖是同一數值,但是每個企業的面對的總的競爭程度不同,所以RIVij對于兩家企業的相對重要性不同。
(3)調節變量
移動壁壘的保護。MB是二分類變量,如果企業所在的群組處于移動壁壘的保護中,MB=1;如果企業缺乏移動壁壘的保護,則MB=0。
(4)控制變量
① 年度時期。Year2011取值為1表明是2011年的數據,取值為0表示是2010年數據。
② 控制人類型。最終控制人是國資委等機構時Ctrl取值為1;是個人時Ctrl取值為0。
③ 股權集中度。OwnCon表示公司前十大股東掌握的股權比例。
④ 資產負債率。DAR表示企業的負債與總資產之比。
⑤ 流動比率。CR表示企業的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
⑥ 庫存周轉率。ITO表示企業該年度內的庫存周轉率,以次數為單位。
⑦ 應收賬款周轉率。ARTO表示企業的應收賬款周轉率,以次數為單位。
⑧ 非流動資產比率。NCAP是企業的非流動資產占所有資產的比,表明企業的資產屬性。
3.4 回歸模型的確定
本研究的樣本數據是同一批企業的兩年期數據,忽視企業的個體效應可能帶來偏誤。由于自變量RIVW和RIVB在樣本期都未隨時間變化,且MB是虛擬變量,因此不能用差分處理或固定效應模型回歸。本文使用隨機效應模型(RE)和混合OLS兩種方法回歸,并將回歸結果進行對照。由于對于每個企業來說組內競爭和組間競爭必然同時存在,不論作為自變量或與調節變量MB的交互項,兩種競爭RIVW和RIVB都同時加入模型而不是分別考慮。此外,為了增強統計推斷的穩健性,所有系數都采用對應的集群穩健(Clustered Robust)標準誤。
4 研究結果
4.1 描述統計與分析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系數如表2所示。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回歸與混合OLS回歸的結果分別列在表3和表4中。從表2中可以看到,自變量RIVW和RIVB與各控制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普遍較弱,多在0.2以下。自變量與調節變量存在一定程度的相關性,這或許表明MB不是純調節變量,而也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表2中還可以看到,RIVW和RIVB與企業績效的三個指標ROS、ROE和ROA基本都是負相關關系。Cool和Dierickx[3]對美國制藥行業戰略群組研究中所得到的回歸系數也是負數,本文與之一致。但本文中自變量與企業績效的負相關性不算很高;這或許表明,如果對行業中的所有企業不加區分而從整體上進行回歸,競爭程度不會具有特別顯著的不利影響。兩類競爭的具體效果需結合回歸結果進行分析。
4.2 模型結果與討論
表3所示是采用RE模型時在ROS,ROE和ROA三個因變量指標下的回歸結果。對于組內競爭(RIVW),在模型二、四、六中交互項MB×RIVW的系數都為正(0.0790,0.0540,0.0329),分別在P<0.05,P<0.1和P<0.05水平顯著,取得了一致的結果。這表明組內競爭對于處于移動壁壘內部(MB=1)企業的不利影響顯著地小于其對移動壁壘外部(MB=0)企業的不利影響。假設1得到了有力支持。對于組間競爭(RIVB),在模型二、四、六中交互項MB×RIVB的系數都為負(-0.1371,-0.0713,-0.0495),且分別在P<0.05,P<0.05和P<0.01水平顯著,三個因變量指標下回歸檢驗的結果一致。這表明組間競爭對于處于移動壁壘內部(MB=1)企業的不利影響顯著地高于其對移動壁壘外部(MB=0)企業的不利影響。假設2也得到了支持。而且,模型二、四、六相應比模型一、三、五的Wald chi2顯著提高(均在P<0.01水平),表明加入移動壁壘與組內、組間競爭的交互項后,模型對績效的解釋能力得到了顯著提升。以上結果共同表明,處于不同競爭地位中的企業參與組內競爭或組間競爭的效果具有顯著差異。

表2 變量的描述統計及相關性(obs=182)

表3 競爭效果差異的RE回歸結果
注:1.系數下方括號中的數字為對應的clustered robust標準誤;
2.Δ Wald chi2數值都是與前一模型的比較;
3. 顯著性水平:***p<0.01;**p<0.05;*p<0.1。
表4所示是混合OLS模型在三個因變量指標下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混合OLS回歸與RE方法所得系數數值相差不大。對于組內競爭(RIVW),在模型二、四、六中交互項MB×RIVW的系數都為正(0.0904,0.0555,0.0354),分別在P<0.05,P<0.1和P<0.05水平顯著。即組內競爭對處于移動壁壘內部(MB=1)企業的不利影響顯著地小于它對移動壁壘外部(MB=0)企業的不利影響。對于組間競爭(RIVB),在模型二、四、六中交互項MB×RIVB的系數都為負(-0.1499,-0.0759,-0.0540),分別在P<0.05,P<0.05和P<0.01水平顯著,即組間競爭對處于移動壁壘內部(MB=1)企業的不利影響顯著地高于它對移動壁壘外部(MB = 0)企業的不利影響。模型二、四、六相應比模型一、三、五的R2顯著提高(均在P<0.01水平),表明加入交互項后模型的解釋能力顯著提升。檢驗結果表明,在移動壁壘內、外部的企業無論參與組內競爭或組間競爭,企業績效受到的影響均有顯著不同。因此,在分析行業內競爭的效果時,應結合移動壁壘以及競爭的性質都做出分類考慮。
以上結果發現了移動壁壘分隔下的組內競爭和組間競爭的效果差異,具有重要理論意義。首先,這提示研究者應注意競爭的本質差異,以后的研究可在模型中對不同性質的競爭做出區分。競爭行為普遍地存在于各個行業中[24]。隨著對競爭的研究不斷深入,越來越需要考慮差異化的模型設定,否則將會得到模糊的結果。例如,在Galbreath和Galvin[25]的研究中,行業內競爭與企業績效相關系數為負,但在生產與服務類企業的回歸檢驗中系數均不顯著。而Cool和Dierickx[3]對組內競爭和組間競爭做出了區分,并發現了它們之間存在一定的此消彼長的變動關系以及對行業利潤的負面影響。

表4 競爭效果差異的混合OLS回歸結果
注:1.系數下方括號中的數字為對應的clustered robust標準誤;
2.Δ R2數值都是與前一模型的比較;
3. 顯著性水平:***p<0.01;**p<0.05;*p< 0.1。
Porac等[24]也區分了同類企業間的競爭和不同類企業間的競爭,并發現同類企業間的競爭程度較高。但上述研究仍未揭示這兩類競爭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有何差異。而在本文的檢驗結果中則可以看到,一旦引入移動壁壘這個結構因素,組內競爭與組間競爭的差異就顯現出來。
其次,以上發現也更深入地揭示了移動壁壘的分隔作用。以往文獻對移動壁壘功能的認識主要是對企業移動的阻礙[6],而對移動壁壘的其它作用表現所知甚少。移動壁壘的理論形象似乎是擋在企業面前的“一堵墻”。而本研究表明,移動壁壘把行業中的企業分隔成為競爭地位不對等的群體,即移動壁壘類似于產生高低差異的“地勢”因素。處在移動壁壘保護內、外側的企業,兩者在分析競爭環境和選擇對手時會有不同的考慮。郭朝陽[18]曾指出,進入某個行業一般不難,但進入后的進一步增長卻較難。這與本文觀點內在地一致,本文還通過實證檢驗揭示了其中的機理。
此外,移動壁壘內、外部企業的整體績效差異在回歸模型中也得到了檢驗。盡管這個問題并未列在本文的研究假設之中,它仍是一個重要理論問題。在表3和表4中都可以看到,變量MB在模型一、三、五中的回歸系數都為正數。在RE模型中分別是0.0815,0.0267和0.0343;在混合OLS模型中分別是0.0816,0.0260和0.0327。在模型一和模型五中的顯著性水平都達到了P<0.01。這些結果表明,移動壁壘的保護對企業平均績效具有顯著的有利影響。這符合Porter[2]的理論觀點,并且為之提供了實證支持。Mascarenhas和Aaker[10]發現移動壁壘是造成平均績效差異的重要因素;Kumar[26]的研究也表明移動壁壘與平均盈利能力相關,本文研究結果與以上文獻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移動壁壘的種類很可能是因行業不同而變化的。也即是說,脫離行業的具體背景知識可能難以捕捉到有意義的壁壘變量。本研究還提示,忽略移動壁壘可能造成戰略群組間的績效比較結果的模糊。例如,Cool和Schendel[8]未發現群組成員身份與盈利水平有直接關系。而Short等[22]雖發現了群組間的績效差異,但其作用效果卻比預想小得多。可以試想,受到不同移動壁壘保護的群組各具優勢,不一定能在績效水平上分出高下。脫離移動壁壘所進行的簡單比較可能不足以揭示群組間績效差異的真正模式。
5 結語
行業內競爭及其效果是管理學研究中的基礎性問題。競爭對參與其中的企業的績效以及整個行業的利潤都具有不利影響。以往對行業內部異質性的認識不夠充分,難以深入揭示不同性質的競爭在效果上的差異。戰略群組理論能夠客觀地把行業分為幾個性質差異較大的企業群,同時使群組內部成員在戰略上高度相似,清晰而簡潔地刻畫出了行業的內部結構。當把戰略群組和移動壁壘納入模型后,競爭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不再是簡單一致的。本研究發現了組內競爭和組間競爭對不同戰略群組中的企業績效具有不同作用。
對于組內競爭,處于移動壁壘內的企業參與組內競爭時受到的不利影響較小,而位于移動壁壘外的企業參與組內競爭的不利影響則很大,兩者具有顯著差異。組間競爭則相反,處于移動壁壘內部的企業參與組間競爭會受到較大的不利影響,而位于移動壁壘外的企業參與組間競爭則影響較小,兩者也具有顯著差異。結論表明競爭的效果隨著企業所處戰略位置的不同而有明顯差異。因此,在分析行業內的競爭格局時至少需要明確兩方面因素:第一,是組內競爭還是組間競爭;第二,企業是否位于某種移動壁壘的保護之內。忽略行業內的戰略群組和移動壁壘很可能無法得到正確的結果。未來研究仍有進一步深入的空間。例如,行業中移動壁壘的高度越大,壁壘內外企業參與競爭的結果差別可能就越大,這需要進一步研究檢驗。
對企業管理實踐的啟示是,對于具有明顯特色和優勢、處于移動壁壘保護中的企業,應把主要精力用于同群組內部成員企業之間的競爭,強化自身的突出優勢,力圖在高利潤或有發展潛力的細分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戰略決策應以本群組的典型選擇為依據,避免過多參與與其它群組成員的競爭。而對于缺少優勢的沒有移動壁壘保護的企業,則不可僅關注現有群組中的競爭。需一定程度上參與組間競爭,避免完全陷于同質化的價格戰之中,而應及時擴充企業技能,把握潛在的發展機會。
[1] Melicher R W, Rush D F, Winn D N. Industry concentration,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profitability[J]. Financial Management, 1976, 5(3): 48-53.
[2] Porter M E. Competitive strategy[M].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
[3] Cool K, Dierickx I. Rivalry, strategic groups and firm profitability[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3, 14(1): 47-59.
[4] Peteraf M A. Intra-industry structure and response toward rivals[J]. Journal of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imics, 1993, 14(6): 519-528.
[5] Chen M J, Hambrick D C. Speed, stealth, and selective attack: How small firms differ from large firms in competitive behavior[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38(2): 453-482.
[6] Caves R E, Porter M E. From entry barriers to mobility barriers: Conjectural decisions and contrived deterrence to new competit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7, 91(2): 241-262.
[7] Reger R K, Huff A S. Strategicgroup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3, 14(2): 103-123.
[8] Cool K O, Schendel D. Strategic group formation and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the U.S.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1963-1982[J]. Management Science, 1987, 33(9): 1102-1124.
[9] Porter M E. The structure within industries and companies' performance[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9, 61(2): 214-227.
[10] Mascarenhas B, Aaker D A. Mobility barriers and strategic group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9, 10(5): 475-485.
[11] Fiegenbaum A, Thomas H. Strategic groups and performance: The U.S. insurance industry, 1970-84[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 11(3): 197-215.
[12] Nair A, Kotha S. Does group membership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steel industry[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22(3): 221-235.
[13] 孫先定,楊錫懷,李穎.基于企業價值的我國家電上市公司的戰略集團與績效關系研究[J].中國管理科學,2002,10(3): 77-81.
[14] 倪文斌,田也壯,姜振寰,等.中日制造企業制造戰略分類研究[J].管理工程學報,2003,17(4): 19-22.
[15] 楊鑫,金占明.戰略群組的存在性及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0,(7): 112-124.
[16] McGee J, Thomas H. Strategic groups: Theory, research and taxonom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J]. 1986, 7(2): 141-160.
[17] Mehra A, Floyd S W. Product market heterogeneity, resource imitability and strategic group forma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8, 24(4): 511-531.
[18] 郭朝陽.策略群組與企業盈利水平的差異[J].中國工業經濟,2002,(6): 86-94.
[19] Guedri Z, McGuire J. Multimarket competition, mobility barriers, and firm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1, 48(4): 857-890.
[20] Bogner W C, Thomas H, McGee J.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competitive positions and entry paths of European firms in the U.S. pharmaceutical marke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7(2): 85-107.
[21] Leask G, Parker D. Strategic groups, competitive groups and performance within the U.K.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mprov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etitive proces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28(7): 723-745.
[22] Short J C, Ketchen. D J, Palmer T B, et al. Firm, strategic group, and industry influences on performa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28(2): 147-167.
[23] Houthoofd N, Heene A. Strategic groups as subsets of strategic scope groups in the Belgian brewing industry[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8): 653-666.
[24] Porac J F, Thomas H, Wilson F, et al. Rivalry and the industry model of Scottish knitwear producer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5, 40(2): 203-227.
[25] Galbreath J, Galvin P. Firm factors, industry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variation: New empirical evidence to a classic debate[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8, 61(2): 109-117.
[26] Kumar N. Mobility barriers and profitability of multinational and local enterprises in Indian manufacturing[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1990, 38(4):449-463.
Opposite Effects of Intra-group and Inter-group Rivalries: A Study Based on the Partitioning Effects of Mobility Barriers
DUAN Xiao, JIN Zhan-m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ntra-group and inter-group rivalries have different performance impacts on firms partitioned by mobility barriers. The sample contains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of China over the period of 2010 to 2011. Data were mainly acquired from CSMAR and RESSET databases and annual reports of those companies. Grouping variables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strategic group research i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he companies were clustered into four strategic groups aided by SAS software with Ward method, and then mobility barriers were identified.POLS and RE models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intra-group and inter-group rivalries in the panel data regressions, where the protection of mobility barriers i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Results show that intra-group rivalry has a stronger adverse impact on firms outside mobility barriers than on firms inside mobility barriers, whereas inter-group rivalry has a stronger adverse impact on firms inside mobility barriers than on firms outside mobility barrier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rivalries within and between strategic group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firm performance. Our findings also suggest that firm studies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trategic group structure and mobility barriers, and the effects of intra-group and inter-group rivalries should be analyzed separately rather than jointly.
strategic groups; mobility barriers; intra-group rivalry; inter-group rivalry; firm performance
1003-207(2015)05-0125-09
10.16381/j.cnki.issn1003-207x.2015.05.016
2013-06-21;
2014-03-19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71172003)
段霄(1982-),男(漢族),河北邯鄲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業戰略管理.
F272;C9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