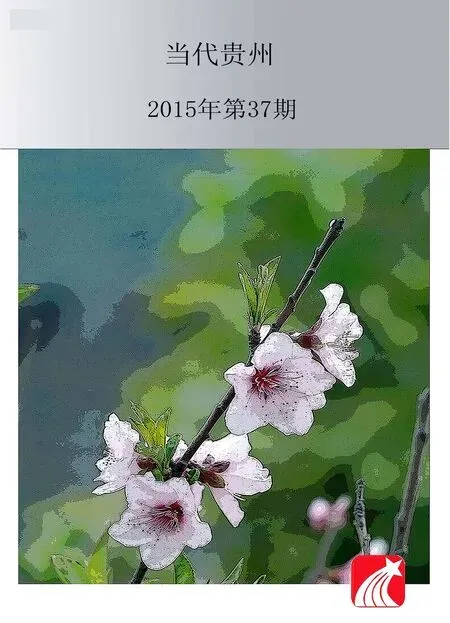一次重要的基層行政體制改革
——記上世紀九十年代貴州建鎮并鄉撤區工作
文丨王茂愛
一次重要的基層行政體制改革
——記上世紀九十年代貴州建鎮并鄉撤區工作
文丨王茂愛
“小鄉”時代,鄉干部只管傳政策、蓋公章、催公糧、抓計劃生育,群眾也只想著種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建鎮并鄉撤區后,政府開始抓產業,群眾開始關心市場。到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和黨的十四大召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工作主旋律時,我省基層干部群眾的觀念也基本跟上了趟。
很多人或許還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貴州進行過一場重要而特別的基層行政體制改革,這就是建鎮并鄉撤區。
這是一次重要的改革
涉及面廣。當時除貴陽所轄5個市轄區,區下直設辦事處,以及銅仁的玉屏、黔東南州的岑鞏因規模小和歷史上多次變動,為縣直轄鄉外,全省還有80個縣和特區在縣和鄉之間設置有區。因此,這次改革直接涉及約630個區,3776個鄉(鎮),5萬余名干部職工,關系到3000余萬農村人口的生產生活。
爭議很大。一方面,區管鄉由來已久,大家已經習慣,撤區后,小鄉并為大鄉,縣及縣以下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運轉方式以及干部職工的工作、生活方式都要轉變,需要時間適應。另一方面,鄉是最基層一級政權,俗話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并鄉弄不好會削弱基層組織建設,大家都很擔心。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不應撤區并鄉。因為貴州是山區,溝壑縱橫,交通不便,農村主要還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鄉的主要任務就是傳達貫徹中央精神,完成上級交辦事項,了解反映社情民意,調解群眾矛盾糾紛,以及給辦結婚證的人出具證明等。因此,鄉小一點,簡單一點好。當時還有人編了一個順口溜:“撤區并鄉,百姓遭殃,包起午飯,來蓋公章。”諷刺并鄉后群眾辦事會不方便。二是撤區并鄉勢在必行。因為區只是縣的派出機構,不是一級政權,但服務功能比鄉健全得多,導致“虛實顛倒”;縣鄉之間加區這一層次,行政層級多,方針政策和工作任務不能迅速傳達落實,降低了效率;鄉級機構規模普遍過小,經濟基礎薄弱,不利于發展商品經濟;鄉級機構人少事多,待遇較低,不利于調動干部職工積極性。岑鞏,玉屏等縣的干部群眾普遍認為,取消“二傳手”,黨的惠民政策和群眾見面更直接。
影響深遠。一是有力推動了基層干部又一次思想解放。通過討論,大家逐步認識到,公社改鄉已實行多年,體制紅利明顯遞減,已不適應現實發展要求,必須改。實踐證明,改革結果讓干部群眾都嘗到了甜頭。二是有效促進了基層干部群眾的觀念轉變。“小鄉”時代,干部只管傳政策、蓋公章、催公糧、抓計劃生育,群眾想的也主要是如何種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小農意識比較嚴重。并鄉后,政府開始抓產業,抓財政;群眾開始關心市場,思考如何把產品變為商品,市場經濟觀念逐步樹立。特別是建鎮并鄉撤區工作還未完全結束,即遇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和黨的十四大召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工作主旋律,基層干部群眾的觀念基本跟上了趟。否則,恐怕還要晚幾年才起得了步。三是奠定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農村基層體制基礎。這之后的改革,有撤鄉設鎮或改辦事處的,有撤小村并大村的,但都是局部調整,大格局基本未變,為農村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這是一次特別的改革
中央領導提議。1990年新春伊始,時任國家民政部常務副部長的張德江同志來貴州考察調研扶貧濟困工作。在基層走訪過程中發現,貴州普遍在縣和鄉之間設有區這樣一個中間層次作為縣的派出機構。而且,不管是機關,還是民政等社會管理服務部門,機構都只延伸到區。如法庭、派出所、司法所、糧管所等,而鄉作為最基層的一級政府,除了書記、鄉長、人大主席團主席,只有秘書、財政員、計生員等,統共十來個人,很多基層服務工作做不了,區鄉“虛實顛倒”。這樣的體制,不僅不利于服務群眾,發展農村商品經濟,況且,全國還保留這種行政體制的地區已寥寥無幾。因此,與貴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座談時,張德江同志建議貴州盡快改革,撤區并鄉,把鄉政府充實健全。
1990年3月20日,貴州省委召開常委會研究 “撤區改鎮并鄉”,決定由省民政牽頭,省委辦公廳、省委組織部、省財政廳、省人事局、省編委、省體改委派人參加,調查研究后再商議具體實施方案,建鎮并鄉撤區由此拉開了序幕。
工作方案獨具特色。一是文種特殊。省委省政府開展建鎮并鄉撤區的工作方案,既不是《決定》,也不是《實施意見》,而是《指示》。二是文字簡練,全文不足5000字。筆者當時在省委辦公廳調研室工作,全程參與了前期調研,并承擔了本組分報告和給省委省政府總報告的文字撰寫工作。
1990年12月的一天上午,當時分管調研工作的省委副秘書長伍席源同志向我交待:省委省政府近期要研究撤區改鎮并鄉,要我趕快以省民政廳的名義,草擬匯報材料初稿。我考慮到匯報材料必須簡明扼要,就把調研情況,遇到的問題,基層的情況反映和大家的意見建議梳理若干條,寫成關于撤區改鎮并鄉調研情況及意見建議,下午就交了稿。次日,又帶上伍席源副秘書長審改過的稿子,隨時任省委秘書長的李元棟到黔南調研,在都勻與正在陪同民政部救災專員調研的省民政廳楊序順廳長一起,利用晚上時間又作了一次修改。
1991年元月9日,省委常委會聽取了撤區并鄉建鎮情況匯報并原則同意,只是將“撤區并鄉建鎮”改成“建鎮并鄉撤區”,要求盡快將匯報材料改寫成具體實施意見。執筆人依然是我,考慮到這個文件主要是面對基層干部群眾,不宜多講道理,語言要淺顯易懂,文字要精煉,于是就開始寫:一、建鎮并鄉撤區勢在必行。二、建鎮并鄉撤區要積極穩妥推進。三、建鎮并鄉撤區工作的具體原則。四、從實際出發調整行政區劃,確定鄉,鎮規模……一氣呵成,全是“干條條”。
實施方案交到省委辦公廳文書處后不久,時任文書處處長劉援朝同志找到我,提了以下要求:這是我省自己的一項工作,不是貫徹中央的部署;這是一項重要工作,但時間很緊,三年內必須完成;這是一項布置任務的工作,須馬上啟動,方案省委常委會通過即可,不等省委全會討論。因為文字簡練,所以采用《指示》這個文種發布。

作者(右三)在黔西南州安龍縣金州農耕文化園調研(作者供圖)
1991年2月19日,貴州省委、省人民政府《關于開展建鎮并鄉撤區工作的指示 》下發。
2012年7月1日,中辦取消了《指示》這一文種。后來,我查閱有關檔案時發現,改革開放以來到取消為止,省委文件中,《指示》僅此一次。
實施過程平穩。盡管之前爭議很大,但啟動后推進較為順利。一是工作基本上實現了無縫對接,農業生產、農村工作未受耽誤。因為大部分地區原來幾個鄉相隔不遠,干部群眾之間并不生疏。二是干部情緒總體穩定。建鎮并鄉撤區后,不少人隨機構升級得到提拔,平級交流的也能服從大局。全過程沒有發生過激行為,很少上訪,特別是沒有群訪。
這是一次有意義的改革
貴州實施的這次基層行政體制改革,有兩點啟示值得我們在今后工作中應用借鑒。
謀事要實。參加“三嚴三實”專題教育,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謀事要實”的要求,覺得“建鎮并鄉撤區”工作之所以能順利實施、沒有反復,正是全過程體現了“謀事要實”。一切從實際出發,積極穩妥推進。1990年3月省委醞釀此事時,即考慮了三步走:當年進行調查研究,制定分期分批進行的方案;1991年地州市各選一個縣進行試點;1992年全面開展。
1991年元月省委常委會聽取匯報和討論時專門強調:在一縣(市,特區)范圍內,要一次規劃,力爭一步到位;工作程序上先建鄉(鎮)后撤區,務使農村各項工作有人抓、不斷檔;民族鄉一般不作大變動;村的行政區劃,一般不作調整;堅持因陋就簡,充分利用現有設施,不搞大拆大建,確需新建辦公樓的鄉(鎮),要幾個部門共建,搞綜合樓,一樓多用;重點做好縣區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充分發揮縣區干部的積極性。
改革整個過程中,當時分管農村工作的省委副書記、建鎮并鄉撤區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龍志毅和其他領導同志,多次到基層調研指導。
群眾至上。建鎮并鄉撤區,本來目的就是更好的服務群眾和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因而處處貫穿群眾路線。如新建鄉鎮選址上強調照顧歷史、重視發展,要有利于生產、方便群眾;規模一般在150平方公里左右,人口2萬人左右為宜。同時,交通方便、經濟發達地區可適當大于這一規模。邊遠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可適當小于這一規模。其目的,就是盡可能方便群眾。(作者系貴州省委統戰部副部長 責任編輯/豆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