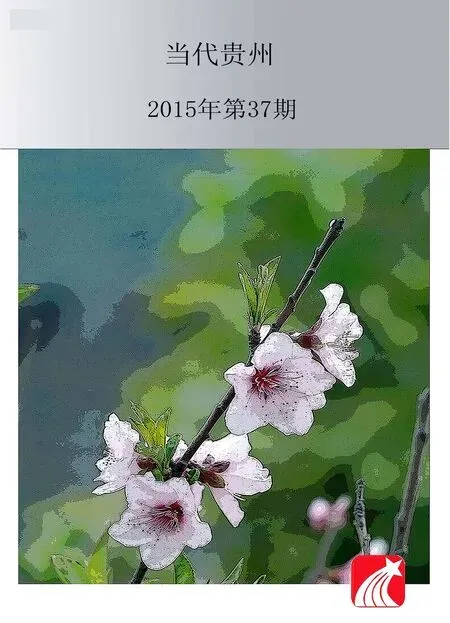法治的社會需要司法公正
法治的社會需要司法公正
法治意味著法律的普遍適用和至高無上,法律平等地約束社會一切成員的法治原則,必須經由公正的司法活動來貫徹實施。

王利明
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民法學研究會會長。系新中國第一位民法學博士。
司法公正,就是指審判人員依法獨立地行使審判權,切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司法公正,直接關涉公民的財產和人身安全,經濟的有序、健康發展,政治的穩定以及社會的安寧。
我們需要司法公正,是因為司法是保障人民權利、實現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行政的調處、領導的平衡或干預,曾經是解決民間糾紛的重要方式。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些形成于舊體制的解決爭議的方法已被證明無法適應變化了的社會需要。在開放的、由平等主體的交易構成的市場經濟中,平等主體之間的糾紛只能由一個獨立的、中立的、享有公共權力的司法機構來解決,這個機構就是人民法院。
公民和法人之間的各種糾紛,不論是民事、經濟的,還是刑事、行政的,只有依法院的裁判,才得以最終解決。這種裁判借助了公共權力的強制執行而具有其他任何類型的裁判所不具有的權威性。當公民和法人的權益受到侵害,當弱者受到強者的欺凌,當社會的良知受到惡勢力的踐踏,受害人能夠尋求的最后一處伸張正義的地方就是法院。法院是保護人民權利的最后屏障。
我們需要司法公正,是因為司法公正是法治的最重要內容。法治意味著法律的普遍適用和至高無上,法律平等地約束社會一切成員的法治原則,必須經由公正的司法活動來貫徹實施。公正的司法,不僅在于懲惡揚善,弘揚法治;同時也是對民眾遵紀守法的法治觀念的教化;是對經濟活動當事人高效有序地從事合法交易的規制。而枉法的裁判、不公的裁判,不僅扭曲了是非,混淆了正義與邪惡,而且會造成民眾對法律的權威性的懷疑、不信任甚至蔑視,法律虛無主義的觀念由此滋生,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成果將因此而遭受毀滅性的摧殘。
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決比多次不公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公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決則把水源敗壞了”。
我們需要司法公正,是因為公正的司法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在現代社會,經濟和法律是不可絕對分開的。經濟的增長、財富的創造需要一個良好的法律環境,法律對經濟的保障和規制都需要公正的司法來體現。公正的司法不僅使投資者和交易當事人充分享有法定的投資自由和交易自由,而且也可以使其合法權益得到司法的充分保障,這就會使人們產生投資信心、置產愿望和創業的動力,經濟由此會得到繁榮和發展。
我們需要司法公正,是因為它是社會安定的基礎。一方面,司法公正能夠給予民眾切實的安全感,使其對于經由正當途徑獲取的財富產生合理的期待;對于依法享有的人格尊嚴和人身自由的保障充滿信心。這樣,人們可以在法定范圍內自由行動,全社會的公正觀念亦得以形成和強化。另一方面,司法公正真正能夠維護民眾對公共權力機構的信任,即使公民的權利受到來自行政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的侵害,也可通過公正的行政訴訟,使其遭受侵害的權利得到充分補償。公民和政府之間的良好關系,通過公正的司法而維系。
尤其應當看到,當無辜的受害者、權利受侵害的當事人不能通過訴訟討回正義和公道時,很可能導致其對法律和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的失望甚至絕望,并可能采用合法途徑以外的乃至于非法的方式自行解決糾紛,從而危害社會的秩序和穩定。所以,在我們這樣一個改革的時代,當各種利益發生沖突、摩擦的時候,通過司法公正而保持社會安定,尤其重要。
司法公正是人民的真誠企盼。那些秉公執法、剛直不阿、明鏡高懸的清官的故事,千百年來給予了庶民百姓莫大的慰藉,包拯、海瑞這些“青天”,也因此成為人們崇拜的正義的保護神。我們的法官是人民的法官,法官手中的裁判權來自于人民的授予,如果我們的法官不能夠為了人民的利益而公正執法,其手中的權力還有什么價值?維護司法公正是每一個法官的神圣職責,司法公正是對司法腐敗的摒棄,是對司法專橫的否定,我們應當公正執法、杜絕腐敗,充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出自己的貢獻。(責任編輯/吳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