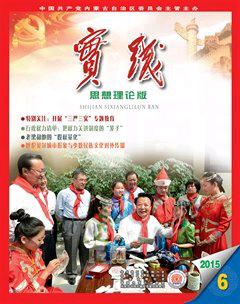文化中的生態:鄂倫春族、鄂溫克族的生存智慧和挑戰
白蘭

文化作為一種資源,人們利用它創造和延續對自然的特定適應方式,解決生活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文化多樣性歷練了人類千百年的智慧,體現了人類適應環境的能力和機制,并實現著獨特發展。文化多樣性保護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傳統文化中的生態知識、文化生態觀在當今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本文以鄂倫春族、鄂溫克族為例分析文化中的生態。
一、鄂倫春族、鄂溫克族概況
鄂倫春族是狩獵民族。有文字記載“鄂倫春”始于清代,史料中稱為“摩凌阿鄂倫春”“雅發罕鄂倫春”“俄爾吞”“俄樂春”“畢拉爾”等。“鄂倫春”是自稱,有“山嶺上的人們”和“馴鹿的人們”兩種意思。鄂倫春族有8196人,主要分布在內蒙古自治區和黑龍江省。1951年10月成立鄂倫春自治旗,總人口28萬人,其中鄂倫春族2500人。
傳統生活中,鄂倫春人恪守有物共享、平均分配的習慣。飲食中鄂倫春人以獸肉為主,野菜、魚類為輔,糧食是通過交換所得。交通工具是獵馬,住房是圓錐形的30多根樹桿搭蓋的“斜仁柱”,冬季用狍皮圍起來,夏秋則用樺皮圍蓋。出獵時騎馬,雪深時也用滑雪板。獵槍、獵馬、獵狗、獵刀是鄂倫春男人的伙伴,漂浮的白云、滿山的野花、針線盒、搖籃是鄂倫春女人的朋友。林中出沒的松鼠、撲扇著花翅的蝴蝶、溪水里游動的小魚,都是鄂倫春孩童的玩伴。
游動遷徙的生存方式,合作和分享的社會準則,豁達平和的心態,構成了狩獵文化的基本特征。狩獵文化是鄂倫春人千百年來在大、小興安嶺和外興安嶺地區的游獵生活中與自然不斷碰撞而形成的與特定的自然環境相適應的文化行為。
“鄂溫克”漢意為“走下山的人們”,也解釋為“大山里的人們”。200多年前,他們是清朝驍勇善戰的“索倫部”將士。鄂溫克族人口30505人,主要分布在內蒙古自治區和黑龍江省,新疆也有鄂溫克人。1958年成立鄂溫克族自治旗,總人口為144251人,其中鄂溫克族11307人。鄂溫克族文化呈現為農耕、游牧和狩獵的多元特征。
特別要說的是,在北緯52度呼倫貝爾草原和大興安嶺交匯處的泰加林區,生活著中國唯一牧養馴鹿的鄂溫克族。鄂溫克人在過去幾千年間游走于苔原地與森里之間,封閉但堅強地與大自然融合,大自然是鄂溫克人最親密的朋友,是鄂溫克人最安全的精神家園。
今天,鄂倫春、鄂溫克族的發展面臨著與現代化相交的文化碰撞之痛。現代文明帶來了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也帶來了適應新的生活方式的困惑。
二、狩獵民日常生活中的生態意識
鄂倫春族與鄂溫克族同自然的關系是最為直接的,因其完全依賴于自然的生存方式。其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敬畏自然而遵從自然”,深刻表達了人與自然融為一體的生存法則,其在酷寒條件下生存的特有的生活方式及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影響了整個中國寒溫帶地區。
鄂溫克族的游徙人群與馴鹿種群和諧地相依為命,鄂溫克族的小生境系統整合了動植物種群與地方族群的物質與精神文化。
鄂倫春族以狩獵民那神秘的空靈感,保持著森林特有的自然和安詳,他們不會任意改變和毀掉什么。生活、生產中有許多禁忌,是他們在千百年的山林生活中積淀下來的。當失去這一切,那種與山林交流的智慧也將失去,與大自然交流而建立起來的生命體驗也將湮滅。
三、狩獵民習慣法中的生態意識
保護生態環境和森林資源的傳統觀念、法制、規定和習俗等內容是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鮮明的生態保護特征,反映了我國少數民族對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進行科學保護和合理利用的情況,同時也體現了文化對森林資源保護和經營管理的影響和作用。從文化推動社會發展的視角出發,對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及其與森林資源管理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學習和借鑒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將對促進生態文明建設非常有意義。
鄂倫春人和鄂溫克人強調的社會法則是,森林是共有的,獵場是共有的,獵物平均分配,狩獵民沒有貪婪和囤積,沒有弱肉強食。正因如此,他們對山林沒有形成硬傷式的索取,這和現代社會中汰弱留強的叢林法則形成強烈對比。
現在,在森林生活的場景中,我們能深刻地體會到很多變異了的因素,例如帳篷逐漸代替了傳統住屋“斜仁柱”,紛至沓來的人們也打擾著這里的靜謐生活。與現代社會的廣泛接觸中,森林生活表現出了不穩定狀態。必須要指出的是,人口極其稀少的族群千百年來一直生活在高寒山林地帶而沒有滅絕,對生態環境沒有造成破壞,是因為他們有適應山林游獵的生存本領和技能。這種獨特的文化優勢就是鄂倫春人和馴鹿鄂溫克人的生存哲學——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獨到見解和價值觀。
四、狩獵民宗教信仰中的生態意識
鄂倫春族和鄂溫克族信仰的薩滿教是以“萬物有靈”為信仰核心的,與宗教信仰緊密關聯的禁忌文化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民族在不同的自然環境和社會交際中逐步形成的一種復雜的社會文化現象。隨著社會的發展,許多禁忌的具體內容與形式會發生轉化甚至消亡,但是有些禁忌卻仍然在現實生活中擔當著重要的角色,許多民族的禁忌習俗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仍然發揮著其他法律規范、制度措施所不能比擬的積極作用,可以認為少數民族包括禁忌在內的傳統文化對生態保護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有著積極作用。
五、狩獵民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
在現代社會中,狩獵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將漸漸退出歷史舞臺,但他們的文化理念告訴我們:人類對自然規律的遵從將是唯一可持續發展的路徑。
由于禁獵,負載著鄂倫春人、馴鹿鄂溫克人的價值取向、生存哲學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而對現代社會并不熟悉、對新的生產生活方式尚未完全適應,讓他們表現出了種種困惑和矛盾。這種困惑和矛盾在逐漸消磨他們的意志,使他們的生活方式變異而不為外界接受。
文化中的生態是狩獵民的生存智慧,它將警示人類從人類中心主義的噩夢中醒來,回歸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永續發展的理念,這是現代以及未來人類文化發展的主流,也是人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因此,從生態學視角認識和理解人類面臨的各種困境和問題,尋求可能的、合理的解決途徑,顯得格外迫切和重要。
六、狩獵民文化與生存的出路選擇
現代文明的進入是對狩獵民文化延續的一個挑戰。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成功地創造出了滿足人們基本需要的方式。人們在獲取自然資源的同時,非常注意資源的再生和重復利用,使資源能夠長期滿足人類的需要。
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是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有著適合當地環境的獨特優勢,并與其價值觀、世界觀、生活態度密切相關。在現實社會中,人們認識和理解傳統生產生活方式時如何看待文化,會對文化變遷產生重要影響,在外部作用力較為強烈的地方尤其如此。
當代人遇到的難題是,我們在獲得巨大成功面前,對于所付出的自然生態破壞的代價能夠承認,而對文化生態破壞的代價卻被考慮較少。于是就形成了當代人在解決自然環境問題上遇到的一個無法走出的悖論,這就是我們希望在原有的工業文化不變的前提下,以導致自然生態破壞的文化與理念來挽救自然生態環境。
以多元民族文化的破壞來換取工業化,如同破壞生態環境換取經濟增長一樣,是值得關注的另一種生態破壞。
(作者系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責任編輯:康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