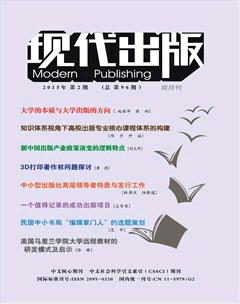晚清時期商務印書館地理學譯著出版的文化貢獻
◎ 肖 超
晚清時期,商務印書館是我國較大的民營出版機構,其翻譯出版的地理學書籍在民營出版機構中占有一定地位。
一、商務地理學譯著出版概況
筆者利用周昌壽編撰的《譯刊科學書籍考略》,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所編《新編中文書目:地理類》,結(jié)合艾素珍①②和鄒振環(huán)③對晚清時期地理學譯著的研究,對這一時期商務版地理學譯著的書名、出版時間、出版數(shù)量等作了考證。經(jīng)統(tǒng)計,商務印書館在1897~1911年間出版了19種地理學譯著。商務印書館的地理學翻譯出版工作始于1901年。這一年,商務出版了《地學講義》和《日本地理志》兩種日文地理學譯著。到民國成立前,又陸續(xù)出版了《(中學)萬國地志》《揚子江》《世界地理志》等地理學譯著。在這19種地理學譯著中,日譯地理學著作有15種,占比78.95%。此外,來源于美國的地理學譯著有3種,源自法國的1種。④
這一時期,廣智書局、作新社、金粟齋、會文學社、通社、學部編譯圖書局等譯書機構也出版了一批地理學譯著。其中,廣智書局的人文地理學譯著與學部編譯圖書局的區(qū)域地理譯著,出版數(shù)量多,品種全,形成了自己的出版特色。會文學社擁有范迪吉等知名譯者。與這些專事譯書的機構相比,商務印書館的注意力集中在地理學教科書的編撰上,出版的地理學譯著在數(shù)量上并不多。
二、主要著譯者為歸國留學生
晚清時期,商務印書館的地理學譯著主要由日本翻譯而來,因而作者多是日本人。據(jù)筆者統(tǒng)計,1897年至1911年間有15種地理學譯著譯自日本,排重及加上合著作者后,日本個人作者有11位,包括志賀重昂、中村五六等集體作者為日本參謀本部。此外,來自美國的作者有忻孟和謙本途,法國作者為波留。
經(jīng)筆者對晚清時期商務版地理學譯著第一譯者的統(tǒng)計,翻譯兩種以上地理學譯著的譯者僅有3人,分別是王建極、奚若和張元濟,這說明這一時期譯著的譯者較為分散。歸國留學生是譯著的主要譯者,其中以留日學生居多。邵羲是留日學生譯者中的代表。1903年,他在上海預備立憲公會兼任會刊編輯員時翻譯了《地文學問答》。由《<地文學問答>譯例》⑤可以看出,該書的譯介與其留日經(jīng)歷有密切聯(lián)系。留日學生通過翻譯活動,傳播了經(jīng)日本人消化的西方地理學思想。
三、商務地理學譯著出版興起的原因
晚清時期商務印書館地理學譯著出版的興起,一方面受到編譯所設置這一內(nèi)因的促進,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留日熱潮的推動和地理學教育的發(fā)展。
1.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設置
在1897年建館之初,商務印書館只是一家專事印刷的機構。1902年,編譯所的設置,使其重心轉(zhuǎn)移到出版上來。經(jīng)張元濟舉薦,蔡元培出任首任編譯所所長。據(jù)蔣維喬回憶:“由蔡元培先定國文、歷史、地理三種教科書之編纂體例,聘愛國學社之國文史地教員任之,蔣維喬任國文,吳丹初任歷史、地理。”⑥可見,此時商務印書館的選題環(huán)節(jié)由編譯所長決定,并聘請教員編撰地理教科書。1903年,張元濟接任編譯所所長后,聘請蔣維喬為常任編輯員,莊俞編輯地理。半年時間,蒙學課本初稿十冊編撰完畢。而后,商務印書館“聘高鳳謙為國文部主任,采合議制,先定編輯之根本計劃,依此計劃,審查已編成之蒙學課本”。⑦此時,商務印書館已采用會議制來商討選題。可見,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設置,尤其是張元濟擔任編譯所長后,地理學譯著的策劃出版開始步入正軌。
2.留日熱潮的推動
甲午戰(zhàn)爭以后,中國掀起了留學日本的熱潮。1896年,清朝政府選派13名青年學生留學日本。以后,留日學生逐年增加,1901年274人,1903年1300人,1905年8000人,1906年竟達12000人。⑧留日學生取代傳教士,成為翻譯出版界的主要譯者。梁啟超、羅振玉、張之洞等學界和政界人士都提倡翻譯日文書籍。國內(nèi)也建立了多家翻譯出版日文書籍的機構。熊月之以《中國譯日本書目綜合目錄》統(tǒng)計資料為基礎,推算了中國翻譯日文書籍的數(shù)量。他認為從1896年至1911年15年間,中國翻譯日文書籍至少1014種。⑨在這一時期翻譯的日文書籍中,社會科學、史地類的書籍數(shù)量增大,譯自日本的地理學書籍也逐漸增多。
3.地理學教育的發(fā)展
19世紀末,中國人自辦的新式中小學校多單獨設置了地理課程。⑩京師大學堂等高等學校也開設了輿地課程。地理教育逐步在高等學校和中小學中開辦起來。同時,政府也頒布章程,規(guī)定在地理以外的學科中設置地理課程。1902年,政府頒布《欽定學堂章程》,規(guī)定大學預備科、政科設置中外輿地課程,中小學設置地理課程。1903年,清政府頒行《奏定學堂章程》,規(guī)定經(jīng)、文、格致、農(nóng)、商等科皆應設置地理課程,在進士館、譯學館、師范館等都設各種地理課程。1906年,清朝政府頒布《優(yōu)級師范選科章程》,規(guī)定在以培養(yǎng)初級師范及中學的師資為主旨的優(yōu)級師范中,設置地理課程。
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制度,廣設學校。新式學堂地理課程的開設,客觀上推動了地理學教科書的出版。此時,中國傳統(tǒng)輿地學已經(jīng)不能適應新式學堂的需要,翻譯日本地理教科書成為一條捷徑,因而地理學翻譯出版日漸興盛。
四、商務地理學翻譯出版的文化貢獻
晚清時期,商務版地理學譯著通常作為教科書使用,重心在于普及地理學知識。商務印書館地理學翻譯出版的意義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1.增進了國人對世界的了解
國人通過閱讀商務版地理學譯著,能夠更加清楚地認識整個世界。商務印書館譯介的《地理讀本》為美國人謙本圖所著,是一套游記類譯著。謙本圖1903年從北美出發(fā)開始游歷,到非洲結(jié)束,每游歷一洲就刊行一本游記。這套游記經(jīng)孫毓修譯述后,1908年開始出版,國內(nèi)外出版時間間隔很短。《地理讀本》的譯介,能夠讓國人及時且充分地了解世界概況,保證國人對世界認識上的先進性。譯著采用“中國游歷員語氣”,通俗易懂。同時,譯本也聯(lián)系了鄭和下西洋等國人知曉的歷史知識,緊密結(jié)合了時下國內(nèi)國際形勢,讓國人能夠身臨其境地跟隨謙本圖游歷,進而輕松地認識這個世界。
商務版地理學譯著讓普通民眾認識到中國以外的世界,了解到世界之大。通過閱讀地理譯著,國人打開了眼界,認識到自身的狹隘,從而引發(fā)了中國人世界觀念的轉(zhuǎn)變,促進了中國社會的變革。
2.促進了中小學地理教育的發(fā)展
與明末清初的漢文西書相較,商務版地理學譯著通常作為新式學堂教科書使用。其中,《東洋歷史地圖》和《西洋歷史地圖》屬于《最新中等教科書》系列,《地理讀本》《(中學)萬國地志》《地文學》《地文學教科書》等也作為中小學教科書使用。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范圍不局限于精英階層,而是擴散到中小學生群體。
美國人忻孟所著《地文學》一書,經(jīng)商務印書館譯介后即作為中學教科書使用。在翻譯時,譯者對原文作了一些適于國情的調(diào)整,以便普通民眾閱讀。由于作者是美國人,書中引證的美國資料很詳細,譯本中刪去了與文中關系不大的附圖。在標點符號上,譯者“讀用點,句用圈,遇專名則加點于旁”,符合國人的閱讀習慣。為了簡便地理單位,譯本“以喱代英厘,!代英尺,!代英寸,哩代英里”。由于中外地理單位不同,讀者容易混淆,譯者列出了中外地理尺度換算表,以便讀者核對。清朝1905年廢除科舉制后,教育體制產(chǎn)生了重大變革。《地文學》作為中學教科書使用,廣大的學生讀者群體保證了該書的市場需求,促使該書初版一年后就再版。為了培養(yǎng)學生對地理學科的興趣,商務印書館譯介了一些游記作為學生課外讀物。《地理讀本》即作為中學課外讀物使用。該書體例新穎,采用了“旅行體”風格。譯者孫毓修認為之前的地理課本“枯寂寡歡”,讀來乏味。即便一些地理教科書采用了游記體裁,但是“作者往往未出戶庭,僅集合他家之書,以己意附會之”。《地理讀本》作者仍是美國名人謙本圖,他學識好,寫作質(zhì)量也高。孫毓修將該書譯介后作為教科書使用,能夠培養(yǎng)學生的興趣,使學生快樂地學習和吸收地理知識。此外,《地理讀本乙編》書末還附有地圖和其他地理教科書的廣告,有益于學生進行延伸閱讀。
商務印書館重視譯本的適讀性,精心譯介體裁新穎的西方地理著作,為學生提供了易于學習且不失趣味的地理教科書,傳播新知。因而,這些地理學譯著的出版客觀上促進了中小學地理教育的發(fā)展。
3.加快了中國地理學的近代化
晚清時期西方地理學著作的譯介,加快了地理學及其他科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這一時期,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地理學譯著多作為教科書使用。在使用譯著作為教科書的過程中,中國教師潛移默化地吸收地理學譯著中的學術思想和優(yōu)良體例,從而影響了其今后的地理學教科書編撰實踐。因而,商務印書館地理學譯著為清末新式地理學教科書的編撰提供了范例。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地理學教科書的編撰在框架結(jié)構、知識體系和表述方式上,深受地理學譯著(尤其是日本教科書譯本)的影響。19世紀,西方地理學常采用數(shù)理地理學、自然地理學和政治地理學的三分法。在鄒代鈞《京師大學堂中國地理學講義》等地理教科書中可見此種分類體系。清末出版的問答式、游記體、白話文教科書,均受到西方地理學譯著編寫體例的啟發(fā)。同時,國人編撰的地理教科書多取材于日文地理學譯著。一些輯錄的地理教科書,明確表示資料來源中有日本地理學著作。總之,在商務印書館等出版機構地理學翻譯出版的推動下,國人在地理學教科書編撰中吸收西方地理學知識,促進了中國地理學近代化。
注釋:
①②艾素珍.清末自然地理學著作的翻譯和出版[J].中國科技史料,1995(3):16-22,26-35.
③ 鄒振環(huán).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J].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53-406.
④ 肖超.商務印書館地理學譯著出版研究(1897~2012)[D].南京大學,2014:155~165.
⑤ 邵羲.譯例[M]//邵羲.地文學問答.上海:商務印書館,1903:1.
⑥⑦蔣維喬.編輯小學教科書之回憶(1897~1905年)//蔡元培等.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Z].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57.
⑧⑨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508-509.
⑩ 褚亞平等.地理教育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