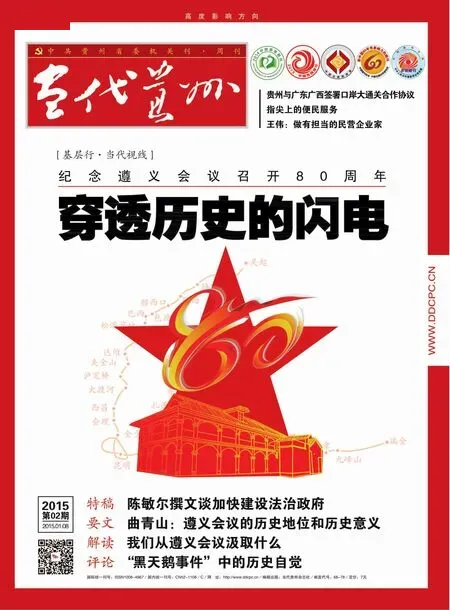憶遵義
整理丨本刊記者 彭美玉

周恩來
“新三人團”的成立
一個比較小的問題,但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就是從遵義一出發,遇到敵人一個師守在打鼓新場那個地方,大家開會都說要打,硬要去攻那個堡壘。只毛主席一個人說不能打,但別人一致通過要打,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還是不聽,他也只好服從。但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里提馬燈又到我那里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這樣,毛主席才說,既然如此,不能像過去那么多人集體指揮,還是成立一個幾人的小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組指揮作戰。 (摘自周恩來1972年6月10日的講話,據中央檔案館所存記錄稿)

朱 德
談遵義會議
第五次反“圍剿”就更壞了,完全是洋教條,把過去蘇區反“圍剿”的經驗拋得干干凈凈。硬搬世界大戰的一套,打堡壘戰,搞短促突擊,不了解自己家務有多大,硬干硬拼。軍事上的教條主義,伴隨著其它方面的教條主義,使革命受到嚴重損失。直到遵義會議,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才結束了錯誤路線的領導。長征后一、三軍團一共只剩下了七千人,這都是教條主義拒絕毛主席的正確思想,把方向搞錯了的結果。(摘自朱德1944年在延安編寫紅一軍團史座談會上的講話)

彭德懷
二占遵義
蔣軍追迫遵義,紅軍放棄遵義,繼續向西轉進。待各路敵追迫至云南、貴州、四川三省交界時,紅軍從間道插回桐梓。三軍團向南轉進,在婁山關與王家烈部約四五個團遭遇,王部被我擊潰,我軍猛追至遵義,當晚強攻該敵,敵棄城南逃,這就是第二次攻占遵義。(摘自《彭德懷自述》)

劉伯承
回顧長征
遵義會議以后,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象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敵人之間,以為我向東卻又向西,以為我渡江北上卻又遠途回擊,處處主動,生龍活虎,左右敵人。我軍一動,敵又須重擺陣勢,因而我軍得以從容休息,發動群眾,擴大紅軍。待敵部署就緒,我們卻又打到別處去了。弄得敵人撲朔迷離,處處挨打,疲于奔命;這些情況和“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相對照,全軍指戰員更深刻地認識到:毛主席的正確的路線,和高度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藝術,是使我軍立于不敗之地的唯一保證。(摘自劉伯承:《回顧長征》)
從黎平到遵義
1935年1月初,我軍渡過烏江,接著打開遵義,為召開這樣一次會議創造了條件。打遵義,二師六團是攻城部隊。渡過烏江以后,六團團長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同志就接受了攻取遵義的戰斗任務。他們把一切攻堅的準備工作都做好了。這時,總參謀長劉伯承同志趕到了他們部隊,他當時對干部講:現在,我們的日子是比較艱難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傷亡少,還要節省子彈。這就需要多用點智慧。后來隨著情況的發展,這次攻打遵義的戰斗,實際上變成一次智取遵義的戰斗。(摘自《聶榮臻元帥回憶錄》)

楊尚昆
回憶遵義會議
這是一次帶有緊迫性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當時,因為被戰事所分割,一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不可能到會,但是到會的還是占多數。五中全會后的政治局委員,除顧作霖因病去世外,還有11人,出席會議的有: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陳云、毛澤東、朱德6人,超過了半數,缺席的5人中,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張國燾在四川,任弼時在湘鄂川黔,項英在江西堅持游擊戰爭。政治局候補委員共5人,出席會議的有劉少奇、王稼祥、鄧發、凱豐(何克全),是絕大多數,只有關向應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中央的4位書記(或叫常委),除項英外,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都出席了。后來張國燾竟說,遵義會議他沒有參加,不能算。這真是不講理了!(摘自《楊尚昆回憶錄》)

伍修權
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
會議一般都是晚飯后開始開會,一直開到深夜。因為中央政治局和軍委白天要處理戰事和日常事務。會場設在公館樓上一個不大的房間里,靠里面有一個帶鏡子的櫥柜,朝外是兩扇嵌著當時很時興的彩色花玻璃的窗戶,天花板中央吊著一盞舊式煤油燈,房間中間放著一張長條桌子,四周圍著一些木椅、藤椅和長凳子,因為天冷夜寒,還生了炭火盆。會場是很簡陋狹小的,然而正是在這里,決定了黨和紅軍的命運。(摘自《星火燎原》季刊,1982年第1期)

康克清
難忘遵義
幾百人聚精會神地聽周恩來傳達中央政治局擴大會的情況。他講到博古、李德兩人在軍事上犯了十分嚴重的錯誤。給紅軍和蘇區造成重大損失,使我們不得不進行這次長征。因此,中央決定取消他二人的最高軍事指揮權,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負責指揮,而周恩來又是黨中央委托的在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指揮者。會議決定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這,仿佛是陰沉的天空響起了驚雷,跟著是狂風暴雨般的掌聲,一陣陣經久不息。許多人流下了激動的眼淚。傳達結束,會場上爆發出激動人心的歡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工農紅軍萬歲!”“偉大的黨中央萬歲!”(摘自《中共歷史轉折關頭——關鍵會議親歷實錄(下冊)》,李劍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