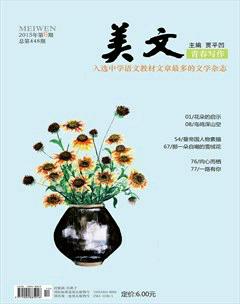尋找孤獨的語言文字
我們每天說的很多話,本身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但如果不說這些話,似乎就會陷入尷尬中,就會令人覺得沒有禮貌和教養。
“吃了?”
“吃了。”
“去走走的啊?”
“嗯,去走走的。”
“你也吃了?”
“吃了。”
“你也去走走的啊?”
“嗯,去走走的。”
我經常聽到長輩們偶遇時,會進行類似的對話,仿佛在街上見到了熟悉而不了解的人,沉寞會顯得尷尬,而要說什么,又覺得彼此之間沒有熟悉到可以無話不談,甚至傾心相交的地步。于是,語言變成了某種打破沉默狀態的工具。可是,沉寞的對立面未必就是熱情的問候,多數情況下只是化解尷尬氣氛的草草之談而已。
有時,我們經常看到一些人夸夸其談,卻不知所云。他們喋喋不休地說著,舌頭在翻滾,嘴巴一張一合。還有的人三三五五地圍成一個圈,交頭接耳地談論著奇聞軼事。有時,還能看到好多人都搶著說話,唯恐自己插不上嘴,但卻很少用耳朵聽別人說話,用心聽的則更少。那么,這些語言的意義在哪兒?
語言,本是因思想而生的。現在,語言卻成了習慣性和模式化的產物。不說話就難受,卻不知道想要表達什么。很多時候,語言只具有向外的功能,唯獨無法向內擴展。多數人害怕孤獨,于是,他們憑借群體社交,獲得一時語言表達的快感,然而,在這種看似雙向的溝通中,語言存在的本質意義早已蕩然無存。
有些語言是喧囂的、吵鬧的,有些則是孤獨的、靜默的;有些是溝通的媒介,有些反而是交流的藩籬,誤會的橋梁,沖突的肇因。孤獨的語言,往往是將視線引向內在的,只有在擁抱和享受孤獨的時候才會顯現出它的意義。它在安靜的角落里,等待時機,靜靜地流淌出來。誠如方子春言“我自靜默向紛華”。
文字,是寫下來是語言。孤獨的語言寫下來是孤獨的文字。盡管有些東西我們永遠無法書寫,無法記載,但我確信,愈是有價值的文字,愈是孤獨的;愈是孤獨的文字,則愈是有價值的。蔣勛說:“語言和文字的終極是更大的孤獨。”它們的背后,是一顆顆孤獨的心靈。這樣的心靈屬于孤獨者,尤其屬于偉大的孤獨者。當我用心聆聽這些文字的時候,眼前總會浮現出那些孤獨的背影:一個老者,一個衣衫襤褸的人,就像赤腳的第歐根尼 ;一個赤腳的人,一個瘋瘋癲癲的人,就像寫下《悲劇的誕生》的尼采。他們都背對著我,緩緩走向杳渺的遠方,走向密林的深處。這些背影總令我雙目涔涔,淚水盈眶。在緊張忙碌的學習間隙,我經常從父親的書房中,努力尋找一些用心寫成的孤獨的文字,然后用心聆聽它們。于是,它們便擁有了一個可貴的分享者,那種字里行間透露出的孤獨被我分享了一部分,我便也獲得了一分可貴的孤獨感。我慶幸自己是那個分享者。
好的語言和文字總有兩面性: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確定性的一面企圖精確表達或傳達某種信息和意義,不確定性的一面則表達“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東西。當語言和文字以廢話和套話的面目出現時,人們之間的溝通表面看起來是不成問題的,彼此似乎很理解對方所表達的意思。當它以另一種形式出現時,人們卻理解不了了,溝通反而成了問題。此時,語言和文字就會陷入孤獨中。然而,正是這種孤獨,才折射出語言的本質。這一本質要求語言不應是模式化的東西,應該承載更豐富的內在和更深刻的思想。正如蔣勛所說:“孤獨是一種沉淀,而孤獨后的思想是清明。”
說出的并不重要,沒有說出的才最重要;嘴巴說出的并不重要,心靈說出的才最重要;筆端寫在紙上的文字并不重要,文字背后的才最重要。好的文字是“生命最深處的吟嘆”,所以,讀書不是用眼睛看那些文字,而是用心領悟文字背后的意義。我曾讀到夏曼·藍波安的一句話:“父親是很低的夕陽了。”這句話所要表達的意思,有的人可能會這樣寫:“父親,大去之日不遠矣。”還有人可能會這樣寫:“父親年事已高,體弱多病,可能快要死去了。”很顯然,三種寫法中,第一種寫法能帶給人更多的感動。死亡變得非但不可怕,反而充滿了一種詩意和壯美感。
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帶我進出各種書店。去年暑假,父親帶我前往南京五臺山下的獨立先鋒書店。那是我所見過的最好、最具特色和個性的一家書店。書店所售圖書皆為嚴肅書籍,外來經典譯作頗多,沒有一本教輔資料。書店的經營格調是“大地的異鄉者”,其內部布局和書籍陳列也充分體現了這一格調。父親與我在里面足足待了一整天。我專門細細地瀏覽那些藏在角落里,封面變得有些泛黃的舊書。它們孤獨地躺在角落,很少有讀者問津,時間久了,蒙上了一層纖塵。從中,我慶幸發現了許多那樣孤獨的文字。那些文字孤傲又謙卑地躲在角落,是不是也慶幸被我分享了呢?它們對我微笑著,沒有回答我。但我分明看得到它們靜默中淡淡的微笑。
【推薦理由】
孤獨,歷來是一個深刻的人文話題。在這個喧囂浮躁的社會里,一個人享有內在的孤獨尤為可貴。作為一名以科學思維見長的理科生,孫瑞軒同時擁有不俗的人文素養,頗為不易。他的文字內斂敏銳,簡潔樸實、內涵豐富、邏輯清晰,論證有力,以超出同齡人思考深度的獨特視角對孤獨進行與眾不同的詮釋,觸及到對人類語言、文字終極有限性的形而上思考,實為不可多得的佳作。
(推薦:蒲錕)
(點評:張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