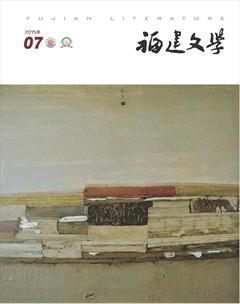那些遠古悠揚的遺響
楊國棟
一
春光明媚春風拂面的四月天,夕陽西下時海風微微吹拂,我感覺爽快而愉悅。黃瓜山連綿起伏的山巒上綠陰濃郁,層層翠茵由田野和港灣向著山頭延伸。因了海拔的低矮,黃瓜山反倒被一株株高大的龍眼樹和一棵棵綠油油的柚子樹擠滿。田壟邊或山腳下,魚肚白似的海蠣殼閃耀著銀白色的耀眼光芒。吳春明館長告訴我,這就是遠古時代留下的貝類遺存。我小心翼翼地挖下一片海蠣殼,簡直不敢想象它的歷史久遠到四千多年前。在那個鉆木取火的年代,這里就已經聚集居住著霞浦人祖先的海邊族群。1987年的那個春天,福建省考古隊進入霞浦普查,發現黃瓜山貝丘遺址,兩年后進行了發掘。2002年中美專家學者合作又進行第二次發掘。依據考古碳14方法測算,認定它是新石器末期的貝丘遺址。當時出土的石器有石錛、箭鏃、石錐、石鑿、兵戈和凹形石器;還有大量工藝比較成熟的陶器,諸如陶罐、陶缽、陶盆、陶盤、陶杯、陶碟的碎片,線條細膩,紋路清晰,分青釉、柏紫青釉和醬釉等。就在我們一行登臨黃瓜山期間,博物館的畬族小伙子小雷,順手向黝黑的土地里一摸,就找出了一個三寸左右長的石錛給我觀賞。作為那個久遠年代古人的生存工具之一,形如魚狀的石錛在福建海邊不少文化遺址中均有發現。小雷將其拾起存入縣博物館,又多了一件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黃瓜山周邊,還發現了先民們告別穴居,懂得遮風避雨的明證——柱洞、桿欄和灶坑。這表明,霞浦先民走出令人窒息的穴居年代并不比中原先民晚多少時間。
接下來吳春明先生的介紹更讓我大吃一驚。他說考古人員在黃瓜山貝丘遺址深掘六米多,竟然見到了碳化小麥和旱稻的實物遺存。這在福建其它海邊文化遺址或貝丘遺址中尚屬首次。這表明,早在三四千年以前,霞浦境內就有了比較先進的農業耕耘,海邊與山野群居的先民就已經開啟了小麥和旱稻的技術性勞作。
旱稻是稻類的一種,原產自中國南方。這里暫且不論。小麥原產地在西亞,何時傳入中國并未見詳細的記載。上世紀六十年代在新疆天山東部石子鄉土墩遺址發現已經碳化的小麥粒,可能是最早的實物見證。1979年塔里木盆地東面的羅布泊西北處古墓中也發現小麥粒。然而史籍記載小麥卻是在《春秋》和《漢書》當中,不過在2000至2500年前。那么霞浦黃瓜山貝丘遺址發掘的碳化小麥,比之中原地區乃至黃河流域的小麥歷史還要更早千余年?小麥是怎樣流入偏安一隅的東南沿海?霞浦先民又是怎樣學會了小麥的種植技術?吳春明館長沒講。可能它就是一連串尚未解開的謎。有待于考古專家拿到更多的實物遺存或者史料,方能獲取準確的答案。
二
離開黃瓜山,我們一行跟著吳春明先生來到了雜草叢生的屏風山。滿山遍野的野蒜苗花和滿天星花朵,為我們輸送了鮮亮潔白的色彩;碩大的野人參帶著泥土的芬芳拔地而起;一畦一畦排列整齊的土地表明過去這里栽種了許多菜蔬和瓜果,而今完全被氣象萬千交叉縱橫的長長葛藤和密集艾草緊緊纏繞。屏風山未必像一扇屏風,也未能擋住來自海灣呼嘯而來的強勁海風。屏風山更像是一個高地的觀景臺,站在逶迤而上的峰巒,可以放眼眺望遠處南北兩個深深的海灣峽谷,清晰地看見海灣內漸次分明的層層綠色景觀和西面豐饒的樹木花卉,尤其是柚子花的清香和梔子花的淡雅,聞了讓人陶醉。
2014年下半年國家文物局已將霞浦屏風山貝丘遺址列入國家的發掘計劃。比起黃瓜山,屏風山貝丘遺址將采取更加先進的氧18考古方法測算。依據目前世界級考古專家來到屏風山考察得出的預見,屏風山貝丘遺址將展示的是五六千年前的實物遺存,較之黃瓜山貝丘遺址早了近千年。我們在山腳下發現的白色海蠣殼,其大小和厚薄同黃瓜山見到的海蠣殼幾乎相同。它同樣是數千年前海邊先民食用的一種海產品。
吳春明先生介紹說,屏風山貝丘遺址發掘的意義重大。它下可以同三四千年歷史的黃瓜山貝丘遺址發生層級連接,上可以同具有6000年歷史并且已經發掘的臺灣白馬港亮島(亦稱浪島)文化遺址發生層級連接。而亮島(浪島)文化遺址所發掘的兩具遺骸,據測算有著6000至8000年歷史,比之河姆渡文化遺址發現的遺骸歷史還長。從兩次發掘后命名為“亮島人1號”和“亮島人2號”的遺骸中提取DNA檢測,發現是未受污染的100%完整的16569個堿基序列,一個為E單倍群,一個為R9單倍群,都是現代臺灣原住民與東南亞若干島嶼族群共有的遺傳血緣基因,被學界判定為南島語族人種。世界研究機構——馬克斯、布朗克人類演化研究所推論,中國內地東南沿海一帶可能是近一萬年以來“原南島語族”的祖居地之一。2014年,研究團隊在臺灣馬祖島進行抽樣調查,對50名健康居民抽血化驗,發現有6人與亮島人DNA符合,證實為亮島人的后代。6人中5人居住在南竿復興村,證實為當時亮島人遷徙到了馬祖。馬祖、連江(含亮島)和霞浦一樣,在遠古時代屬于福州(福建)轄區,這也從血緣上證實了閩臺先民的同根同源。
從亮島文化遺址所發掘的船只殘片為樟木來看,很有可能同位列于霞浦博物館內的樟木古船相同。這表明,在數千年前霞浦海上漁民就有著同臺灣先民交流交往的歷史,他們所使用的石錛、石鏃和陶罐、陶盆、陶碟等等幾近相似。從地理方位上說,霞浦和連江離臺灣亮島較近,其陶器制作技術從霞浦或連江傳至臺灣的可能性最大。
我們下山時,海天依然照射著燦爛的陽光。
三
一縷霞光射入霞浦縣博物館,立刻就有了溫暖溫馨溫潤的感覺。
新建數年的博物館只有幼兒的年齡,卻裝載了數千年沉重的文物古器和輝煌久遠的歷史。漫漫航道上疾速前行的航船,涂抹著朦朧而迷惘的色彩,在悲涼凄婉的心境下,向著先人尚未開辟的海上航線趨進。當三國東吳政權的管轄延伸到溫麻,尤其當溫麻船屯與廣東番禺船屯、浙江橫嶼船屯被東吳并稱為三大官辦造船基地后,溫麻在華夏揚名了,也就源源不斷地向著東吳的海域與長江古戰場輸送著船艦和水手。這看起來是一種榮耀,但榮耀的背后卻也潛藏著戰爭年代溫麻人造船技術的進步和水手船工們的奉獻犧牲。
建衡元年(269年),東吳政權在建安郡侯官縣(今福州市)設立“典船校尉”官職,都尉營設在福州開元寺東直巷,號船塢。于是開啟了福建官辦造船的歷史。當年,東直巷是個河口港灣,群山環抱,綠樹成陰,花團錦簇,又有翻卷的浪濤撞擊岸口碼頭,景色十分秀麗迷人,遂成為東吳在福建的造船中心。三國末期,東吳官府又以“屯田”的方式向閩東至浙南沿海地區擴展,增派兵丁加盟,建立更大規模的造船基地。又由于當時從閩江口至浙江甌江流域溫州一帶統稱“溫麻”,故而有了“溫麻船屯”一詞的出現。典船校尉掌管和監督海船建造,負責將造好的船艦運送到東吳戰場前線,成為溫麻船屯的軍政最高長官。這里距離海邊并不太遠。當年,廣闊的原野和高大的工場人流如潮,卻沒有想到他們當中很多人原來是謫徒(罪人)囚犯,也有部分從當地征調的工匠或出賣苦力的勞工。他們在丁當作響的鐵器和樟木刀砍斧鑿聲中辛勤勞作,用心血和汗水鑄就了一艘艘用于海上或者江面作戰的龐大船艦,在客觀上也培養了一大批技術骨干,較快地發展了福建地方的造船事業。
史料記載,三國時代的溫麻船具有相當的規模,船身長達50余米,寬達7米,高達10米,可以裝載60至70人,或者載物近百噸。溫麻船也稱“溫麻五會”(溫麻五合),“會五板以為船”,也就是船的橫斷面由五塊巨型長木板組合一起,用榫頭密集連接。船艙有隔板,船艙內可以載人或載物;船舷弧形,兩舷插上斧鉞槍戟或者戰旗,煞是威風壯觀。溫麻船最多桅桿上連張五帆,風帆在強勁的海風吹拂下獵獵作響,助添了船艦的風景和氣勢。
溫麻船的特點是,首部尖,尾部寬,兩頭上翹,首尾高昂,艙內寬敞。船的兩舷向外拱,兩側有護板。一片或數片風帆鼓蕩,助力航行。因為船頭堅挺,又配有堅硬的沖擊裝置,故而吃水較深,可達到三四米,適應于海上運輸和作戰。
古代海上水戰或江面水戰,往往需要船艦高大挺拔。水戰從上往下打容易,由下往上打困難;在短兵相接時往往高大的船艦上水兵會向著低矮的船艦跳下格斗或肉搏;水戰激烈時,還往往發生兩軍戰船互相對撞的情況。這都表明船艦造的高大堅挺十分重要。溫麻船屯從實戰需要出發,建造體量大的船艦,艙內設置多層船體,底層放置軍需物資,中層運載軍兵,上層是指揮所與水手船工。戰斗一旦開啟,上層的指揮官居高臨下,看清目標后可以指揮水軍奮力搏殺。有時為了表達對于朝廷皇室的忠誠,指揮官還會下令用自身的船艦碰撞敵船,不惜船毀人亡或同歸于盡,上演著古戰場海戰(水戰)悲愴而悲壯的歷史慘劇。
東吳政權之所以選定溫麻船屯作為造船基地,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福建境內多山,物產豐富,盛產古代造船所需要的木材、鐵器、桐油、蠣灰、生漆和藤、棕、麻等等原材料,加上千年以來閩人在造船這個行當里摸爬滾打練就了本領積累了經驗,因而到了三國與西晉,建造木船的技術接近成熟。他們率先發明并且不斷改進的航船船型,在當時的年代可謂獨步華夏。這為此后福建在宋元時代船艦服務于海上絲綢之路奠定了厚實基礎。
西晉咸寧六年(280年),東吳孫皓被司馬炎所滅,三國歷史就此結束。但西晉王朝依然保留了溫麻船屯。溫麻船的建造技術在三國末年至西晉初年,還算先進。西晉太康三年(282年)因了溫麻船屯的天下揚名而設置了溫麻縣,也是今日霞浦縣的最早縣名稱謂。東吳遺留下相當數量的工匠和屯兵繼續在這里建造船只。只是,他們在遠離了烽火硝煙之后改變了造船的走向。他們不再是官辦船屯,也就不再建造軍用船艦,而是主要建造民用的帆船或者商船。這樣做的結果,帶來了福州和閩東民間造船業的發展和繁榮。到了東晉末年,由于盧循起義軍失敗而被福建官方收編,盧循建造的船艦和技術工匠全部留在了東南沿海。他們加入福建造船和溫麻船屯,極大地提升了溫麻船屯的造船技術水平。其“八槽艦”規模宏大,船艙分隔為八艙,一旦個別船艙內漏水,并不影響船艦的航行,仍舊保留了較大的船艦浮力,不致沉沒。后來,溫麻船屯又改進技術,建造了頭尖尾高,當中平闊,沖波送浪的“了鳥船”,成為那個時代頗具特色的民用商船。這類帆船的特征,后來也成為福州為主創建的“福船”的主要特征,影響了福建數百年的造船歷史。
四
2012年金秋的收獲季節,考古人員在霞浦西南面的屏風山發掘了一艘獨木舟。船身長1106厘米,頭部直徑147厘米,尾部雖說殘缺,也有118厘米,船體中間掏空,凹槽通寬85厘米,通深38厘米,底部平整。依據專家分析,槽內塊狀炭灰是人工焚燒后逐步挖去木炭形成凹槽時留下的,是漢代以前制造獨木舟的主要方法。尾部右側有著明顯的人工鋸切痕跡。那個時代的船工已經開始熟練地使用斧頭和鋸子等先進鐵器。巨大的樟樹被運到造船工場,船匠們先是剪去繁雜的枝葉,然后使用鐵鋸鋸掉瘦小的尾巴,靜靜地削去樹皮,繼而進行煉打,再后涂抹桐油,將獨木舟的外觀建造得通體透亮。難度最大的是如何將船體中間的木質鏤去。因為沒有先進的鏤空技術和工具,先人們只能一斧頭一斧頭地砍削而去。為了省力省時,他們用炭火燒去中間的木質,或者用鐵鋸鋸去部分不需要的木質,這樣就能比較輕松地用斧鑿出有寬度、有長度和有深度的凹槽。專家們從鋸痕的厚薄度分析認定,這艘獨木舟大約有兩千年歷史,是福建省目前發現體量最大的獨木舟,在全國也極其罕見。
遙想當年霞浦境內的原始森林,一定是猿臂掛樹,飛鷹凌空,野狗獵兔,游蛇繞樹,松鼠高跳,走獸出沒無常。陰森森濕漉漉的灌木和喬木叢中,樟樹以其高大挺拔的樹身和稠密的枝葉遮天蔽日,庇蔭著低矮的幼樹和小草花卉,否則就不可想象現在陳列在博物館里的那棵巨型樟木何以能夠劈鑿出這樣長寬和高大的獨木舟?
風吹雨蝕,浪打濤擊,潮漲潮落,多少遠古的珍寶和物件被歲月打磨、時光浸淫而沉湮在大海之中。慶幸的是這只獨木舟挾著半身滄桑和風華,重新展現在世人面前。我從船體涌動而來的浪濤聲和船上陶罐傳導的呼吸聲中聽見,舟船搖蕩的遠古槳聲和彩釉陶片奏響的悠揚音律,以及討海人呼嘯而出的動人歌謠,如港灣里的波紋似的一陣陣傳來,定格在我的大腦深處。然而也有不解和遺憾。亮島上仍有南島語族的聲形,古跡文物的現代遺響中卻并未見到霞浦(福寧)境內南島語族先民的任何記載。他們都去哪兒了呢?難道他們一夜之間全被海嘯的沖天巨浪卷走了嗎?倘若是海嘯為何不將亮島上的南島語族人掀翻卷走?他們被集體屠殺了嗎?為何也未見文字記載?那么他們集體遷徙了嗎?那么好的生態、土地、漁業和生存環境,為何還要集體遷徙?又遷徙于何處?現代的霞浦人講話屬福州語系,先祖來自中原大地,中間的斷層發生在哪個朝代?博物館找不到,縣志里也未讀到。謎面是現成的,謎底何在?或許,只有等到霞浦那淺淺的海灣再次發掘古跡文物,我才可能獲得最佳的答案。
責任編輯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