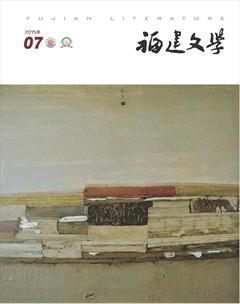鏗鏗榨聲悠遠長
余書林
1972年,我這個出生不好的小青年因患腰疼病,在生產隊里不能做重活,隊長為了甩掉我這個“包袱”,把我安排到了當時的大隊綜合廠。那個時候,是沒有“土壤”讓個體工商戶生長的。有手藝的師傅們,由大隊集中在一起。“綜合廠”這個特有的名詞是再恰當不過的。綜合廠里所有的收入歸大隊所有,年底分給各生產隊。綜合廠里的人員參加自己所在生產隊里的勞動分紅。
我到了綜合廠之后,“廠”里沒法安排我“腰里疼”的人才能做的事。其實,綜合廠里除了那些裁縫、剃頭佬、鐵匠……之類的手藝人,再就是一個榨坊,一個磚瓦“廠”。我來之前,榨坊里的一位師傅原來讀過初中,大隊初辦小學,他的父親又是土改“根子”,被抽走當民辦老師去了。綜合廠領導還算有心,安排我到榨坊里當學徒。我有幸接觸了榨油技術和木榨。
大隊榨坊里那時已有兩種榨機,一種是當時比較先進的液壓榨油機(臥式,后一代改進為立式),一種則是古老而傳統的木榨。
木榨俗稱“撞榨”。顧名思義,撞,撞擊的意思。榨者,榨出、榨取。撞榨就是采用撞擊的方式將油脂榨出油來。榨油的油脂多以當地土生土長的芝麻、菜籽、棉籽等為原料。雖然我的家鄉也產大豆和花生,但是,原先這里的人們不大愛吃這兩種油,因此,榨坊里一般不榨這兩種油。
從油脂到榨出油來的過程,要經過:炒籽、碾(磨)籽、蒸氣,踩餅、撞榨等這一道道工序。這些工序都是有一定的技術含量和難度。不管是哪一道工序做得不認真、不嚴謹,出現紕漏,都會影響出油率和油的質量。
炒籽用的是一口大鐵鍋,但是鍋的置放,與燒火做飯的鍋大相徑庭。炒籽的鍋不用裝水,它的灶面是斜著的,俗稱炒籽鍋為“歪鍋”。炒籽鍋斜放,便于鍋內油脂的翻動,炒籽的師傅只管把鍋內的油脂往上掀,被掀上去的油脂會自動地往下滑落。炒菜籽和芝麻用得是竹笤帚,通常在籽炒好后,直接用笤帚像掃地一樣把它們從鍋里掃出來,方便、快捷。炒棉珠籽則用锨。因一鍋棉籽有好幾十斤,加之還附在棉籽上的短絨,它們相互纏繞,用锨掀效果最佳。锨把用一根繩子吊在房梁上,這樣,能減少炒籽師傅在鍋內翻動棉籽的體力。棉籽炒好后,還要經過礱籽、退殼、篩籽等工序。菜籽和芝麻在焙炒出鍋前,要碾破籽粒看里面的成色。通常要炒得色焦而不糊,味香而不醺。不要太嫩,也不能太老。籽炒嫩了,榨出來的油不香;籽炒老了,必然降低出油率。
碾(磨)籽有歌訣:芝麻破皮,菜籽如泥,棉籽碾得像鍋巴皮。碾磨芝麻只要“一破兩開”就行。菜籽則要碾得“細如粉末”,磨好后的菜籽,用食指頭和拇指頭碾拭時,手感要特別細膩,沒有顆粒狀為上成。抓在手里,一捏成團。棉籽碾出來后,要像“榆錢(榆樹的種子)”一樣,呈一片一片的薄片,黏而不散,才是恰到好處。
蒸氣,是榨油中最為關鍵的一環,這種技術一般都由掌門師傅拿在手里做。蒸氣的蒸籠,就是用一些鐵條,鍛成的一個像鍋的形狀的半邊球體,把它反扣在鍋沿上。油料蒸氣,先把鍋里裝滿水,燒至沸點后,在蒸籠上鋪上紗布包袱,然后把碾好的油脂倒在紗布包袱表面,不用蓋。倒在蒸籠上面的油脂量,恰好是一塊餅所需要的數量。油脂既要蒸透,又不能喪水(蒸氣量過大為喪水)。喪了水的油脂,就會成稀糊狀,踩餅時,不容易踩實,即使做成餅后,在撞榨時,油脂也會從餅箍的縫隙里飆出來(擠壓得射出來),一塊餅能妨礙整個榨筒的出油效果。有時,甚至一榨餅滴油不出。油脂蒸氣俗稱“站鍋”,意味著站在蒸氣鍋邊。站鍋的師傅要一刻不離地守在蒸氣鍋邊,隨時掌握蒸氣的程度。師傅一般都是用右手夾著三根竹簽,不住地來回地操動蒸籠上的油脂,給蒸籠上的油脂以充分的出氣孔,要是蒸籠上的油脂稍有板結,表面的油脂蒸不透,底下的又易喪水。一旦油料蒸得恰到好處時,“站鍋”的師傅就會迅即地取下蒸籠上的紗布包袱,放進徒弟事先準備好的餅“窩”里。
踩餅是學榨油手藝的“跨門活路(即進門學的第一件事)”。那年我進榨坊時,首先學的就是踩餅。學踩餅還要先學抻草。要把一捆雜亂無章的稻草抻得整整齊齊,剛開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把稻草拿在手上后,要像抻拉面一樣,兩只手反復抻,待一把稻草抻順后,再用釘在柱子上的鈀子鈀掉稻草秸稈上的苞葉,然后還要將那些除掉了苞葉的稻草,橫在釘在柱子上的鐮刀口上,把它那參差不齊的兩頭割齊,讓稻草長短一致。開始,我并沒注意這抻稻草的過程中,還暗藏著“殺機”,我在鈀子上鈀那稻草上的苞葉時,卻把小指靠手掌的邊上鈀出了一條口子。當時一滴滴的鮮血“汩汩”溢出,染紅了稻草我才發現。至今,我的手上還留著一條一寸來長的疤痕。踩餅之前,要在餅箍里做好餅窩。做餅窩,即把那一把抻齊的稻草在一端的二十公分處扭上一轉,再將那扭成絞的地方折成彎,用手把那長約五十公分的一端呈放射性分散開來,接著反過來鋪在餅箍上,以這放射性的稻草作為包餅的“經”草,然后用那些鈀下來的稻草苞葉鋪在那“經”上面,作為包餅的“緯”草。踩餅全憑兩只腳。第一腳下去,就要把餅窩內的油脂鋪平。踩餅人的腳,要不怕燙。可想而知,剛在鍋上蒸得熱氣騰騰的油脂,溫度該是多高?餅要趁熱踩,油脂冷了,就踩不緊。特別是靠近餅箍處要踩結實。不然在上榨時,餅就會散掉。踩餅踩餅,就是要把油脂踩成餅。撞榨里的餅直徑有七十多公分,厚不過三厘米,要踩好拿在手里不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開始學踩餅的時候,一連三次新踩的餅都是剛側面立起來,就像現在有些地方新建的橋梁一樣,沒等汽車上去,橋就垮了。要是解放前,我學這門榨油手藝,肯定要吃師傅的“家伙”的。那時,是集體所有制,損失多少都與師傅無關。師傅只是用鼻孔“哼”了兩聲。“哼”下之意,不外乎說我很笨吧。我現在寫這篇文字,當時情景又歷歷在目。
撞榨,算是榨油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使力的活路。技術要領也很強。撞桿是一根一丈多長的檀木,只有檀木韌性最強,不易折斷。撞桿的前端占整個撞桿的五分之三,較粗,頭上鑲嵌著一個重約五十來斤的鐵砣帽。在五分之二和五分之三處鑿有一長槽,長槽的中間拴著一根一尺五寸來長的吊桿(連桿),吊桿的上頭系著一根從屋梁上垂下來的纜繩。后端手握的那一頭,稍細一些,粗不過虎口,撞榨師傅握著既受用,又好使力氣。撞桿用來撞擊榨上一個叫“撞釬”的楔子。“撞釬”呈扁錐形,分上下兩根。每根的頭上也鑲嵌著與撞桿上相同的一個鐵砣帽,鐵帽與撞桿上鐵帽呈正、反相對著。撞榨師傅在撞榨時,不是像人們打靶那樣,先瞄準目標,然后再撞上去。撞榨師傅而是勾著腰,兩只手握緊撞桿,呈前弓后箭架勢,先把撞桿的前端壓得高高地翹起,慢慢地向前運動到最前的止點,撞桿幾乎到了直立的程度。這時,撞榨師傅迅急地向后退跑,一直退跑到最后的終點時,借助慣性,人直立,高高地舉起撞桿,再手腕運力讓那撞桿的前端落下來。就在那撞桿落下來之際,撞榨師傅傾其身體和所有的力量,猛地撞向木榨上的撞釬。金屬撞擊金屬時,發出“鏗”的一聲巨響,好似從沉寂中爆炸出的一聲“驚雷”。要是餅剛上榨,就這一下,木榨上的楔子能向前推進一寸多遠。要不了三五下,榨筒內的油餅,就會被擠壓得疼痛難忍,牽動它那大腦的哭泣神經,“慟哭”得“聲淚”俱下。這就是撞榨出油的情景,十分壯觀。撞榨的師傅這時會像一個勇士追擊敵人一樣“乘勝追擊”,前后不停地迂回,一桿緊接一桿地撞擊……
撞榨師傅撞榨時要費很大的力氣,即使是數九嚴冬,哪怕只穿一件油膩的單衣服,身上也是暖氣融融。
木榨榨出來的原油,味道純真,氣味濃香,油體清亮,是機械榨榨出來的油不可比擬的。當然現在科技提煉出來的精品油,則另當別論了。
古老的木榨是一個十分笨拙的物體,長有一丈五六尺,高也有五六尺。榨身由四根粗大的棗樹挖鑿組合而成。棗樹質地堅硬,不會變形,它有液體難以浸入,不容易腐朽、受得住擠壓等特點。這四根方形棗木,由四個井字架分為兩頭固定著。四根棗木的中心由“榨木匠”挖鑿出一個長約丈許、直徑與餅箍稍大一點的內圓空,名叫“榨筒”。鑿這么大一個“洞”,榨木匠全憑一張錛,一把大圓鑿。做成一個榨,要的時間一般都是講多少月,而不是多少天。榨木匠一天“撾” (方言:zhua的第二聲) 出來的木渣不到兩捧。按民間對榨木匠做出來的事情的形容是:“那些木渣要是能吃,供一個榨木匠吃一天都不夠。”這說明過去的“木榨”不是做出來的,而是磨出來的。榨筒的兩邊對開著一道尺來寬的工作槽。供榨師傅裝榨、卸榨、分餅箍等工序用。更重要的是供“打榨”( 擠壓油餅)時的諸如:木餅(分別置于油餅的兩頭)、撞釬、方子等楔子運行。
榨木匠是一種特殊的行業藝人。據說,只傳兒子,不傳女婿。榨木匠名曰木匠,其實算不得木匠。榨木匠只會做榨和維修榨,連那木匠師傅做得最簡單的“拖灰筢”都做不好。榨木匠使用的是“錛”而不是斧頭。修整木料,不是 “砍”而是“撾”。榨木匠不使用刨子,要把那些堅硬的木材收拾得光滑如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說那榨筒的內徑,正好是餅箍的外徑那么大,要是不光滑、不精確,打榨時,那些餅塊就會出現畸形而影響出油。
我1976年從榨坊里出來的時候,我那親手觸摸了三四年的木榨,已經壽終正寢。這時的機械榨越來越先進,出油率越來越高,技術含量越來越低,一般懂機械的人都能操作。炒籽也是機械,甚至不用蒸氣、不用踩餅了。只要把炒好的油脂倒進榨里,油就會汩汩流出。
木榨這種古老的傳統榨油工具和工藝消失了。我書寫它,是它曾經存在過。是想讓后人見到這篇文字時,知道歷史的長河中,人們的生活中,社會的發展中曾經有過一種“木榨”和榨油這門手藝。是想讓它那“鏗、鏗——”的榨聲在歷史的長河中源遠流長。
責任編輯 林東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