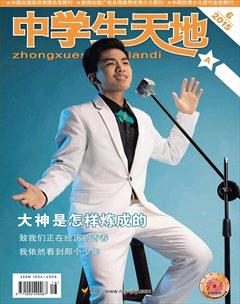我依然看到那個(gè)少年
每次聽許巍那首《少年》,心頭就會(huì)涌起一點(diǎn)小憂傷,伴隨著一種略顯斑駁的畫面感。在歌聲里,我似乎與那個(gè)名叫“吳志翔”的懵懂少年狹路相逢。他站在操場上,稚嫩,清新,感受著蔚藍(lán)天空下晨風(fēng)拂面的溫柔。他幾乎一無所有,手心里卻緊緊攥住一個(gè)還沾著朝露的夢想。雖然他并不清楚,那夢想究竟是什么。
歌中唱道:“世界已過去多少年,如今的你們在哪里?經(jīng)歷著什么樣的故事、什么樣的幸福傷痛?”哪怕像我這么平凡的一個(gè)人,從少年時(shí)代出發(fā)的若干歲月里,也多少會(huì)產(chǎn)生一些故事,雖然它們未必有多精彩。曾經(jīng)不舍晝夜地奮筆寫作,留下整整一編織袋無人問津的文稿任老鼠啃咬;曾經(jīng)在工廠的車間看著房頂?shù)男熊嚢l(fā)呆,只有廠房外火車的汽笛聲給我一絲遠(yuǎn)行的沖動(dòng);曾經(jīng)借住學(xué)生宿舍準(zhǔn)備考博,幾天后卻被毫不客氣地掃地出門;曾經(jīng)有過短暫的“北漂”生涯,但冷硬的寒風(fēng)和無邊的孤獨(dú)又把我趕回南方,我還為此造出“需要沙發(fā)而不是馬背,需要家里的炊煙而不是路邊的篝火”這樣沒出息的句子來自我安慰……當(dāng)然,一直在讀書,一直在思考,一直信奉哲學(xué)家利奧塔說的“成為自己,就是不斷寫出屬于自己的句子”,一直在“學(xué)者”和“作家”的邊緣游蕩,卻從未真正登堂入室。
那個(gè)帶著朝露的夢想呢?是否已經(jīng)在時(shí)間的巷道里風(fēng)干,在日常的慣性里淪陷,在現(xiàn)實(shí)的重壓下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參照很多人心目中的成功標(biāo)準(zhǔn),我所經(jīng)歷和擁有的一切都無比寒酸。沒有出大名,沒有賺大錢,沒有登高位,沒有寫出轟動(dòng)一時(shí)的作品,沒有創(chuàng)造出值得一提的價(jià)值,總體上來說,只是路人一枚。我相信自己在未來應(yīng)該能寫出更像樣的文字,嘗試“在母語的天花板下不斷摸高”(哲學(xué)家德里達(dá)對“寫作”的描述)。但是,正如畫家雷諾阿所說:“等我吃得起上好牛排的時(shí)候,我的牙齒已經(jīng)掉光了。”時(shí)光在無情地侵蝕我們?nèi)蓊伒耐瑫r(shí),也改變著我們精神的成色。是誰說過,一個(gè)人14歲時(shí)若不是個(gè)理想主義者,他一定庸俗得可怕;一個(gè)人40歲時(shí)若還是個(gè)理想主義者,他一定幼稚得可怕。當(dāng)少年的吶喊變成了中年的呢喃,當(dāng)激越的抒情化為平緩的敘說,我們似乎與年少時(shí)那個(gè)朦朧的夢想已漸行漸遠(yuǎn)。
或早或晚,慢慢地我們都會(huì)懂得,在守望夢想的同時(shí),也要學(xué)會(huì)尊重平凡,尤其是要接納和尊重自己的平凡。我曾說過,沒有夢想的人生不值一過,的確如此,但我同樣說過,不該輕視和嘲笑“塵土中的匍匐前行”。夢想的確很可貴,但我總覺得很多人掛在嘴上的夢想相當(dāng)可疑。有的所謂夢想不過是欲望的化身,有的則是花哨的唱腔,有的甚至成了帶點(diǎn)心理病態(tài)的虛火過旺,所以我會(huì)給出這樣的建議:不要受困于高海拔的理想。
“報(bào)大仇,醫(yī)大病,解大難,謀大事,學(xué)大道”,龔自珍提到的這些大愿,聽起來蕩氣回腸,但正如這個(gè)世界正在經(jīng)歷的是一個(gè)“小時(shí)代”一般,我們個(gè)人所遭逢的也常常是些小事小情。如果不習(xí)慣從最小的地方做起,我們恰恰容易令自己因?yàn)閴粝肱c現(xiàn)實(shí)的巨大落差而陷于失望和頹廢的境地。許多抱有大志的人,渴望超越平庸的人,往往對于平淡的生活更缺乏耐受力,動(dòng)輒發(fā)出一些生不逢時(shí)的矯情之嘆,冒出許多自我夸飾的悲情之語。豪情滿懷的英雄,常被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打敗。
我讀過多遍的當(dāng)代中國最優(yōu)秀科幻小說《三體》三部曲,構(gòu)建了一個(gè)深湛、恢宏的幻想奇境。里面的角色貌似尋常,卻都主動(dòng)或被動(dòng)地卷入了與人類文明生死存亡息息相關(guān)的重大使命當(dāng)中:有的實(shí)現(xiàn)了與外星文明的交流,有的憑個(gè)人力量與敵意的外星文明建立起了威懾平衡,還有一個(gè)孤獨(dú)的絕癥患者,他做過的最浪漫的事,嗬,居然是送了一顆幾百光年外的恒星給暗戀的女孩……這些大到“宇宙尺度”的情節(jié),總是給我極致的震撼。要說夢想,這才是超越一切的夢想!眼眸里映著“銀河系的星光”,踏上孤絕且永無歸期的太空流浪,此情此景,想想也是醉了。只是,這樣的狂肆傳奇和夢態(tài)抒情,只會(huì)發(fā)生在科幻想象的時(shí)空里。我們所要面對的,終究還是一個(gè)平凡的世界。
記得剛參加工作那會(huì)兒,我對周遭的環(huán)境和自己的狀態(tài)特別不滿意,焦慮感總在心頭咕嘟咕嘟冒著泡兒。每天黃昏降臨時(shí),我會(huì)斜靠在宿舍單人床上,與室友競相抱怨生活是如何虧待了自己。可是時(shí)至今日,我已不再焦慮。我開始承認(rèn)自己的平凡,學(xué)會(huì)不再用可見的指標(biāo)來丈量自己人生的成敗。我知道自己本質(zhì)上與快遞小哥、房產(chǎn)中介、便利店大姐以及千千萬萬認(rèn)真工作和生活著的人并無區(qū)別,知道是否勤勉、專注、誠信、堅(jiān)持等才是決定人生品質(zhì)的核心要素。我知道今天的夢想太擁堵,倒是平凡的自我期許還顯出幾分素樸,能帶給自己滿足。得不到世俗意義上的成功,so what? 只要我們忠實(shí)于自己,愿意從瑣碎處著眼,從低洼處起步,從一針一線、一字一句、一點(diǎn)一滴中尋找和發(fā)現(xiàn)意義,生命的價(jià)值感照樣會(huì)如約而來。“當(dāng)不了太陽,當(dāng)一只螢火蟲?”why not!
也有一點(diǎn)警覺,我這一套“自甘平凡”的說辭,莫非是在為自己的無甚作為進(jìn)行辯護(hù)?是因?yàn)樵谧非髩粝氲牡缆飞细吒杳瓦M(jìn)卻鮮有斬獲,眼見大勢已去,于是開始吟唱“平平淡淡才是真”,為自己“背叛理想”的選擇尋找合理性?我確定不是這樣的,因?yàn)闊o論在怎樣繁瑣而平淡的日常境遇里,我依然能看到那個(gè)少年:那個(gè)在操場上憧憬的少年,那個(gè)在瓜棚里苦讀的少年,那個(gè)在屋頂上仰望星空的少年……只要無愧于曾經(jīng)歷過的每一個(gè)日子,那么不管結(jié)果是卓越還是平凡,都是好的。
那個(gè)少年,就站在時(shí)間的景深里,用清澈的眼神提醒我:哪怕一切都是徒勞,也要讓這徒勞發(fā)生;發(fā)生了,便不是徒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