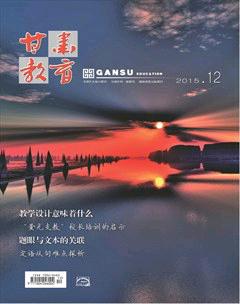母女合發論文,佳話還是作假
喬志峰
上陣父子兵,搞科研也不拒“母女情”。母女合寫論文,原本應該是一段佳話,何以引來作假質疑?無非還是由于其中有著太多的巧合:其一,論文的選題恰好發揮了母親的特長,吳寧主持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后期資助項目“安德烈·高茲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而論文的選題恰屬她的主要研究方向;其二,論文恰好滿足高校自主招生優先條件。由于論文的發表,使張某剛好符合武漢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招生簡章中對報名學生“優先考慮”的要求;其三,論文發表的時間恰到好處。這篇論文和另一篇類似的論文,均在今年2、3月發表,而2月底正是教育部要求各自主招生試點高校公布今年招生簡章的截止日期。如此多的“恰好”,難免令人生疑:這一切都只是“巧合”,還是精心的籌劃?
雖然我們相信“有志不在年高”、不排除中學生也能出“科研成果”,但常識告訴我們,搞科研既需要天分,也需要有扎實的理論基礎,同時還須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高三女生即使天資再高、再有家學淵源,其理論積累真的能達到專業水平嗎?她在繁重的學習之余,真的有那么多的時間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并洋洋灑灑寫出十幾頁的論文來嗎?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奇跡”。
另外,論文的署名也非常有意思,中學生女兒是第一作者,母親是第二作者。或許有人會說:如果成心作假,為了避嫌,母親難道就不能不署名,只署女兒一個人的名字?問題在于,只署一個高中生的名字,論文還能不能發表?最起碼,會引起編輯的疑惑。如果有個專家坐鎮,哪怕是第二作者,其作用也不言而喻。吳教授回應稱,相關論文是女兒自己寫的,她參與修改,“很多都是她自己想的,像引述、符號、思路拓展,我還是提供了一些幫助。”那么,論文到底哪些是女兒想的,做母親的進行了哪些修改、提供了哪些幫助,似乎都有進一步解釋的必要。
可憐天下父母心,特別是中國式父母,為子女的成長和未來操碎了心。只不過,有些時候過多地涉入子女的成長過程,不見得一定能夠事半功倍,反倒可能“添亂”。母女合發論文,到底是佳話還是作假?一方面,需要當事人能夠出示更多證據自證清白,比如論文草稿、修改稿等原始材料;另一方面,教育部門及涉事大學也應對此展開調查,如果其中存在弄虛作假、學術不端的行為,必須依規依法作出處理,否則不足以維護大學自主招生的正常秩序和良好的學術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