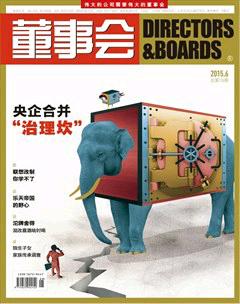聯想改制:你學不了
仲繼銀
柳傳志不是聯想的創始人,卻是聯想的實際締造者。他締造聯想以及推動聯想從一個國有實體企業發展為混合所有制現代公司的過程,是中國轉軌過程的一個生動寫照。不過,無論是職工持股會35%股份的取得,還是中國泛海以略高于凈資產評估價的價格受讓一家成功公司的29%股份,在那些依靠國家大量投資形成的國有企業里,都是行不通的,并且不會被社會所接受
產權明晰化是中國漫長的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一個特色概念。純正國有企業的公司化改制和上市,是在用市場化的概念重新界定清楚國有資產——國有股權之后,實現國有資本與私人資本的混合。這里的關鍵問題,只是一個國有資產的定價問題,這種定價與私人企業的上市定價并無本質差異。定價過低,產生所謂“國有資產流失”,等同于創業者的回報不足,可以選擇不賣;定價過高,則會無人認購。
聯想控股(2015年4月在香港聯交所發布了IPO招股材料)則是中國改革之后產生的一種特殊國有企業,或說新型國企。其特殊或新型所在,是其誕生本身就是一個傳統國有單位(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邁向市場的一種探索。只是很少(20萬元)的國有單位資本投入,但從創業之初到后來的成功,都一直在依靠其母體國有單位的各種支持。理論上,我們完全可以把這種企業看作是,還沒有“混合所有制”概念時的一個實際上的混合所有制企業。聯想漫長的改制歷程,則是隨著市場經濟和現代公司概念的深入發展,逐步將這種模糊的混合所有制清晰化,明確界定出來公和私各占多少比例。
誰是創始人?
聯想公司前身,是1984年由中國科學院計算所創辦的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新技術發展公司。當時中國還沒有現代概念的公司法,股本金、有限責任和董事會等這套概念還都無從談起。作為中科院計算所的員工,柳傳志等人是這一公司創立的推動者,但真正決策者是時任中科院計算所所長的曾茂朝。公司創始人和全部創始資本的提供者都是中科院計算所。
中科院計算所作為聯想公司創辦者和創始人,不僅表現在最初成立時的20萬元“資本金”投入,和將計算所傳達室提供給公司作為辦公場地,還表現在作為公司最初三位負責人的王樹和、柳傳志和張祖祥,都是計算所的員工,被計算所任命為公司負責人。并且這一任命中,還明確著三人各自的行政級別:王樹和為總經理(正處),柳傳志和張祖祥為副總經理(副處)。從計算所的角度看,中科院計算所新技術發展公司就是其新設立的一個二級單位(所辦公司,事業單位辦企業)。
在公司發展起來并最終改名為聯想公司的過程中,計算所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顧名思義,中科院計算所新技術發展公司,頂著計算所的招牌,并實際背靠計算所,將計算所研發的技術進行市場化和產業化,是其當時有別于中關村其他公司的一個關鍵特征。公司的名稱,從中科院計算所新技術發展公司,到中科院計算所公司,最終到聯想公司,源起于1985年開始投放市場的聯想公司的第一款成功產品:聯想式漢卡。“聯想”最初是中科院計算所研究人員倪光南開發出來的漢卡(LX-80聯想式漢字系統)所具有的一種功能,用作產品品牌,最后又用作為了公司名稱(1988年創辦香港聯想公司時開始)。
締造者柳傳志
聯想公司的創辦者是中科院計算所,做出這一創辦決策的是時任所長曾茂朝,聯想作為產品品牌的創始人是聯想漢卡發明人倪光南,這是歷史事實。指出這一歷史事實,有助于我們理解聯想改制的核心內涵,同時,這并不會有損柳傳志在中科院計算所新技術發展公司成為今日聯想帝國過程中的核心作用和歷史地位。
產品品牌創始人、公司創始人和公司帝國的締造者是不同的人,很多世界級公司都是這種情況。麥當勞品牌創始人是麥當勞兄弟,麥當勞公司創始人是克洛克。星巴克品牌創始人是鮑德溫等三人,星巴克公司創始人是舒爾茨。可口可樂產品發明人和品牌創始人是彭伯頓,公司創始人是坎德勒,公司帝國締造者是伍德羅夫。在IT領域里,這種情況也很多。奠定IBM公司核心業務領域(信息處理)的前身公司制表儀器公司的創始人、制表機發明人是統計學家霍列里斯,IBM公司(前身C-T-R)創始人是弗林特,締造了IBM帝國并且給公司取了IBM這一名字的人是老沃森。老沃森作為職業經理人,從僅以5%的分紅權激勵開始,把C-T-R打造為IBM帝國。
從“職業經理人”締造企業帝國這一點來說,柳傳志與老沃森是很相似的。區別在于,老沃森是公司成立十幾年后受聘加盟的,而柳傳志是從成立公司動議開始就參與了。還有一點重要區別是,老沃森從加盟開始就明確擁有5%的分紅權,而柳傳志是經過長時間的改制和多次重組——中國式產權明晰化過程之后,才最終擁有了聯想控股3.4%的股權(根據聯想控股今年4月的香港上市申請書)。由此我們說,柳傳志比老沃森還要道高一籌也不為過。
柳傳志作為中科院計算所員工,盡管從一開始就參與創辦聯想公司(甚至可以說是主謀),但從嚴格的法律和責任承擔意義上,我們說他不是公司的創辦者和創始人,他是公司創立的經辦者,也是以事實上的“職業經理人”身份締造了聯想企業帝國的。在這一點上,柳傳志的角色與鈴木敏文十分相似。玲木敏文作為日本伊藤洋華堂的經理人締造了日本7-11公司,7-11公司作為伊藤洋華堂的子公司發展得比母公司還好,最后重組為7&I帝國。聯想作為中科院計算所的下屬公司發展起來了,最后把中科院計算所的大部分資產和人員重組進了聯想。
股權變更路
1984年中科院計算技術所新技術發展公司創立,為注冊資本130萬元的國有獨資企業。柳傳志最初為副總經理,1986年開始出任總經理。1991年,改名為北京聯想計算機新技術發展公司。
1988年香港聯想公司創立,柳傳志成為主席。注冊資本90萬港元,股東為中科院計算所、中國技術轉讓公司和香港導遠公司,各占三分之一。
1994年,北京聯想公司更名為聯想集團,香港聯想公司以香港聯想控股公司名義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北京聯想持有上市公司香港聯想38.78%的股權。
1997年北京聯想與香港聯想合并,柳傳志出任聯想集團主席。
1998年更名為北京聯想集團控股公司,注冊資本增加到1億元。計算所改制,千余人縮減到百人,大部分人并入聯想集團。成立了聯想員工持股會(640人參與),獲得35%分紅權。
2001年,聯想集團控股公司改制為有限責任公司,更名為聯想控股有限公司,注冊資本增加到6.6億。聯想員工持股會用未分配的歷年利潤購買了聯想控股35%的股權,正式形成了中科院(通過國科控股)出資4.3億元、占65%,以及聯想員工持股會出資2.3億元、占35%的聯想控股公司股權結構。
2009年民營企業中國泛海集團以27.55億元的價格從國科控股手中收購了29%的聯想控股股權,形成了國科控股36%,聯想控股職工持股會35%,中國泛海29%的股權結構。
2010年,源自聯想員工持股會的有限合伙企業聯持志遠創立。創建人為聯持志同(作為普通合伙人)和15家有限合伙企業(作為有限合伙人,由原職工持股會的618名成員和聯持志同創立)。
2012年,以員工激勵為目的的有限合伙企業聯恒永信成立,創建人為聯恒永康(作為普通合伙人)和4家有限合伙企業(作為有限合伙人,由聯想控股的127名員工和聯恒永康創立)。聯恒永信從中國泛海受讓8.9%的聯想控股股權。
2014年聯想控股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20億元,公司發起人包括國科控股(36%)、聯持志遠(24%)、中國泛海(20%)、聯恒永信(8.9%)四家機構和董事長柳傳志(3.4%)、總裁朱立南(2.4%)、副總裁寧昊(1.8%)、副總裁陳紹鵬(1%)、副總裁唐旭東(1%)、惠州市百利宏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少康(1.5%)6位自然人。
對比2009年以來幾個時段的聯想股權結構變化數據可以看出,6位自然人共計持有的11.1%股份中,11%來自原員工持股會(從2009年的35%下降到24%),0.1%來自中國泛海。中國泛海2009年時持29%,現持20%。減少的9%中,8.9%轉讓給了聯恒永信。
標桿的意義
柳傳志不是聯想的創始人,卻是聯想的實際締造者。他締造聯想以及推動聯想從一個國有實體企業發展為混合所有制現代公司的過程,是中國轉軌過程的一個生動寫照。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柳傳志是這個特殊時代的一個特殊的企業家,是一個特殊時代的典范。
柳傳志締造聯想,和王石締造萬科的歷程很像,都是從傳統體制出發,并依靠了傳統體制的各種資源和優勢,但主要是通過到市場上打拼,締造出了一個形式和名義上國有、而事實和實質上很民營化的大型企業。這是他們與傳統的、國家有大量有形資產注入所形成的國企所不同的地方。
兩人的價值取向也有一定的類似性,就是在名和利之間,更多地選擇了名。他們沒有像同時代的那些直接選擇了脫離傳統體制、創建私人企業的企業家那樣,做個徹底的商人,悶聲發大財。就柳傳志和王石來說,相比他們所締造出來的企業,和他們的企業給國家及各方面所創造出來的財富,他們個人財富上的所得,可以說只是個零頭。也正是這個原因,作為非常適應這個特殊時代的企業家,他們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比那些做私人企業而個人發了大財的企業家影響力要大得多。當柳傳志和王石這樣的企業家夠轉身笑納個人財富的時候,這個時代就進步了。
純粹和傳統的國有企業,學不了聯想的這種改制做法。無論是職工持股會35%股份的取得,還是中國泛海以略高于凈資產評估價的價格受讓一家成功公司的29%股份,在那些依靠國家大量投資形成的國有企業里,都是行不通的,并且不會被社會所接受。對于那些新興和新型的創業者,時代的發展已經為私人企業提供了更為平等也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他們已經沒有必要再像前一代人那樣,先戴上頂紅帽子,然后再費力地去把它摘下來。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