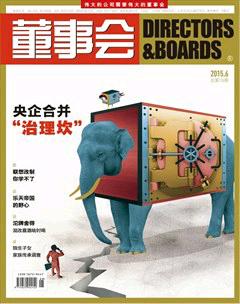如何穿越“混改”關
張喜亮 周海晨
混改企業允許員工持股,但必須汲取之前員工持股中的教訓,員工持股的目的是“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而非變相集資、控制員工或曲線實現“內部人控制”
對國有企業實施股權多元化改革,開啟于上世紀最后十年,不乏成功案例。
從單一IT行業起步,聯想控股經過30多年的發展,構建起“投資+實業”的創新商業模式,成為中國最大的多元化投資控股公司之一。2014年綜合營業額2895億元,利潤41.6億元。聯想公司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業績和美譽度世人公認,其不能不說是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典范。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解讀和貫徹這個文件,加快對國有企業在新形勢下混改,成了焦點和一些人的期盼。一些地方政府急切地設置了混改完成的時間表,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20多年的國企混改實踐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混改中出現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遭到了廣泛的詬病,至今仍心有余悸。站在新起點上,全面深化國企改革,如何推“進”混改,作為國企經理人亦有其不得不“畏”之難。《決定》明確指出:“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核心的內容就是企業的資產或資本屬于全民所有,引進非“國有資本”進行混改,實現資本所有權的多元結構,企業的性質發生變化。如此改革,一方面涉及職工的身份問題——可能產生勞動關系不穩定的問題,另一方面涉及授權的問題——國企所有權性質的變化的授權主體問題。作為國企經理人理論上是沒有權利改變所有權性質的,這是個大原則,不能不令人生畏。事實上,輿論已發出了警示——“混改不可以搶跑”。針對有的地方政府制定混改時間表和覆蓋面的問題,管理層也發出了聲音:混改不能一刀切,需要有序進行。
聯想公司混改的成功案例能否移植到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新起點上的國有企業“混改”,是值得深思的一個課題。最初的聯想公司僅是投資20萬元設立的,其資產影響力度對中科院而言,微不足道。而經歷了36年的改革之后,國企尤其是央企資產的體量巨大。再者,由引進民資股權,再由民資返轉讓與給自然人高管持股,這種行為對于國企經理人(官方稱謂是“負責人”)是難以承受的“利益輸送”之風險。我們不得不承認,中科院國科控股持股36%作為第一大股東,實際上只是聯想公司的投資人,擁有資本收益權,而對公司的生產、經營、資本運作等行為的掌控權大打折扣了。好在聯想公司雖然經歷了風雨坎坷終于成為了優秀企業,如若不然,或有另外的評說。另外,從聯想公司最初的業務板塊來說,是極其單一的,這與今天的國企尤其是央企不同。以央企為例,可以說任何一家的股權結構的混改,都將對國家的經濟運行產生一定影響。所以,對如今的國企經理人來說,對混改存有敬“畏”之心而謹慎行事也是在情理之中。
當然,從聯想公司的混改與今天的成功之中,國企經理人應當學到一些精神和勇氣。混改需要縝密思考,謀定而后動。
首先,經理人必須要做好自身的修練。打鐵要靠自身硬,混改是中央作出的決定,如何操作需要經理人具有過硬的本領。一方面要具有極強的政治責任感、使命感和追求卓越的成就感,同時必須具有極高的職業能力——開拓進取帶領企業健康發展。有高度黨性原則而非個人私欲,在積極進取大膽創新的征程中即便是出現一些失誤也是能夠被理解的。《決定》指出“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國企經理人需要具有企業家的情懷和品質以推進混改。
其次,經理人必須準確把握混改的方向。混改并非是國企改革的目的,而是改革的一種措施,不能為“混改而混改”,更不能簡單地認為“一混就靈”。《決定》指出:混合所有制經濟“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這是國企混改的方向和原則,否則不宜混改。只有那些需要混改又有條件混改的,才可以依法依規混改。混改的重點應當是建立健全治理結構,在推進企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下功夫。
最后,經理人應當縝密謀劃混改方案。混改是一項系統工程,應當全面謀劃妥當操作。目前的國企尤其是央企體量龐大、業務板塊眾多,對國計民生和經濟秩序有著一定的影響,混改方案必須縝密,統籌規劃、系統考慮。可以在影響相對較小的業務板塊或低層級的企業進行試點。要對各子公司或業務板塊進行功能定位分析,屬于競爭性業務、非核心主業的可以試點混改。混改還需要特別注意引進投資人的性質,應當首先考慮的是那些戰略投資伙伴;那種短期利益追求者、企圖借混改國企發橫財者、試圖籍混改侵吞國有資產者、別有用心掌控國有資源者和干擾國家經濟秩序者等,都必須被拒之門外。混改企業允許員工持股,但必須汲取之前員工持股中的教訓,員工持股的目的是“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而非變相集資、控制員工或曲線實現“內部人控制”。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混改方案必須對可能出現的“國有資產流失”情況嚴加防范。是以國有資本的增量部分還是存量部分進行混改,這是個有爭論的問題:本著確保國有資本“價值”增值的原則,把握改革的大方向,準確定位業務功能,便可以化解“增量”與“存量”之爭。
作者供職于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