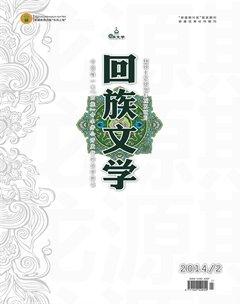漁筌子
竹林坡
在記憶中,我從不認為漁筌子的人有“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這么高的境界,但他們的房前屋后,的確總能夠看到大片的竹子。也許只為了遠遠看去,給人一個回旋的視野和想象的空間。亦可以說,平民生活自有平民生活雅致的地方。我一直這么認為。
在這里我要說的是毛竹不是斑竹(又稱湘妃竹),斑竹總讓人想起帝王和妃子,甚至一些文人墨客,這不是平民家戶的事。而且那斑竹,還要選擇土地才能一根根瀟灑地生長。不像毛竹,從某地挖來一窩,往土里隨便一栽,澆點水,就能蓬蓬勃勃地生長起來。最有意思的是,山野間或者是村鎮聚居的地方,這樣的地方隨處可見。再如外婆所在的鼓鑼山,如我童年記憶里的漁筌子,如同學所住的張家灣、李家坡——在四川東北部,這都是些很平常的地方。長年居住在有坡有坎的山林野地,把竹子也栽到坡坎邊上——這些生長竹子的地方,便習慣地被叫做“竹林坡”。“二女子,到竹林坡去撿幾個筍殼回來引火。”“大嬸子,下午到竹林坡去筢(四川語,在這里讀kuɑ) 竹葉子不?”指的都是這樣的地方。
童年時,一聽到大人們的語言中牽涉到竹林坡,我就想笑。因為漁筌子所在的地方還算平地,竹子總是長在一些溝溝坎坎相對平坦的地方,哪里能跟住在山上的人比?一說到坡,那定是陡峭的。我家屋后的竹林可以叫坡。因為我家建在東河——我們都叫東河,讀書后有老師說應該叫宋江,總讓人自覺不自覺地想起《水滸傳》中那個軟骨頭人,便一直不被認可。我家在東河岸邊,建在大石塊小石板直直壘砌三五米高的保坎上,從后門可以看見碧綠的東河,可以看見對岸的河壩以及居住的人家,也能夠看見對岸的竹林坡。當然,為了居家的安全和保坎的穩固,我們也栽了一叢叢竹子在坡坎的中部平臺邊以及坡坎之下,都是毛竹。
那些毛竹在坡坎下生長著,一兩年就茂茂盛盛地茁壯起來,根根碧綠向天。那些竹子直直中空,四季常青。一到秋冬,新舊替換,黃黃的竹葉兒雪花般紛紛飄揚,但竹子卻經年累月地沒有一點兒枯萎頹敗的跡象。根部的筍殼脫落下來,露出虬須的金黃,在陽光的照射下,就這么暖洋洋懶洋洋地和松梅蘭菊度過歲寒。
這樣的竹子在貧瘠的地方栽一叢活一叢,蓬蓬勃勃地隨著根須蔓延展開。肥沃的土地也能生長,生長得一片一片的,但長出來的竹子卻失去了原本的韌性,容易折斷。我常想,先出林的筍子先遭難,是不是說的就是肥沃土地上長出來的那些竹子呢?答案當然不是。那時候天地間的空氣是純凈清新的,沒有什么環保,也沒有什么污染,大地流露的就是自然與本真。天氣寒冷,在風霜雨雪中,先出林的筍子先遭難,也是自然的。
竹林坡里的竹子總是有許多的好處,不但可以遮陰涼、美化環境,還可以整個兒砍下來做篙竿、修房子,支架起來晾衣服曬藤蔓。可以用篾刀劃細劃小編篾背、莎背、背篼、墊席、簸箕、撮箕、筲箕、竹簍、筢子、蓋子、席子、竹籃子……枯黃落下的葉子可以用竹筢摟到背篼里,背回家墊牛圈羊圈雞窩鴨窩,開年了還可以成為田地里的農家肥。筍殼除了可以引火,還可以用草葉擦去它后背的毛,放到睡覺的篾席草墊下壓平了,剪成鞋樣子。多年的老根和壞了的竹子,可以做上好的燃料——這樣的燃料在平常做飯時是舍不得輕易燒掉的。
那時候的房子多半是茅草蓋的,用木頭做框架,竹籬笆編織填補了中間,為阻止冬天寒風的侵犯,便用黃泥巴調和了麥粒皮抹了縫隙(夏天自然有門窗通風,這樣的房子住著更是冬暖夏涼)。大瓦房也有,可那是廟堂和達官貴人們住的。那時候穿的鞋是外婆奶奶媽媽做的千層底,衣服是粗布衫。那時候吃的稻谷麥子是石窩里舂出來的,是石磨上磨出來的。那時候的灶臺是石板與泥巴壘砌起來的,生火用的是風箱與扇子,燒的是筍殼樹葉樹枝干柴與黑炭……細小的樹枝樹葉與筍殼一樣,都易燃而不耐久,只能做燃火的引子。做一頓像樣的飯,只怕得用小山一樣的葉和筍殼,才做得熟。所以,還得靠過硬的枝柯與木柴。那竹子砍下來曬得面黃肌瘦,便是上好的燃料,只有在過年過節來人上客時,才舍得大把大把地填進灶膛,讓日子過得紅紅火火有聲有色,充滿希望。
于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恬靜的山野恬靜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炊煙裊裊霧籠寒紗,月上柳梢人約黃昏。也有冷的風吹,也有黑咕隆咚暗夜里嬰孩的哭聲,也有呢喃輕唱的歌謠,歌謠說:
鴉鵲鵲,板板梭,一梭梭到竹林坡;找大姐,蒸饃饃;饃饃香,買生姜;生姜辣,買黃臘;黃臘苦,買雞母;雞母惡,買牛角;牛角彎,彎上天;天又高,好買刀;刀又快,好切菜;菜又青,好買針;針又禿,好買驢;驢一走,好買狗;狗又花,一刀花個禿尾巴,大嫂回來哭冤家,二嫂回來抱娃娃……
這首歌謠隨著干寒陰冷的風,在夜的籠罩下呼嘯于原野和山間,若斷若續若有若無黑咕隆咚地跑了很遠很遠,足可以和時間賽跑。靜靜聆聽,靜靜感受,聞者有面容安詳甘苦自知的,也有眼含熱淚潸然而下的……
從公社壩子到甘蔗林
古老而又淳樸的漁筌子,清一色的草房面對面長長的兩排,中間是一條青石板鋪成的街道,從東頭一直延伸到西頭。兩頭都有一棵挺拔茂盛的黃角樹,西頭是公社,有一個容得下千人的壩子,壩子邊沿還有幾棵樹和一個石頭壘成的臺子。這臺子上常常演戲,有樣板戲、地方戲,有時放電影,有時候開會用來做主席臺。壩子在民兵集訓的時候,又成了訓練場,威威武武地站著滿壩的民兵,“突刺刺殺”地喊得震天響亮。在收獲的季節,壩子里揚麥打谷的聲響通宵不滅,大人們相互逗趣和善意的打罵所表達出來的歡樂和欣悅,小孩們在麥山谷垛中“爬雪山”、“過草地”,在空壩里蹦來跳去聚集在一起做游戲的鬧嚷,讓漁筌子的人們記憶了很久很久。
壩子的斜坡下面,是湛湛如玉帶的宋江(即東河)。街道后面是一條公路,公路兩旁有零星散落的單位,雖然是散落,卻也是錯落有致。一切圖像的背景,是雄偉的獨鷹嘴山。從山上看整個的場鎮,竹林郁郁掩映,綠水清清環抱,景色秀麗宜人,別有一番鄉村小鎮的風韻。依山傍水的漁筌子,松散而又不失規格,那清一色的草房給人的感覺是溫馨的、古香古色的、憨直而又淳樸的。
漁筌子的大人、小孩們,有他們各自的艱難與困苦。當戴著帽子的隊長從東頭的黃角樹沿著青石板街道吆喝到西頭的公社壩子里時,他們就得出門,其中不乏正在成長的青少年,遲到了或是缺席了,就要扣工分。工分是一年一度血汗和糊口的一種價值的表述,是他們不辭勞苦不分晝夜勞動的“價值”。那些參加勞動的男女老少,不管你實際中付出了多少汗水,表面上卻要分出個勞動力主次,并以它為標準記工分的高低,到成熟的季節,再用這些紙上的符號累計分計算所得糧食。于是,男人多的,家里的女人便得輕松,省一省,糧食便也充足;男人少的,或是丈夫兒子在外地工作,拖兒帶女的女人們,一年累到頭,工分不多,還難免受人氣,最終又不得不忍耐下去,爭著包攬活兒,為的是多畫些可憐的工分,以便家里的老老小小少餓幾天肚皮。
窮人家的孩子早懂事,稍微大一點兒的便知道替大人分憂解愁,或是幫媽媽做來不及做好的家務事,或是在外尋些能吃的東西帶回家。
沿東河兩岸,隨季節變換,有一望無際的青紗帳——甘蔗林。在日子難熬時,總有人從后門坎上溜下去偷吃幾根,于是,那林子里常常有嚼過的甘蔗殘骸,引來看蔗人一頓頓臭罵。罵也得吃飯啊,罵得愈兇偷吃得愈兇,只要不被人當場抓住,說不定第二天還故意砍倒幾根,讓你受隊長的訓,罰點兒工分。
在夏天的傍晚,那河岸的甘蔗林沒了,便是全場鎮人的樂園。男女老少都會聚到西頭黃角樹下川淹石旁,那嘻嘻哈哈暢游一江的大人小孩,那一浪蓋過一浪的歡聲笑語,洗凈了一切的艱難困苦。即使不能洗澡,冬春之際也有切菜女、洗衣婦的歡聲笑語。彼時形成的風俗:酸菜、青菜從不在家中切,用筲箕盛了端到江邊,邊切邊淘洗干凈。傍晚切下的菜可供第二天一整天的食用。這承載一河岸的欣喜和歡樂,是苦中的樂,是勞動過后的樂,是人們生活中尋求到的自得其樂,也即是有人嘲諷的“窮歡喜”。
真是越窮越歡喜,雖然窮得吃不飽肚子穿不上華衣,但能夠活著就能夠歡喜。
馬寅木,女,回族,1971年出生于四川省閬中市。有小說、散文、詩歌散見于多種報刊。出版有詩歌集《一地月光》、散文集《在路上》。系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