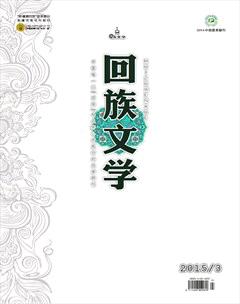在瀾滄江下游
化的同時有一種貼近的溫度感。
確切地說,我已經進入了湄公河流域。瀾滄江從云南西雙版納州勐臘縣南臘河口出境后就開始被稱為湄公河,此后,流經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最后從越南的胡志明市奔向太平洋。
清邁怎么看都像一座花園,目及之處,皆為繁復的花草樹木。古城不大,卻聚集了眾多的名勝古跡,距最北部的首府清萊只有一百六十多公里。湄公河從古城的東邊緩緩流過,把老撾和泰國隔開。在湄公河與洛克河交匯的轉彎地帶,形成了一個三角帶,就是有名的“金三角”區域。
我選擇住在DangtaWan飯店,這里離夜市和古城都較近,無論吃喝還是采訪都很方便。首先花了二百泰銖在海鮮大排檔解決了肚子問題,然后便在酒店沉沉睡去。我確實很累。
晚上,到夜市轉悠。買了一大堆工藝品:蟒皮的二胡,琴身完全用油黑發亮的花梨木制成,柚木制成的牛鈴,各式各樣的手鐲、圍巾。這些東西全是手工制作,不僅質量上乘,且價格十分便宜。
在一個炎熱的下午,我去了馬輝先生的家里。馬輝先生家的房子坐落在熱帶茂密的樹蔭里,周圍用柵欄圍成了一圈好看的院子,院子里種著梔子和藍靛。屋子寬大而舒適,地板和家具都是用油亮的柚木制成,莊重華麗。客廳的墻上掛著一幅麥加天房的純手工壁掛,昭示著這是一個穆斯林家庭。馬先生祖籍云南巍山,已是第六代華人的他,依舊操一口純正的云南腔。
稍后,馬先生驅車三十多公里,帶我去了一個村落。這個村七十多戶人家祖籍全部是云南,從耄耋老人到剛會說話的孩子,全都能夠說一口地道的云南話。走進去,熟悉的鄉音,熟悉的場景,儼然回到了云南。
抬頭看看,盡管陽光有些泛濫,但那些布滿山谷的綠色,依然那么寧靜,仿佛從來也沒有從夢中醒來過一樣。
村子旁邊是一座木質結構的清真寺,規模不大,建筑也略顯簡單,我們沒有進去,只在那微開的門前駐足了一會兒。馬先生說,這里進寺的以年輕人居多。
再往前走,就到了小學校,有一個班的孩子正在上課,黑板上寫的是漢字。在學校辦公室,我見到了那位來自云南的校長納先生。據納先生介紹,學校是村民們自籌資金修建的,五十多個孩子分為兩個班上課,教師加上校長一共有四位,除了校長,其他三位老師都是由清邁聘來,孩子們在學校主要學習漢語,也學一點阿文,為的是讓孩子們多一些謀生的技能。
我們來到村中一個馬姓的老鄉家里,得知我來自云南,很多老鄉聞訊聚攏來,問長問短。有個八十多歲的老奶奶,說著說著就拉著我的手哭了起來。
一般說來,泰國南方的穆斯林主要以馬來人為主,而泰國北方的穆斯林祖籍大都為華裔,其中有為數不少的云南人。他們因各種各樣的原因,從遙遠的云南來到這異國他鄉,帶來了先進的農耕技術和貿易,堅毅與吃苦造就了許多穆斯林巨商。他們不僅建蓋清真寺,還興辦學校、醫院,對當地教育和經濟建設做出了難以想象的貢獻。
我拍了一組照片,以視覺的方式記錄下那些我尊重的人。他們是:那個正瞇縫著眼睛看太陽的孩子小明,那個目光深邃安詳的老人王云仁以及他那個滿臉溝壑縱橫依然面帶笑容的妻子,還有,那些有些局促的男人和女人……
現在,他們每個人的手里都有了至少一張我拍的照片,我希望他們能從中看到我深深的敬意。那時候我想,信仰是什么呢?信仰就是一種力量,一種長生不滅的生命。當一種東西成為一種信念,并自發成為你生活
的一部分的時候,無論對自己還是對生活,都是一種鼓勵。
離這個村莊不遠,有一座佛寺,鐘聲從里面很隆重地傳出、鋪開,然后又慢慢地從眼前的樹梢掠過去。熱帶的溪流潺潺流下,我們涉水而過。
等待著馬先生幫我聯系去清萊的車,我要繼續沿湄公河而下。
順便又去看了珠寶店。那是一座黃色的法式大房子,店主馬汝華老先生今年六十八歲了,祖籍云南騰沖,家族幾代人一直以珠寶生意為業。也許是人到晚年更喜歡憶舊,更容易生出思鄉情結,從見到我的那一刻起,老先生就不斷地在回憶,回憶曾經有過的奮斗與汗水,回憶曾經有過的輝煌與失落。在老先生的敘述中,猶如膠片的顯影,云南回民跨境貿易的歷史脈絡逐漸清晰起來。
事實上,云南回民進入東南亞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元代,明末清初進入繁榮時期。滇西是云南回民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因此,進入東南亞的馬幫也較多。據英國人安德森《滇西探險記》記載,當時進入緬甸的云南商人幾乎全部是騰沖回民,他們帶著云南的茶、絲出去,換取緬甸的寶石和棉花,把生意一直做到西藏和兩廣、江浙地區。清朝初年,云南各地的回民更是普遍興起了到東南亞的馬幫貿易,線路也從傳統的滇西擴展到多條。滇東南玉溪、通海、紅河等地的回民開辟了從峨山—墨江—西雙版納進入緬甸的貿易路線。這片地域曾是當時中國最可怕的地區,猛獸出沒,土匪橫行,原始森林,蠻煙瘴氣,很多人因此而失去了生命。可以說,云南回民創造了馬幫文化和中國貿易史上的奇跡。
生命中的細微之處無所不在,還有什么能比歷史告訴我們的更多?很長一段時間,我的眼前都晃動著馬幫艱難跋涉的身影,心里對先民們充滿了深深的敬意。
馬汝華老先生給我看了一段短片。片中顯示,柬埔寨的紅寶石、藍寶石和黃白寶石分別產于緊靠泰國的珠山、拉達那基里省和磅通省。挖寶石礦的人,全部是當地貧苦的柬埔寨人。看著那璀璨的寶石被人從地球的深處挖掘出來,就仿佛把人的心臟摘除一樣。無數的手撫摩著,掂量著,傳遞著,深藏著,甚至是膜拜著。
人們顯然忘記了它曾經黑暗的歷史。
畫面上的人們不斷用錘子砸向巖石的同一位置,幾天,甚至是幾個月的努力,才能使某些地方呈現花紋,并長久地保持不變。他們日復一日沒完沒了地挖著寶石的身影讓人相信,所謂的滴水穿石,也不過如此。我抓起一塊沉甸甸的毛石握在手上,有一種生硬的金屬質感。
離開泰國,我又去了柬埔寨。
從金邊沿二號路直接去了僻遠的巴地縣,柬埔寨的占族穆斯林大部分居住在那里,以養牛著名。長時間的戰亂使柬埔寨比想象中荒涼,村莊與村莊之間有著大片無名的荒地,同熱帶大多數的民居一樣,占族人的房屋也是用木板建成的,上面飄著搖搖晃晃的炊煙,每餐的食物也很簡單,米飯加上少量拌了調料的碎肉。貧窮,但安詳。在這個旅游者罕至的地方,人們好奇地看著我,偶爾說一兩句當地的語言。我從一個女子家里挑了三只做工精美的麻編手提袋,然后掏出一些錢攤開,讓她自己取。我們不懂彼此的語言。女子有些遲疑地看看我,然后伸手取了一美元。“One?dollar?”我問。便宜得于心不忍,我依然攤著手。女子使勁搖搖頭走開了,看得出,對于索取,她是很羞澀的。
望著女子遠去的背影,我想到了時間以及地理。占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一千五百多年前就在今天越南的中西部地區建立了
輝煌的占婆王國,信奉印度教。大約十八世紀,占婆王國被北越王朝所滅,大批占族人向湄公河三角洲遷徙并皈依了伊斯蘭教,今天的柬埔寨占族人即是他們的后裔。當我坐在他們中間時,我不由得思索一個又一個現實的問題:如果沒有信仰,亡國以后的占族人今天會是怎樣?毫無疑問,不是每個有信仰的人都有明確的目的,有的人甚至可以說是盲目的,但他們希望今生后世對自己對他人能夠有所改變是肯定的。同時,因了對生存積極有致的信念,他們長久地頑強地保持了心中的那份信仰,即便是身處亂世,也沒有影響他們向著認定的心靈更深處邁進。
又折回首都金邊。
這是一個位于湄公河與洞里薩湖之間的三角洲地帶,一個表面平靜,實際上比想象中貧困迷亂的地區。到達前我被告知,要隨身攜帶應急電話,不要帶護照,不要隨便逛街,即使白天也不要進入小街小巷,以防不測和被搶。也是,長期的戰亂不僅使這個國家幾乎沒有發展經濟的機會,而且喪失了大量人口,法國學者拉古特把紅色高棉那段歷史稱為“自我滅絕的屠殺”。如今,在金邊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當年被地雷奪去雙腿的殘疾人。
還是去了幾個地方。皇宮、國家博物館、獨立紀念碑、紅色高棉殺人場,以及城邊上的湄公河。
在塔山前的廣場上,幾個年幼的孩子和幾個被地雷炸掉雙腿的人正在賣藝。窮人太多。沒有房子,沒有職業。除了乞討,只能無所事事地待著。因此,眾多的乞丐成了這個國家的又一景觀。
夜晚的金邊沒有路燈,主要街道只有如潮的汽車和摩托車燈光。在這座工業幾乎凋零的城市,超市貨架上擺的幾乎都是外國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幾乎看不見出租車和公交車,取而代之的是滿街亂跑的電動三輪“嘟嘟”車,一輛摩托車上坐著五六個人也是常見的景觀。對于金邊市民來說,持槍、劫匪、垃圾、娼妓、毒品已是司空見慣。那種黑夜里的困窘生活,想也想得出來。
真有那么可怕嗎?
在隨后的幾天里,我的猜想很快得到了證實,只要隨手翻翻報紙,暴力、色情、搶劫等新聞占據整個版面的情況屢見不鮮。
好在大多數的柬埔寨人都比較君子,心態平和友善,大街上即使發生了交通事故也不會爭吵打鬧,一般只是將車子停在一邊,然后再平和地交涉。
回到昆明,固有的生活周而復始,卻似乎又瞬息萬變。
身體、心理、精神和思維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悸顫。腳步收回來了,眼光卻一直還在外面。
很多的人和事,再也無法遺忘。
(節選自葉多多散文集《邊地書》,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