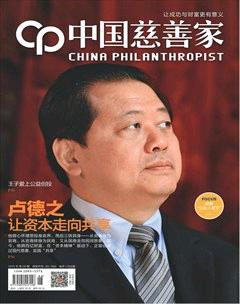阿米爾?佩茨克: 新一代慈善家更注重社會影響力
徐會壇 章偉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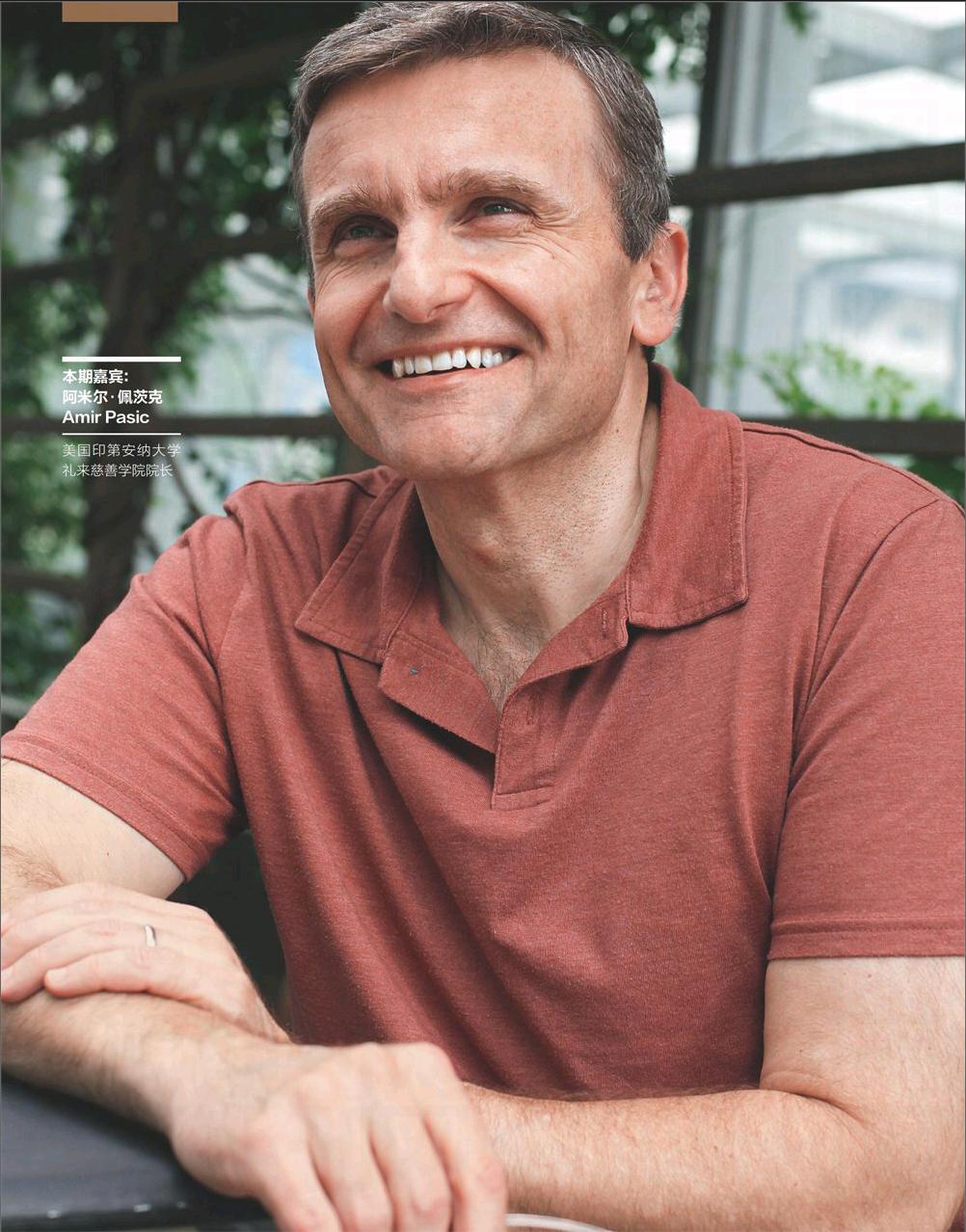
在數字化的世界中,一切都在加速發展,慈善領域也不例外
“新一代的慈善家更注重社會影響力”
《中國慈善家》:到目前為止,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捐贈已超過10億美元。他才31歲,而他的前輩如比爾·蓋茨(Bill Gates)、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以及更早前的洛克菲勒(Rockefeller)、卡耐基(Carnegie)等都是人生的后半階段才這么做。你如何看待這種不同? 阿米爾·佩茨克:這種變化在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都很明顯。像馬云這樣通過互聯網和電子商務迅速積累了財富的慈善家不在少數。在美國,我們發現,一些像馬克·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普莉希拉·陳(Priscilla Chan)這樣的年輕人都在二十多、三十多歲的時候就做出了大額捐贈。你也可以看到谷歌的兩位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都非常年輕,但他們都在很認真地做一些創新的慈善。在數字化的世界中,一切都在加速發展,新人不斷涌現,這也反映在慈善領域中。 《中國慈善家》:從洛克菲勒、卡耐基,到蓋茨、巴菲特,再到扎克伯格等人,美國不同時代的富豪的慈善行為、慈善理念有什么明顯的不同? 阿米爾·佩茨克:在對新一代高凈值個人的采訪中,我們發現,他們做慈善的態度和動機都有所改變。新一代的慈善家更注重社會影響力,他們想知道自己的捐贈究竟帶來了哪些切實的改變。過去,前幾代的慈善家,回饋社區是一種應盡的義務。 我們還觀察到一個長期的趨勢,那就是對宗教的捐贈在減少。和三十年前相比,現在美國對宗教的捐贈變少了。其他領域,例如環境,則越來越成為人們捐贈的重點。 《中國慈善家》:對宗教的捐贈在減少,是不是說明信仰作為一種慈善的動機,其影響力在下降? 阿米爾·佩茨克:在美國,65%的捐贈流向宗教之外。宗教仍然是獲得捐贈最多的,但是,信仰(Faith)作為捐贈的動力之一同樣存在于宗教之外。有些人相信科學有助于解決社會問題,因此資助科學發展。但是,我們并沒有科學的證據可以證明科學確實能夠解決我們遇到的社會問題,是嗎?所以,才會有“相信科學”(Have faith in science)一說。 我認為,信仰—不一定是“宗教信仰”—始終是做出大額捐贈的重要基礎。有人會愿意把錢捐給一流的大學,資助它們的教育和科研,就是因為他們相信這能夠造福人類。 《中國慈善家》:卡內基的那句“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堪稱美國富豪的慈善啟蒙名言。這句話對于新生代慈善家而言依然有效嗎?有人認為這是一種道德綁架,你怎么看? 阿米爾·佩茨克:是的,卡內基說的這句話可以被看作是命令式的,這樣自然會引起人們的反感。但是,它也可以被看作一次對話的開始、一個思考:我是怎樣獲得今天的財富的,我和我的家人需要用到其中的多少,超出需要的那些該用于什么目的?這樣看的話,卡內基作為他那個時代最富有的人,其實是在很認真地思考財富的價值,他看到了自己對社會的責任,他認為是社會讓他變得那么富有,如果他不能有效地把這些財富用于造福社會,對他將是一種恥辱。所以,他其實是在挑戰自己以及和他一樣獲得了巨額財富的人。
很多人覺得卡內基的這句話很有說服力,并且很欽佩他的以身作則,以他為榜樣。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發起了“捐贈承諾”行動(The Giving Pledge),呼吁全世界的有錢人在去世前捐出一半以上的財富。我認為,對于今天所有的富豪們而言,如何運用財富,這是一個挑戰。當然,你也有權利說這是我自己的事,與別人無關。 《中國慈善家》:那么具體到慈善的做法上,據你觀察,新生代慈善家有哪些創新之處? 阿米爾·佩茨克:在慈善創新和成效評估等方面都出現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實踐。人們正在嘗試聯結市場的力量和慷慨的力量。也有一些人在用新的流行語來描述由來已久的做法。早期的一些慈善家,像洛克菲勒和卡內基,他們也都想改變世界,只不過是他們沒有用現在的一些語言去表述。 《中國慈善家》:你所說的“嘗試聯結市場的力量和慷慨的力量”,指的是社會企業和社會投資的出現嗎? 阿米爾·佩茨克:是的,圍繞著社會企業和社會投資的概念出現了很多非常棒的、創意十足的能量。例如,有些非營利機構依靠捐贈來提供服務,他們不得不每年都去募捐,人們就想,能不能有一種新的機制,可以讓這些機構不用非得籌款就能夠服務窮人、殘疾人、饑餓的人呢?
這是很好的愿望,但是在有些情況下卻難以實現。也許不同的階段可以由不同的部門介入以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例如,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用社會投資的辦法創立了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接著有許多學術研究指出微金融的市場價值,一開始人們并不知道這里面蘊藏著商機,直到越來越多的非營利機構參與其中。再接著,許多營利性的機構進入,這時候非營利機構的角色就可能發生轉變甚至完全退出這個領域。換言之,非營利機構可以創造條件以生成市場,然后離開,讓營利性機構進來。 “美國提出了一些新的法律定義,例如‘益公司”
《中國慈善家》:你剛才提到的美國的一些慈善理念、模式的轉變在中國也有所體現,例如,現在有一些公益人士、慈善家放棄運作或投資NGO,轉向社會企業,但他們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的轉型并不順利。在這一點上,美國的社會企業和社會投資的發展可以提供哪些經驗? 阿米爾·佩茨克:我的感覺是,中國適應科技和新事物的速度太快了。而且,這里還沒有確立像美國那樣非常明確的非營利機構監管機制,這或許能給創新提供不可多得的機遇。 但是,無論是對于企業還是非營利機構,法律都很重要,因為在法律之下,非營利機構和商業機構的界限是很清晰的。在清晰的法律框架中,你能夠明確地知道能夠做什么、能夠期待什么。對于企業家而言,法律法規不明晰反而可能會是障礙。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在商業還是社會領域,他們不會進行投資,不管是商業投資還是慈善投資,因為他們不知道法律法規會如何改變。 《中國慈善家》:在推動美國社會企業和社會投資的發展方面,美國是不是也像英國那樣出臺了一些創新的法律法規? 阿米爾·佩茨克:美國提出了一些新的法律定義,例如“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如果你創辦了一個“益公司”,你可以營利,但是在法律上,你是以追求社會效益為目標的,需要向社會公開匯報你的社會影響力和解釋你所扮演的社會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