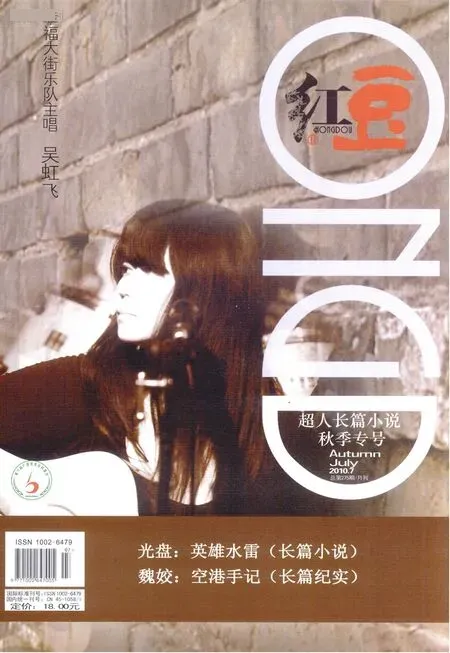遮蔽
朱以撒,男,1953年生,福建泉州人。現(xiàn)為福建師范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福建省書法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學(xué)術(shù)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在國內(nèi)報刊發(fā)表大量散文、隨筆作品。出版散文集《古典幽夢》《腕下消息》等多部。作品入選眾多選本并獲獎。書法作品廣有流傳和影響。
車子在北方這個小縣城邊緣奔馳,和夏日里所見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不同。路邊密集且舒展的楊樹,已經(jīng)退去所有的綠意,一葉不掛,把楊樹背后的村子暴露出來。枝頭上的黝黑空巢一下子變得醒目高懸,它的方位、形制在目擊時被確定無遺。一年里頭,這些村子、這些空巢都被碧綠的葉片遮擋著,讓人從旁邊走過,渾然無覺。葉片是漸漸長大的,初始有如星點,而后每一日伸張,形成一張綠色的屏障,幾里,幾十里,把人們窺視的好奇心擋在外邊。夏日里經(jīng)過,我揣度連成一道的楊樹背后,藏著奇妙的玄機,會是很空曠、深邃,根本不會想到是一些實在的村子,每日雞飛狗咬的,充滿了世俗的氣味。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都是有所遮蔽的,或是自然之物,或是人工設(shè)置,總之不讓人一眼洞穿。如果沒有冬日的到來,樹葉掉得這么徹底,村子里的真相永遠(yuǎn)看不到,里邊的人安然地過著尋常的日子。隨著秋日以來一片又一片綠葉轉(zhuǎn)黃、枯焦落下,空白越來越明顯。誰都沒有辦法彌補這些空白處——遮蔽不見了,一個個村子讓人看到了。只有等待這個漫長的冬季過去,春日緩緩到來,葉片由小及大,他們村子里的秘密才又重新得到了守護。
在很多時候,每一個人都喜歡有所保留,不愿罄露。記得我第一次見到尼龍蚊帳時,心里大吃一驚——它和舊日的麻蚊帳最大的不同就是薄且透明,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邊睡覺的那個人的身體。而麻蚊帳讓人看不清,睡起來就特別自在。這和一個人著不著衣裳是一樣的,由于有衣裳的遮蔽,人們的心理、生理都會更加坦然。實在的墻體是一個家庭的遮蔽——目力再好的人也無法穿透一堵薄薄的墻。如果一個個家庭的墻都是透明的,那么在這種透明中,每一個家庭成員都會生出許多的不安。夜幕是白日的遮蔽,夜幕拉開的時候,目力逐漸受到挑戰(zhàn),最終宣告目力的失敗,在漆黑中無能為力。人們不得不動用了火,即便一燈如豆,也使人能夠清晰地看到眼前的人,看到他的眉目神情。人們在追求光明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光電專家應(yīng)運而生,有能力把暗夜的迷霧驅(qū)散,使人們不再有日落而息的心態(tài)。光亮越發(fā)達的城市,遮蔽消失了,許多人要在這些光亮的場域里,勞作或者娛樂。只有那些循自然之道的人,才可能探究夜色獨有的情調(diào)——柔和的、朦朧的,隔紗窺月的,霧里看花的,使置身其中的人的心理起了微妙的變化。就像暗夜里在荒野上趕路的人,恍恍惚惚疑真疑幻,那些草木搖曳之狀,鳥鳴蟲唧之聲,都被無限地放大了,朝著詭異的方向。于是心弦收緊腳下生風(fēng),深淺不計,慌亂中踢飛了石塊,忽忽過了茅店社林,過了亂墳崗子,看到村頭水電站昏黃的燈光。此時背上已經(jīng)沁出了汗水。驚悸之美——事后我回味不已,是因為這些暗夜、暗影,使我品咂了清明白日所沒有的快感。
華滋的水土,總是有相續(xù)不斷的水果推出,讓這個南方城市的人們大飽口福。動作熟練的人們,撬開它們的外殼進入實質(zhì),感受內(nèi)部的甜蜜和黏稠。對于一些形制碩大之物——西瓜、榴蓮、菠蘿、椰子,人們必須在購買前判斷出內(nèi)部的質(zhì)量,然后決定取舍。西瓜是尋常之物,人們用左手托起,放在耳邊,用右手拍拍,或者指頭彈彈,傾聽內(nèi)部的回音,判斷出生熟程度。對于榴蓮就不能如此,這種植物的前世肯定遭受大劫,以至于它的后代對這個世界有著強烈的抵御意識——渾身是刺,摸不得拍不得,無從考察內(nèi)部的真實,只能憑運氣,把它綁回家再見分曉。就是皮層很薄的石榴,如果沒有讓它咧開嘴,誰也想不到里邊隱藏著如此多的晶瑩顆粒,閃動著珠玉輝光。這使我第一次見到時驚喜異常——一個孩童全然不懂,一枚外表不起眼的石榴,它的內(nèi)部會是如此精彩,這些珠玉有秩序地堆壘在一道,任何力量把它們解開了,都無法還原到早先的那種鑲嵌狀。這是我對一枚水果最初始的感覺——內(nèi)部的默契、神秘,不可究詰。由此可以延伸到任何一種果實,在或厚或薄的外表下,有著各自的精彩——不同的汁液,不同的氣味,沒有一種天生天養(yǎng)的果實會混同在一起。這使我在遭逢一枚從未見過的果實時,都充滿了對它內(nèi)部的好奇沖動。我不會急于打開這些陌生的形態(tài),而是揣摩再三。往往在它們內(nèi)部豁然開朗時,才知道我的猜度往往錯了。
多水的南方,水把許多物體浸泡在里邊,讓人看不到深邃處的動靜。我在海邊行走,感到巨大液體內(nèi)涌動著無定的力量——沒有什么可以阻止它們的進退,如此的柔軟,又如此的堅韌,讓每一位進入水中的人,心與水一樣,不停地蕩漾。一些海邊居民在退潮時用镢頭在淤泥中刨出一堆堆木塊,曬干了做劈柴使。時日久了讓人感到蹊蹺,覺得這些木塊應(yīng)該是一艘船的某個部位,只是已久不在波濤上行走,而是深藏于波濤之下了。此后費很大氣力,這艘宋代古船終于從黑暗處起身,使人看到粗壯的錨、漫長的桅桿、恢宏的船體。政府為它建了一個巨大的館,把它供在里邊。在淤泥的覆蓋下,還有多少沉船和沉船里的寶貝,永遠(yuǎn)見不到天日?并不是每一個事物都可能從暗中走出,被陽光鋪滿。在我認(rèn)識的人中,金先生是個沉淪的人,他的家庭成分、個人身份,意味著連報考大學(xué)的機會也沒有。他只有不斷地買書,想象著要像大學(xué)生那般擁有很多的書。高考恢復(fù)后我上了大學(xué),曾經(jīng)遇到金先生,他很細(xì)致地向我打聽大學(xué)課程的方方面面,魏晉文學(xué)史要講幾節(jié)課呢?元代的說經(jīng)話本、諸宮調(diào)可能你們都很陌生吧,能讀到多少呢?明代傳奇讀過了,是不是明雜劇就簡略許多?我把自己知道的說給他聽——一位長期徘徊在大學(xué)門外的人對于大學(xué)里的動靜是很感興趣的,千百次地想象著它的美好。那時金先生已經(jīng)五十多歲了,覺得自己就是泥淖中的曳尾龜,渾身泥澤,永遠(yuǎn)爬不出來。他每日褲管一腿高一腿低地在雜亂的工地上奔走,監(jiān)督著民工們的施工進度。這個年齡,繁忙的工作和繁重的家庭生活已經(jīng)使他心力交瘁。從外表看,尋常日子的辛苦,已使他眉目低斂步履匆忙,似乎對任何人事都沒有瞻顧的心思。只是,一丁點兒對于大學(xué)的言說都讓他敏感、警覺,豎起耳朵聽,并且會追問不停。他放光的雙目終了黯淡下來。
四十年前,有一位女知青來生產(chǎn)隊找我。我們在村頭的樟樹下,為著一家縣辦工廠招工而興奮交談,直到暮靄下來,兩個人的臉都有些看不清了才分開。這些稱為知青的人,在一個知青點生活、勞作,彼此文化水平相距未遠(yuǎn),交流起來聲氣相投,互為知音。十年八年過去,知青點曲終人散,有的當(dāng)了兵,有的進了工廠,有的又回到舊日的城市開始新的生活。我和知青點的所有人不同,考上大學(xué),后來成了一名大學(xué)教師。生活的維度朝著專業(yè)的方向發(fā)展,單槍匹馬,自得其樂,漸漸深入下去。我身邊都是一些各有專長的同事,各懷隋璧,各騁其能。我們交談的,也就大多是紙本上的風(fēng)雅了。那些曾經(jīng)辛勞的鄉(xiāng)野生活,漸漸地淡薄甚至忘卻了。我在家鄉(xiāng)一條街的拐彎處遇上她,當(dāng)時都感到驚奇,覺得應(yīng)該說很多話。在對于各自近況都打聽之后,慢慢就覺得言說的話題相差許多了,彼此已是熟悉的陌生人。正如《一代宗師》里的那個老潘對葉問說:“其實小姐她不知你,你不知她。”畢竟相隔太久,發(fā)展的方向朝著相異的方向延伸,關(guān)注點全然沒有一點瓜葛,不知何所云,云何所。我發(fā)現(xiàn)如此漫長的時日過去,她的文化水準(zhǔn)還停留在當(dāng)時階段,小學(xué)生的表達。她對學(xué)習(xí)毫無興趣,覺得庸常日子足以應(yīng)對。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措詞,有意帶一些知青時的粗魯、粗糙的表達方式,以免讓她察覺出我言說中的書生氣味。是什么讓我們不能像舊日那般暢快地談吐?我只能說是時日,時日的風(fēng)塵把我們談吐的通道遮蔽了,使我無法回到舊日的我,連同那些舊日的表達。
父親八十多歲時,又重拾了年輕時的書法愛好,每日寫上一段時間,作為消遣。一個人老了,相跟著也就眼花了,手抖了。格子折好了卻看不清楚,寫得忽大忽小,時緊時松。父親喜歡寫多字?jǐn)?shù)詩詞,以此來挑戰(zhàn)自己持久的耐力。百十個字下來,氣力費盡,忽然一滴口水控制不住,忽地落下,使字跡上的墨汁洇化成團。一個人年齡大起來,連使喚一桿輕柔的羊毫都那么力不從心。青年時的父親神情俊朗動作敏捷,一幅字寫下來,干凈利落。如今,這個稱為“病”的幽靈,潛伏在他身體內(nèi)部,讓他感到渾身上下的不適,有時甚至僵硬地釘在一處,動彈不得。病趕不走,還在體內(nèi)越發(fā)坐大了。這樣就使一個人的形態(tài)、神態(tài)不似本來,而扭轉(zhuǎn)成另一種樣子。病很像風(fēng),風(fēng)是看不到的,但是人們看到了緊張搖曳的草木,聽到了潮水急促地拍岸的聲響,就知道風(fēng)到了。所謂的病體就是這樣,肢體語言本來是正常的,如同我們的正常言說,而后來不正常了,顯得古怪、滑稽了,讓人看了憐憫——不正常的力量太大,就把正常遮蔽。一個人終其一生,順順暢暢無疾而終的畢竟鮮有,更多的為一些病癥糾纏,智力上的、體力上的,難以擺脫,只能在生存過程中極力抗?fàn)帯D赣H最終是全然不知這個世界上的人事的——一個往昔思路清晰的人如此這般,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因為那些使之轉(zhuǎn)變的因素我如何都看不到,只是看著母親一年年地衰退下去,無法阻擋。父親如今還是堅持自己理財,他的記憶漸漸有些退化,但是拒絕妹妹的幫助。他認(rèn)為一個人如果連管理自己的錢都做不了,那真是廢了。這些錢代表一些數(shù)字,父親根據(jù)這些數(shù)字進行分配,飲食起居所用、人情世故所用,還有心血來潮時所用。數(shù)字的分配、增減是一場智力上的游戲,有助于他大腦的磨煉。大筆的錢、小筆的錢,在加減乘除的過程中使自己的思維理性起來,不敢迷糊。過年時父親的錢會多一些,子女給他一些錢,他塞入口袋里,或隨手?jǐn)R哪里,有時就找不到了,有時就被保姆抽走了——盡管有證據(jù)證明這些不足,父親還是要自己理財,認(rèn)為自己完全有這個能力。我覺得還是隨父親去,讓他在數(shù)字的計算中感到自信——這個小城的人情禮數(shù)特別多,父親那些算對了的、或者算錯了的數(shù)字,進進出出,會讓他更真切地琢磨、追究,親人不要因為好意遮蔽了他的這種追求傾向。
最近我獲得一株香樟樹。當(dāng)時動用了吊車還有七八個工人,才把它挪到院子右側(cè)的角落上。而它的左側(cè)是一株樸樹,我想讓它們相互映襯,達到平衡。這株香樟樹已有幾次的挪移經(jīng)歷,每一次挪移,為了成活,總是要鋸去一些枝杈,使它生長的狀態(tài)全然不是天生的那種,而是荒腔走板了。到了我這里算是塵埃落定。一個人和一株流浪的樹在一起也是事先沒有想到的,我希望此后它就兀立不動,從此漸漸恢復(fù)元氣,枝葉舒展。
總是有一層皮表,包裹著人和物,使內(nèi)部在暗中存在,給人們探究時設(shè)置了一些難度。往往是人的探魅欲望,執(zhí)著地要去打開,得出一個真切的解釋才罷休。其實,這個世界最吸引人的,還是那些恍兮惚惚,惚兮恍兮的部分,它讓我們有許多糾結(jié),不忍舍去。
責(zé)任編輯 盧悅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