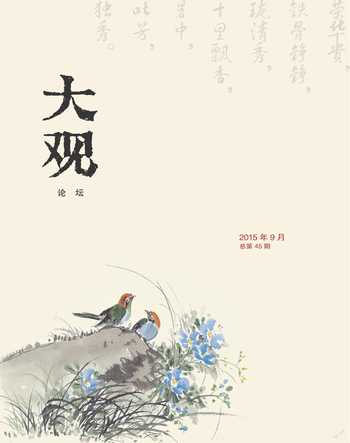師陀《果園城記》的語言特色分析
摘要:在《果園城記》中,師陀塑造出了許多經典的人物形象,并通過恰當的敘事手法將全文的情感基調統一,除了這些特點之外,《果園城記》的語言特色也十分的突出。本文在闡述人物形象及情感基調的基礎上,分析了《果園城記》中的語言特色,將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完美的展示出來。
關鍵詞:《果園城記》;師陀;語言特色
20世紀30、40年代,在中國現代文壇上有過很多作家,在這些作家中,師陀的文名是比較高的。《果園城記》為短篇小說集,這是師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歷時八年創作而成。《果園城記》誕生之后,在評論界受到了廣泛的關注,之所以會引人注意,是因為《果園城記》具有獨特的風格,尤其是在語言特色上,師陀將其不與他人相同的寫法表現的淋漓盡致。
一、師陀及《果園城記》
師陀的原名叫王長簡,師陀是他的筆名,還有另一個筆名叫蘆焚,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自覺追求文學獨創性的作家。在最初,師陀就給自己定下了一個規矩:絕不就正于前輩,帶著這個信念,師陀進行了一番艱苦的努力,終于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寫作風格。1937年,天津《大公報》的文藝獎金得主有三位,曹禺、何其芳都是其得主,而第三位得主就是師陀,不過,這項成就并沒有讓師陀在文壇上大放光彩,真正讓他享有盛譽的是短篇小說集《果園城記》,《果園城記》一經出版,就引起了評論界的廣泛關注,有的評論者認為,通過《果園城記》,師陀的創作走向了成熟。
《果園城記》于1946年出版,而早在1938年,師陀就開始了這篇小說的創作,經過斷斷續續的八年時間,師陀終于完成了小說的創作。小說的主人公為知識分子馬叔敖,離開家鄉七年后再次返回家鄉,他的家鄉為一座小城,通過對小城的審視與打量,將小城中的物是人非、衰落境況清楚的描寫出來。在師陀的筆下,果園城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地方,擁有著寧靜平和的氛圍、如畫一般的風景,然而果園城中的人們卻大多數悲劇命運,通過這種明顯的對比,讓讀者對《果園城記》印象深刻。
二、《果園城記》中的人物形象
(一)游走在愛情邊緣的女性
在現代作家的筆下,描繪出了無數種女性形象,女性的命運一直是作家們不斷探討的問題,尤其是五四運動之后,提倡女性個性解放,在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下,更是對女性命運進行了深入的探究。師陀就是“五四”時期的作家,在他的《果園城記》中,描繪許多悲苦的女性形象,她們都是在傳統禮教的束縛下長大的,自甘順從,然而,在這座小小的果園城中,無論是何種類型的女性,最終的結局都是走向毀滅。在《桃紅》中,師陀塑造了素姑的形象,她是一位溫柔嫻靜的小姐,和寡婦媽媽相依為命,對于愛情,素姑有著無限的憧憬及向往,從十二歲起,素姑就開始為自己縫繡衣物,現在素姑已經二十九歲,依然在縫繡衣物,她所攢下的衣物已經足夠她穿三十年。素姑之所以二十九歲還沒有出嫁,都是因為母親在年輕時受過傷害,母親害怕素姑也受到和自己相同的傷害,所以讓素姑獨守空閨。或許,這種獨守空閨還會持續下去,時間足以摧毀一切,最終作者以“一顆淚珠從她的臉上滾下來,接著又是一顆”來寫出了素姑的悲劇命運。
(二)孤獨不得志的知識者
在很多的現代小說作品中,都塑造了知識分子的形象,比如魯迅在《吶喊》中塑造的知識分子形象,始終為中國民主革命奮斗著。而在師陀的果園城中,也塑造了很多的知識分子形象,他們都在學堂里讀過書,努力成為有志青年的年輕人,但是對于獨立獨行、抗命不尊的年輕人,果園城是予以排斥的,并且被排斥過的年強人經過歲月的洗禮之后,再無當初的志氣。在《傲骨》中,傲骨是一位典型的知識分子,他掌握了很多先進的理論和知識,師范學校畢業之后應聘到縣立中學教書,在縣立中學中,傲骨不與其他無知無賴的同事同流合污,這樣一來,傲骨就顯得格格不入,最終落得了在監獄中呆半年的下場,由此,傲骨變得憤世嫉俗,在尋找共產黨未果后回到了果園城,但是果園城的人們并不接受他的先進理論,自此,傲骨就成為了“牢騷,沒有完的牢騷”的憤世家。
(三)卑微堅忍的小人物
在果園城中,生活著許許多多的小人物,他們每天都按照傳統的生活方式生活著,是社會最底層的人,雖然這些小人物很卑微,但是他們都在堅忍的活著。在《一吻》中有一個錫匠,經過時代的變遷,錫匠成為了要飯的人,在十字街的轉角處跪著乞討,錫匠的徒弟也由勇敢追求愛情的小伙子變為為了生活終日奔波的車夫。通過描寫這些小人物的悲苦生活,引發了人們的深思。師陀在對小人物自在自為的生命狀態進行凝視的過程中,流露出一種焦灼與憂傷的感情。這些小人物全部都命運不濟,但是又自甘忍受,通過對這些小人物的描述與反思,隱現著作者內心深處的歷史、道德與審美之間的鄉土悖論。師陀的敘事方式中始終都包含著詩意的情感,他通過這種情感展現出了果園城中各個人的悲慘命運,這些人都逃不開最終悲慘的結局,而這些人的結局也正是對時代與社會悲劇的反應。
三、《果園城記》中的情感基調
(一)對故鄉眷戀與厭惡并存的矛盾情感
師陀居住在上海,不過他的祖籍是河南,對于自己的家鄉,師陀具有濃濃的鄉情,盡管故鄉的小城是那樣的破舊、原始,但是這個記憶深處的小城已經在他心中生根發芽。但是這個落后、閉塞的小城又讓他感到厭惡,這種情感方面的矛盾一直都在他的文章中始終貫穿。師陀的果園城已經歷盡滄桑,經過時間的洗禮,現在的果園城已經如同一個老人一樣,滿臉皺紋、衣衫襤褸。在師陀的心中,是無比懷念自己的家鄉的,但是又是對家鄉有著厭惡的,這在《巨人》中就很好的體現了出來,“我不喜歡我的家鄉,可是懷念著那廣大的原野。”師陀同情果園城中的善良小人物,同情為了自己準備了豐厚嫁妝而又待字閨中的素姑,同情心無大志而與人無爭的地主葛天民等。果園城在不斷的變遷中,不論是欺壓別人的還是被被人欺壓的,都逃不過時間與宿命,在經歷了漫長的封建統治之后進入到了風燭殘年,已經逐漸呈現出了頹敗的趨勢。
(二)憂郁的情感與明快的寫景指對比
師陀所描寫的果園城,擁有美麗的景色,但是果園城是一座小城,絕美的景色更加襯托除了小城凄涼的氛圍,悲涼的景色加上可悲的命運,使人物的悲劇色彩、時代的黑暗程度更甚。在師陀的筆下,果園城這座小城可以說是有生命、有性格的,以至于在離開家鄉多年之后還能回到家鄉,而時隔多年,果園城的景色依舊,似乎是從來沒有改變過,而正是果園城這種近乎永恒的姿態,凸顯出了生命的無常。在借景寄情上,師陀深知其重要的襯托作用,因此在《果園城記》中大量的運用了該寫作手法,比如在《期待》中,有這樣一段描寫,“在街上,時間更加晚了,照在對面墻上的云霞的反光逐漸淡下去了。一只豬哼哼著在低頭尋覓事物;一個孩子從大街上跑過來;一個賣煤油的盡力敲著木魚。”通過這段描寫,更加突顯出了悲涼,也顯現除了人物命運的可悲。
四、《果園城記》中的語言特色
(一)泛指
在《〈果園城記〉序》中,師陀曾經說過,他有意將小城寫成中國一切小城的代表,因此,在《果園城記》中,多次的出現了“中國的”這個定語,通過這個這個定語,可以發現,師陀并沒有將果園城看做是自己的故鄉,而是當做了中國一切小城的代表,這種寫法在現代文學中并不多。
師陀的故鄉是河南的一個小城,風沙、鹽堿、貧瘠是師陀家鄉所特有的特點,但是這些景色在果園城中是不存在的,而且具有河南代表性的景物、語言也未出現在文中。師陀所描寫出來的果園城有的是青草、白羊,風景秀麗,溫暖中又帶有悲涼的傳說。《果園城記》在地域上的模糊表達,實際上就是泛指,通過這種泛指實現了文本在內涵方面的擴展。
中國的鄉土小說分為兩個派系,一派為鄉土原生態派,其主要的代表為魯迅,還包括騫先艾、許欽文等;另一派為鄉土詩情派,其主要的代表為周作人,還包括沈從文、廢名等。師陀所創作的《果園城記》,并不屬于上述兩個派系中的任何一派,與鄉土原生態派相比缺乏鮮明的地域性,與鄉土詩情派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周作人提出的鄉土文學理論中,在提倡地方色彩的基礎上也包含寫意與想象,例如受到周作人思想影響的廢名所著的《橋》中所描述的史家莊。但是師陀筆下的果園城,雖然也具有撲朔迷離的特征,但是師陀與鄉土詩情派相比,更加注重平凡人生答案的追尋,文中更多的是對命運進行理性的思考。
在《果園城記》中,師陀是將小城作為主人公來創作的,小城所具有的隱喻層面已經遠遠超過了其在寫實層面的意義,成功地為讀者開辟了更加廣闊的想象空間,將作者與讀者并未經歷過的人生情感、體驗等都包含在內。實際上,作者創作《果園城記》的過程可以說是一次在精神上的返回家鄉,無論讀者是什么人,都可以在《果園城記》中探尋到一些自己家鄉的蹤影,感悟到時間的無情、命運的無常以及人的無奈。作者及讀者都擁有自己所獨有的視界,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通過參預化及間距化,與作者的視界達到統一,而師陀在語言上的泛指,則更好的實現了作者與讀者視界的融合。
泛指的另一種表現是人物的類型化,在果園城中,有著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無論是哪個人物形象,師陀在進行描寫時,并沒有深刻的刻畫人物的性格,而是以“類”來表現,因而,在果園城中,一個人就代表了一類人。師陀在進行人物描寫時,盡管也會描寫人物的個子、頭發、臉色、嘴、眼眉等,但是在這看似清晰的描寫中,實則是一種模糊的輪廓。師陀在對人物進行描述的過程中更加注重的是每個人所具有的肖像共同特征,更加注重塑造整體感。通過這種泛指的語言特色,使《果園城記》具有非常濃重的藝術特色。
(二)濃縮
《果園城記》是師陀創作的短篇小說集,因此,《果園城記》是由很多短小精悍的小說組成,對于故事的內涵,師陀都會將其濃縮為哲理性的議論,引發讀者的深思。師陀在創作的過程中,是不避議論的,哪怕上一秒正在描寫一個人物,下一秒師陀都可以寫出大篇幅的議論和感慨,這些議論并沒有特定的位置,而是隨機的散落在文中的各處,而這些議論就是作品的著力點。比如在《狩獵》中,有這樣一段議論,“你不防順從你的志愿盡量往遠處跑,當死來的時候,你倒下去任憑人家收拾。”實際上,這種議論方式并不是師陀所創作出來的,前面已經說過,師陀成長于“五四”時期,因而受到新文學理性色彩的影響很深。在師陀的思想中,點明作品的主旨在作者的責任,不過,師陀在點明主旨時,將自身的感情傾注到議論的文字中,而這種飽含深情的語言也將濃縮所帶來的負面效果降到了最低。在濃縮的過程中,師陀的場景描寫也變得精雕細琢,留給讀者很多額外的想象空間。《果園城記》中包含了非常豐富的情感型議論,一般情況下,更加隱蔽的見解對于作者所創作的藝術作品來講就越好。但是師陀在創作的過程中以抒情,以情感和詩化的語言彌補著思想濃縮后帶來的負面影響,為理性尋找到了較為恰適的“合作伙伴”。在《果園城記》中,師陀使用較多的就是濃縮手法為縱向濃縮,通常是以“講故事”來代替“寫故事”,故事在時間跨度方面也非常大,例如在寫“人”的過程中寫了人的一生,在寫“家族”的過程中寫了家族幾代人的興衰。師陀在簡短的敘述中包含了十幾年甚至是幾十年的事件。例如師陀在寫說書人的過程中,從早年說書的場景一直寫到他垂垂老矣,最終孤獨死去。在《劉爺列傳》中對劉家三代進行了描述,第一代起家、第二代爭斗、第三代敗完家業。
五、結語
師陀是20世紀30、40年代的作家,《果園城記》是其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經過八年的艱辛創作而成,具有非常獨特的風格。在《果園城記》中,包含著多篇短小精悍的故事,每篇故事中都塑造出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并且蘊含著師陀對其的情感。在語言特色上,師陀采用了泛指及濃縮相結合的方式,使得《果園城記》更具獨特的藝術風格,將師陀不與他人一致的創作手法表現的淋漓盡致。
【參考文獻】
[1]丁曉萍,王伊薇,說書人之聲:論《果園城記》的敘事方法與敘事意圖[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07):14-26
[2]王欣.鄉土中國的“思與詩”——重讀師陀的《果園城記》[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05):27-34
作者簡介:黃賓賓,遼寧理工學院(原渤海大學文理學院)2012級漢語言文學專業在讀本科生。研究方向為漢語言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