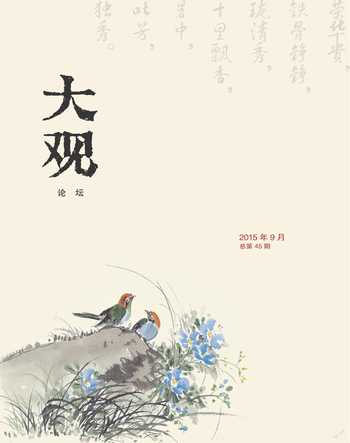《夷堅志》
熊鑫
摘要:李逵形象的形成,首先出現(xiàn)在民間口頭傳說,經(jīng)過說書藝人的講述和記錄,最終通過作家的編輯和加工完成。本文就以《夷堅志》中與李逵有關的文學人物作對比,簡單的勾勒出黑旋風李逵形象的形成史,搞清楚《夷堅志》中的人物形象對李逵形象的形成的影響。
關鍵詞:李逵;《水滸傳》;《夷堅志》
有關《夷堅志》對《水滸傳》的影響,前輩學者多有提及。魯迅《華蓋集續(xù)篇·馬上支日記》引《夷堅甲志》卷十四《舒名殺四虎》,指出此條與《水滸傳》第三十四回所敘李逵沂嶺殺四虎事相類,“疑即本此等傳說作之”。那么,就讓我們具體去《夷堅志》中看有關李逵的故事。
《夷堅甲志》卷十四有《舒民殺四虎》條,此正是“李逵殺四虎”的原型。最早持此觀點的是魯迅,見其《華蓋集續(xù)編·馬上支日記》。孫楷第先生的語氣更為肯定,他認為“李逵殺四虎”事,完全依此改寫。李逵殺四虎是李逵故事中最為精彩的部分,那么,它是如何取材于《夷堅志》的呢?
《舒民殺四虎》的內(nèi)容如下:
紹興二十五年,吳傅朋說除守安豐軍,自番陽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見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弛擔觀之。其人曰,吾村有婦人為虎銜去,其夫不勝憤,獨攜刀往探虎穴,移時不反,今謀往救也。久之,民負死妻歸,云,初尋跡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戲巖竇下,即殺之,而隱其中以俟。少頃,望牝者銜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斷其一足。虎棄所銜人,踉蹡而竄;徐出視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數(shù)十步,墮澗中。吾復人竇伺,牡者俄咆躍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殺之。妻冤已報,無憾矣。乃邀鄰里往視,輿四虎以歸,分烹之。
我們再看看《水滸傳》李逵殺四虎的故事,《水滸傳》中李逵與舒民同樣都是殺了四只老虎,都是兩只小老虎兩只大老虎。與舒民不同的是,《水滸傳》在改編中突出了李逵的孝心與勇猛。舒民殺四虎中,舒民是隱藏在洞中,老虎倒身入穴,舒民從而偷襲成功。李逵則是直接面對雌老虎,憑借自己的勇氣與武功殺掉了它,而李逵殺雄虎,則頗費周折,這種改編凸現(xiàn)了李逵的雄健與武勇。馬雍先生稱《水滸傳》李逵殺虎之所以描寫生動,“實當歸功于景盧(即洪邁)”,其言甚是。可見,《夷堅志》為《水滸傳》提供了不少的素材,李逵殺四虎的故事便來自與《夷堅志》。
《夷堅志》支丁卷第四有《朱四客》條,故事講敘婺地某人朱四客,在看望女兒途中遭遇盜賊,朱氏勇奪其槍并將盜賊踢于崖下,沒想到傍晚投宿旅店,恰好正遇到賊窩,朱氏燒了此賊房屋后脫身離去。此故事被認為是真假李逵故事的原型。其材料如下:
民朱四客,有女為吳居甫侍妾。每歲必往視,常以一仆自隨。因往襄陽,過九江境。山嶺下逢一盜,軀干甚偉,持長槍,叱朱使住而發(fā)其篋。朱亦健勇有智,因乘間自后引足蹴之;墜于岸下。且取其槍以行。暮投旅邸。主媼見槍,扣之。遂話其事。媼愕然如有所失。將就枕,所謂盜者跛曳從外來,發(fā)聲長嘆日:“我今日出去,卻輸了便宜,反遭一客困辱。”欲細述所以,媼搖手指之日:“莫要說,他正在此宿。”乃具飯餉厥夫,且將甘心焉。朱大懼,割壁而竄,與仆屏伏草間。盜秉火求索,至二更弗得。夫婦追躡于前途十數(shù)里。朱度其去已遠,遽出,焚所居之屋。未幾,盜歸,倉皇運水救火,不暇復訪。朱遂爾得脫。
《水滸》中寫李逵上梁山后欲回鄉(xiāng)取母,至沂州境,路逢假冒黑旋風者,李逵斗倒此人后欲殺之。李鬼自言家有老母,因贍養(yǎng)之故方來此打劫。李逵憐其孝心,給了銀兩放走此人。后李逵投宿于某山村人家歇臥,恰遇李鬼跛腳而歸,向其婦自述經(jīng)歷,正被李逵聽到,于是李逵殺此二人,焚屋而去。二書不僅情節(jié)脈胳極其相似,而且如人物的對話,如盜賊都是跛腳而歸都極其相似,這個故事的發(fā)生地也正好在江西九江(即江州)。這讓我們不得不懷疑真假李逵的故事就取自于《朱四客》。
最后來看《陳靖寶》條,此是《水滸傳》中“羅真人戲耍李逵”的原型所在。試看其原文:
紹興甲子歲,河南邳徐間多有妖民以左道惑眾,而陳靖寶者為之魁杰。虜立賞格捕之,甚峻。下邳樵夫蔡五采薪于野,勞悴饑困,衣食不能自給,嘗嘆喟于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有官有錢,便做一個快活漢。如今存濟不得,奈何!”念念弗已,逢一白衣人荷擔,上系葦度,從后呼曰:“蔡五,汝識彼人否?”答曰:“不識。”白衣曰:“汝不識,如何捉得他,我卻識之,又知在一處。恨獨力不能勝耳。”蔡大喜,釋擔以問。白衣取葦席鋪于破垣之側(cè),促坐,共議所以躡捕之策。斯須起,便旋路東。回顧蔡,厲聲一喝。蔡為席載起,騰入云霄,邊空而飛,直去八百里墮于益都府庭下。府帥震駭,謂為巨妖。命武士執(zhí)縛,荷械獄犴,窮訊所由。蔡不知置辭,但言:“正在下邳村下,欲砍柴,不覺身已忽然飛來。實是枉苦。”府移文下邳,即其居訪,逮鄰左,驗為平民,始獲免。而靖寶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此文寫的是一個樵夫蔡五想捕盜賊以獲懸賞,卻為會妖術的盜賊所戲弄的故事。《水滸》第五十三回《戴宗智取公孫勝,李逵斧劈羅真人》記李逵因斧劈羅真人,受到羅真人戲懲:真人以白手帕鋪于石上,喚李逵踏上,說是要送歸梁山。那手帕化一片白云飛起,羅真人喝聲“去!”一陣風把李逵吹入云端,耳邊只聽得風雨之聲,不覺徑到薊州地界,卻從薊州府廳屋上骨碌碌滾將下來,當時正值府尹坐衙,看見半天里落下一個黑大漢來,謂是妖人,命獄卒痛打之。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被大枷釘了,押下大牢。情節(jié)與《夷堅志》的《陳靖寶》條全同,主人公都是乘坐飛毯之類的法器被送到官府遭到戲弄,二者相襲改編的痕跡,不言自明。
上述三則故事,發(fā)生地皆在江南,其中兩篇或在江州或與之關聯(lián)。那個時代說話藝術中有“樸刀”、“桿棒”一類的題材很是流行,雖然《醉翁談錄》中存留下的這類話本名目多數(shù)已經(jīng)無從考實。由此,筆者揣測,上述三個作品很可能最初會被南宋說書藝人利用來塑造“樸刀”、“桿棒”一類的某位草莽英雄,而且這位草莽盜賊的籍貫與活動范圍應該在江州或其附近。后因南宋期間李逵故事的單薄,于是有藝術人轉(zhuǎn)以此類素材附會到李氏身上。筆者揣測這些素材為南宋民間藝人改編,也許起先塑造出的是一位江州籍英雄,后因李逵故事之單薄,遂又轉(zhuǎn)而附會到李氏身上。當然,在《水滸》故事流行于南宋的街頭巷尾時,說書藝人為了彼此爭雄,也不排除直接采用《夷堅志》中素材來豐富水滸傳奇的可能。
可見,《夷堅志》中,我們可以看到李逵故事最早的出處。不僅是李逵的故事,整部水滸傳都與《夷堅志》存在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水滸傳》中有許多的素材都來源與《夷堅志》。
【參考文獻】
[1] 項裕榮.試論李逵形象塑造的南北融合[J].學術論壇,2007(01)
[2] 聶紺弩.《水滸》四議[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3
[3] 鮑鵬山.鮑鵬山新說水滸[M].上海: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
[4] 馬雍.《<水滸傳>李逵故事來源》,《文史》,北京:中華書局,198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