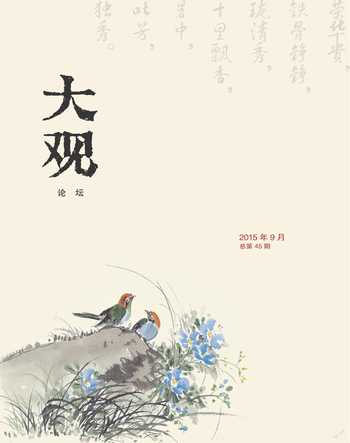悲劇式英雄
摘要:阿喀琉斯和哈姆雷特分別是荷馬《伊利亞特》、莎士比亞《哈姆雷特》中精心刻畫的悲劇式英雄。作者雖身處不同時空,創作風格不同,卻不約而同地塑造了相同的人物性格:勇敢、仁慈卻又粗暴殘忍。本文通過這兩部經典著作的研究,呈現出兩位人物的傳奇事跡。
關鍵詞:悲劇式英雄;阿喀琉斯;哈姆雷特;性格塑造
《伊》以形象鮮明,結構嚴謹,成為西方文學中一顆耀眼的明珠。但丁曾言:“站在《伊》旁邊,我覺得這本書有10英尺高,令人驚嘆不能自已。”《哈》以情節繁復,寓意深刻,成為西方文學的杰出代表。作者雖身處不同時空,創作風格不同,卻不約而同地塑造了相同悲劇式人物的性格:勇敢、仁慈卻又粗暴殘忍。
正如亞里士多德提出的那樣,“悲劇性英雄既非完美無缺,又非邪惡至極…這樣的人物由于錯誤地選擇了某一行動而遭受從幸福到悲慘的命運轉變,這種錯誤的選擇是由于他的判斷錯誤所造成的,或稱為悲劇性缺陷。”而阿喀琉斯和哈姆雷特的悲劇性缺陷無疑與其多面的性格有著莫大的聯系。
一、阿喀琉斯的性格塑造
阿喀琉斯是《伊》眾多人物中杰出的典型。他的身上貼滿許多標簽:半神英雄,第一勇士,刀槍不入,勇敢卻又暴躁殘忍,自私自利。黑格爾曾評價:“這是一個人!高貴的人格的多方面性在這個人的身上顯示出了它的全部豐富性。”
《伊》開篇寫道:女神啊,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致命的憤怒吧!它給阿凱亞人帶來無窮痛苦,把許多英雄的靈魂拋向哈得斯。整部《伊》都是圍繞“阿喀琉斯致命的憤怒”展開的,源于他的勇敢無畏。神諭他有兩種命運:或默默無聞而長壽,或功勛卓著而死亡。即使知道自己將葬身特洛伊城下,他卻毫不猶豫的踏上了征戰希臘的征程,斬敵無數,建立赫赫功勛。同時,他善良仁慈,珍視友誼。在 《伊》中,荷馬用生動的文字描寫了他與帕特羅克洛斯情同手足的友誼。當安提羅科斯帶來摯友死亡的噩耗,他眼前發黑,痛哭不已,決心為朋友復仇。不顧母親再三勸阻,阿喀琉斯憤怒地叫起來:“如果命運之神不讓我保護我死去的朋友,那么我寧愿馬上去死。他遠離故鄉,沒有得到我的援救,因此被殺害了。現在我這短暫的生命對希臘人有什么用處呢?”怒火燃起了他的斗志,阿喀琉斯披上戰甲與赫克托爾決戰,殘忍地殺死對手。然而,面對赫克托爾父親苦苦哀求,他也悲痛地哭起來,交還了赫克托爾的尸體并休戰11天,讓老國王從容地為兒子舉行葬禮。除了勇敢和仁慈之外,阿喀琉斯性格的又一重要側面是他的粗暴殘忍。怒火燃燒的阿喀琉斯將特洛伊城變成了人間煉獄,人擋殺人,神擋殺神,死者的尸體填滿了克珊托斯河。變成嗜血魔鬼的阿喀琉斯殘忍地殺死對手并用馬將其尸體繞著朋友的靈柩拖拽三周。更甚者,他用12個特洛伊戰俘為好友陪葬。
細細品味《伊》的每一處細節,讀者不難發現荷馬在性格塑造上的用心良苦。正是因為荷馬的故意為之,才有血有肉的悲劇式英雄阿喀琉斯的誕生因此,荷馬史詩的作者可以驕傲的說:在西方文學的史冊上,我們創造了第一個“人”。
二、哈姆雷特的性格塑造
哈姆雷特是《哈》劇眾多人物中杰出的典型。莎翁筆下的哈姆雷特風流倜儻,文武全才,聰明睿智卻又陰郁多疑。除此之外,同阿喀琉斯一樣,善良仁慈,崇尚勇敢卻又暴躁殘忍。徐葆耕在其專著中寫道:“《哈》劇使人感興趣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哈姆雷特“拖延”復仇的問題。”關于哈姆雷特為什么“拖延”復仇的闡釋也有十余種,性格上的研究也無疑囊括其中,大大加強該劇的復雜性和深刻性。
“存在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這就是著名的“哈姆雷特命題”,也是貫穿整部《哈》劇及哈姆雷特短暫一生的謎題。這一謎題更加凸顯和塑造了主人公性格的多面性。豁達開朗的哈姆雷特在知得父親死訊,叔父克勞迪斯即位以及母親改嫁叔父的接連變故下,一度郁郁寡歡,頹廢至極。然而從父親鬼魂處得知其被叔父所殺,母親改嫁仇敵的事實后,哈姆雷特從憂郁中振作起來并發誓為父報仇,整治國家。無論是裝瘋躲開宮廷中耳目,還是用計逃脫克勞迪斯的謀害,乃至最終要以性命為代價進行復仇,哈姆雷特沒有膽怯,毅然決然的承擔自己的責任,從中不難看出他的勇敢和擔當。同時,他善良仁慈,視眾生平等。哈姆雷特曾高歌:“人類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貴的理性!多么偉大的力量!多么優美的儀表!多么文雅的舉動!在行為上多么像一個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個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 因此,本可輕而易舉毀滅正在祈禱的殺父仇人,他的仁慈讓他猶豫了,放棄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也為自己的死亡埋下了伏筆。然而,這個對仇人尚可手下留情的人,卻殘忍粗暴的傷害自己摯愛之人-奧菲莉婭,那個心地善良,感情純真的絕美少女。作為仇敵幫兇波洛涅斯的女兒,奧菲莉婭成了哈姆雷特用來復仇的棋子。哈姆雷特借“發瘋”之名,對奧菲莉婭進行無禮挑釁、咒罵,使她傷透了心,悲觀絕望,而后更因其誤殺躲在窗簾后偷聽自己與母親談話的波洛涅斯,哈姆雷特終將摯愛之人逼瘋。父親的死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陷入精神錯亂的奧菲莉婭最終失足落水。哈姆雷特間接害死了自己的愛人,成了結束奧菲莉婭年輕生命的劊子手。
《哈》劇最后的悲慘結局,不僅留給世人不盡的思考,也有對哈姆雷特悲慘命運的惋惜以及對其多重性格的深沉反思。“直到今日,西方哲學家和藝術家還在被其所擾,夢魘般的問自己:存在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一切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作家精神的產物,既代言了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也塑造了無數曠世英雄,賦予他們獨有的多面性格。阿喀琉斯也好,哈姆雷特也罷,不同時空的產物,卻有著相似的傳奇,相同的悲劇命運,成了千古傳頌的悲劇式英雄。
【參考文獻】
[1]荷馬.伊利亞特[M].羅念生,王煥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艾布拉姆斯.文學術語詞典[Z].吳松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3]黑格爾.美學(第一卷)[M].上海:商務印書館,1979.
[4]荷馬.伊利亞特[M].陳忠梅譯.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
[5]徐葆耕.西方文學之旅[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作者簡介:趙麗君:女,黑龍江人,畢業于云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主修英語語言文學專業。職稱:助教。